数学与文学的共鸣——当代数学大师丘成桐教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演讲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6:11:04 国学网 丘成桐 参加讨论
 CF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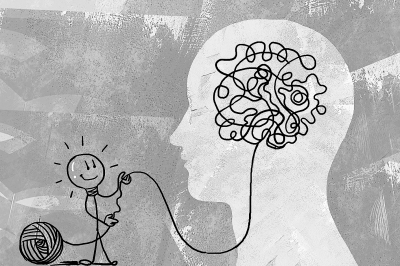 CFP ■演讲人:丘成桐 ■演讲地点:北京外国语大学 ■演讲时间:二○一五年十二月 从古至今,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科方面,学科分支越来越细,内容也越来越丰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工具的增加,使人们发现不同现象的能力比以往更强。另一方面,伴随着全世界人口大量增长,不同种族、宗教、习俗的人在互相交流后,他们的观点和学问得到融会贯通,从而迸发出新的火花。 两千多年前,孔子谈论自己的学问时曾说:“吾道一以贯之”。面对越来越纷繁复杂的学科,今天的学者还能做到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吗?我将探讨这个问题。 原创力从何而来 在建构一门新的学问,或是引导某一门学问走向新的方向时,学者的原创力从何而来?为什么有些人看得特别远,找得到前人没有发现的观点?这是一种本能的理性选择,还是读书破万卷的结果?诸多因素当然都极其重要,但在这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创造力和脚踏实地基础上的丰富情感。 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作《楚辞》,李陵作《河梁送别诗》,太史公作《史记》,诸葛亮作《出师表》,曹植作《赠白马王彪诗》,庾信作《哀江南赋》,王粲作《登楼赋》,陶渊明作《归去来辞》,这些作品可以说是千古绝唱。然后,我们又看到李白、杜甫、白居易、李煜、柳永、晏殊、苏轼,一直到清朝的纳兰性德、曹雪芹。他们的诗词文章,激情澎湃,荡气回肠,感情从笔尖下源源不断倾泻而出,成为瑰丽的作品。这些作者并未刻意为之,却是情不自禁。何以故?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也。”太史公说:“意有所郁结也。”能够影响古今传世文章的气必然至柔至远,至大至刚! 其实,中国文人在文艺以外的活动,表现出来的感情也是极为丰满,不少人为了理想而不惜性命。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间关万里,而卫青和霍去病奔驰大漠,出生入死。东晋时,外族入侵,祖狄谋复中原之地,带兵渡江时,祖狄击楫而誓,说“祖狄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此江!”这是何等的志气!同在东晋,法显为求佛法,五十九岁行走河西走廊,过玉门关,横越沙河,翻过葱岭,直达印度。其间历尽艰险,全程十三年四个月。他在《佛国记》里面说:“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不必全之地,以达万一之冀”。宋朝,文天祥被蒙古人囚禁,作正气歌。其实,他的“气”正是孟子说的浩然之气,也是古往今来,中国文学家和科学家所共同享有的。 至于数理方面,也讲究相似的气质。自希腊的科学家到现代科学家,文笔优美雅洁的大有人在。他们并没有刻意为文,然而文既载道,自然可观。数理之与人文,实有错综交流的共通点。 古代希腊人和中国战国时的名家,雅好辩论,寻根究底。在西方,因此而产生了对公理的研究,影响了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从欧几里得的“几何公理”到牛顿的“三大定律”,再到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莫不与公理思维有关。 无论在西方或是在中国,科学的突变或革命都以深刻的哲学思想为背景。希腊哲学崇尚自然,为近代的自然科学和数学发展打好了基础。中国人偏重人文,在科学上主要的贡献在于应用科学。但有趣的是,中国人提出五行学说,希腊人也企图用五种基本元素来解释自然现象,柏拉图甚至用当时发现的五个最对称的多面体来跟这些元素一一对应。中国人提出阴阳的观点,西方人也讲究对偶,事实上,希腊数学家研究的射影几何就已经有极点(pole)和极线(polar)的观念。文艺复兴时的画家则研究投影几何,对偶的观念,从那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对偶的观念虽然肇源于哲学和文艺思想,但对近代数学和理论物理的影响巨大。七十年前,物理学家已经发现负电子的对偶是正电子,而几何学家则发现光滑的紧致空间存在着庞加莱对偶性质,后来,高能物理学最成功的标准型理论的主要骨干就是几个重要的对称群的表示,这种表示理论在近代几何和数论也有着奠基性的重要作用。近三十多年来,物理学家发现他们在此前引入的超对称观念,可以提供粒子物理和几何丰富的思想,它预测所有粒子都有超对称的对偶粒子,同时极小的空间和极大的空间可以有相同的物理现象,假如实验能够证明超对称的想法是正确的话,阴阳对偶就可以在基本物理中具体地表现出来了,说不定现代物理的概念可以修正和改进中国人对阴阳的看法。 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理文并重,他们也将科学应用到绘画和音乐上去。从笛卡尔、伽利略到牛顿、来布尼兹,这些大科学家们在研究科学时,都讲究哲学思想,通过这种思想来探索大自然的基本原理。 以后伟大的数学家高斯、黎曼、希尔伯特、外尔等都寻求数学和物理的哲学思想。“黎曼几何”就从哲学和物理的观点来探讨空间的基本结构。至于爱因斯坦在创造广义相对论时,除了用到“黎曼几何”等观念,更是大量采用哲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想法。 能够左右科学发展主流的学问必须包含如下的性质:它能够对大自然对数学的现象有普遍和深入的了解。在物理学中,我们对一些现象进行抽象、解释,从而创立理论,在这些理论基础之上,我们去推导,找寻新的现象,并重新观察,反复实验,来检验这些理论。当这些理论得到验证之后,如果应用范围很广泛,我们就称之为定律。受到欧几里得公理化的影响,经典力学的支柱是牛顿三大定律,其叙述极为简单,而描述的现象却极为深刻,它的真实不受时空的限制!这是一千多年来,无数物理学家智慧的结晶。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将无数有意义的现象抽象和总结而成为定律时,中间的过程总是富有情感!在解决大问题的关键时刻,科学家的主观感情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种感情是科学发现的原动力!伽利略对教会的挑战就是这一感情的集中表现。 当科学家发现的定律或定理是如此的简洁,既不失普遍性,又无比有力地解释各种现象时,我们不能不赞叹自然结构的美妙,也为这个定律或这个定理的完成而满意。这个过程值得一个科学家投入毕生的精力!苟真理之可知,虽九死其犹未悔! 数理与人文的共通 我遇见过很多大科学家,尤其是有原创性的科学家,对文艺都有涉猎。他们的文笔流畅,甚至可以媲美文学家的作品。其实,除了文艺能够陶冶性情以外,文艺创作与科学创作的方法实有共通的地方。出色的理文创作,必须有浓厚的感情和理想,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并不比西方人逊色。中国古代学者都有浓厚的感情,它们充分的表现在诗词歌赋上。 诗人墨客,诗词歌赋,最能表现这种高尚的情怀。现代的杰出科学工作者,肉体上未必经得起上述诸贤的艰苦经验,但他们做研究时的毅力却可以跟上述诸贤媲美。科学家与文学家有很多能够产生共鸣的地方。事实上,除了有共同的感情,在研究的方法上,他们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数学家也可以用和古代中国文学家赋比兴类似的手法,做出一流的创作。苏东坡是一代词宗。在他七岁时,见到眉山的一个老尼,姓朱,年约九十。她告诉苏轼,自己曾经去过蜀主孟昶的宫廷中。有一日,天气炎热,蜀主和他的妃子花蕊夫人深夜纳凉于摩诃池上。孟昶作了一首词。这个尼姑还能记得这首词,并把他告诉了苏轼。 四十年后,苏轼只能够记得词中头两句。苏轼有天得暇,寻找词曲,猜测这词应该为洞仙歌令。苏轼因此循着这两句的意境猜测蜀主的想法,将词续完,成为《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苏轼续词对中国文学是一个贡献。但我们想想,不同的文人面对残缺的词句,一定会有不同的反应。假如是清代的乾嘉学者,就可能花很多时间对这件事做考据,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词不可考!因此不会去续这首词。有一些文人,可能没有能力去猜测到这词的词牌名,另外有一些文人,可能像苏轼一样,猜到了词牌名,却没有兴趣去将它续起来。还有一些文人,虽然找到词牌名,但文艺功力太差,续出来没有趣味的词。但是,苏轼却兴致勃勃地花了时间去推敲,写了一篇传世的杰作! 科研的创作也有类似的情形。现在来看看科学的发展,在1905年,物理学家知道两个重要的理论,就是牛顿的“引力场论”和“狭义相对论”。它们都与引力有关,同时都基本正确,却互相矛盾。爱因斯坦对这个问题有无比的兴趣,他知道这两个理论是一个更完美的引力理论的一部分,他在数学家闵科夫斯基、高斯、黎曼和希尔伯特的帮助下,完成了旷世大作,就是让我们钦佩的“广义相对论”。 爱因斯坦的创意和能力当然远胜于苏轼补《洞仙歌》,但却有点儿相似。我来做一个不大合适的比拟,苏轼记得蜀主的两句词,一句可比拟为“牛顿力学”,另一句可比拟为狭义相对论里面的“洛伦兹变换”。爱因斯坦花了十年工夫来研究引力场,就是从这两件事情作为出发点,用他深入的物理洞察力和数学家提出的数学结构。 物理学需要实验,数学需要证明,文学却不需要这么严格,但是离现象太远的文学,终究不是上乘的文学。一首词续得好,需要有文学修养,也需要有意境,才能够天衣无缝,但和大型歌剧或小说比较,它的创作,还是来得容易些。 现在来看看文学和科学的领域里,大型的结构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曹雪芹并没有把经典著作《红楼梦》全部完成,这千古憾事,如何将它续完呢?除了需要有出色的文学技巧外,还需要了解该书的内容和背景。由于这部书的内容错综复杂,在现代的观点来看,可能需要用统计和数学的方法来帮忙。 曹雪芹写《红楼梦》,借用了自身的经历来描述当年家族的荣华富贵,也描述封建社会大家族所遇到的无可避免的腐败和堕落。他与评书人脂砚斋,一路著书,一路触目愁肠断。书中的笔墨,充满了他澎湃的感情,但却是有条有理的创造和叙述。在这本书差不多完成时,作者却因伤感而去世了,“芹为泪尽而逝”。但至今还没有任何作者能够将这部巨著完满地续成,对曹雪芹当年的想法如何处理,仍是争论不已的大问题。 《红楼梦》的创作过程有如一个大型的数学创作,或者一个大型的科学创作。数学家和科学家,也是企图构造一个架构,来描述见到的数学真理或是大自然的现象。在这个大型结构里,有很多已知的现象或者定理。在这些表面上没有明显联系的现象里,我们要企图找到它们的关系。当然我们还需要证明这些关系的真实性,也需要知道这些关系引起的效果。 但如何找到这些联系的方法,因作家而异。在小说的创作里,小说家的能力和经历,会表现在这些地方。一个好的科学家,都会创造自己的观点,或者自己的哲学,来观察我们研究的大结构。 韦伊(André Weil)要用代数几何的方法来研究数论的问题,而朗兰兹(Robert Langlands)要用自守型表示理论来研究数论。他们在建立现代数论的大结构时,就用了不同的手法来联系数论中不同的重要部分,得到数论中很多重要的结论,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得到的结论往往一样,殊途同归。 当年我和一群朋友建立“几何分析”这门学问时就采取一个观点:大量的几何现象需要用非线性微分方程来解释,方程的解往往可以决定空间的几何性质。几何学家想研究的现象包括了子流形和不同的几何结构,我在1976年完成的“卡拉比猜想”就是要构造复流形上的几何结构,方法是解非线性微分方程。二十世纪代数几何和算术几何的发展就是一个宏伟的结构,比红楼梦的写作更瑰丽,更结实,但它是由数十名大数学家共同完成的。 在整个数学洪流中,我们见到大数学家各展所能,发展不同的技巧,解决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要左右整个大流方向的数学家,实在不多,我们上面提到的韦伊、朗兰兹就是很好的例子。 中国数学的喜与忧 在汉朝,中国数学家已经开始研究如何去解方程式,包括计算立方根,到宋朝时,已经可以解多次方程,比西方早几百年,但解决的方法是数字解,对方程的结构没有深入的了解。 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解二次方程: X²+1=0 事实上,无论X是任何实数,方程的左边总是大于零,所以这个方程式没有实数的解,因此中国古代数学家不去讨论这个方程式。 大约在四百多年前,西方数学家开始注意这个方程,文艺复兴后的意大利数学家发现它跟解三次和四次方程有关。他们知道上述二次方程没有实数解,就假设它还是有解,将这个想象中的解叫作虚数。 虚数的发现很了不起!有了虚数后,西方学者发现所有多项式都有解,而且解的数目刚好是多项式的次数。所以有了虚数后,多项式的理论才成为完美的理论。 完美的数学理论很快就得到无穷的应用。事实上,后来物理学家和工程学家发现虚数是用来解释所有波动现象最佳的方法,这包括音乐、流体和量子力学里面波动力学的种种现象。数论研究对象的重要部分是整数,但为了研究整数,我们不能避免地要大量用到复数的理论来帮忙。 在19世纪初叶,柯西和黎曼开始了复变函数的研究,将我们的眼界由一维推广到二维,改变了现代数学的发展。黎曼又引入了Zeta函数,发现了复函数的解析性质可以给出整数中的质数(prime number)的基本性质。另一方面,他也因此开发了高维拓扑这个学科。由于复数的成功,数学家企图将它推广,制造新的数域,但很快就发现除非放弃一些条件,否则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哈密尔顿(William Rowan Hamilton)和凯利(Arthur Cayley)先生却在放弃复数域中某些性质后,引进四元数(quarterion)和八元数(Cayley numbers)这两个新的数域。这些新的数域影响了狄拉克(Paul Dirac)在量子力学的构想,创造了狄拉克方程。从这里可以看到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为了追求完美化而得到重要的结果。 爱因斯坦创造广义相对论时,人类观察到的宇宙空间实在不大,他却得到数学家的大力帮助。在爱因斯坦完成广义相对论后,外尔和很多科学家开始融合引力场理论和电磁场理论,外尔率先提出规范场的理论,经过十年的挣扎,才将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看作和广义相对论类似的规范场论,在物理学上,这是一个伟大的突破。二十多年以后,泡利(Wolfgang Pauli)、杨振宁和米尔斯将规范群推广到非交换群后,完成了一般的规范场理论,成为近代物理学标准模型的基础。 有趣的是,外尔说:假如理论和见到的现象有冲突,而这个理论漂亮而简洁的时候,我宁愿相信理论。这个看法对规范场理论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文学家和科学家类似的地方。 将一个问题或现象完美化,然后,将完美化后的结果应用到新的数学理论,来解释新的现象,这是数学家的惯用手法,与文学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不过文学家用这种手法来表达他们的感情罢了。 在中国古代,很多传说都是凭想象力,根据已知知识夸大地描述很多无法证明的事情。文学家为了欣赏现象或者舒解情怀而夸大,而完美化,但数学家却为了了解现象而构建完美的背景。有些时候,数学家花了几千页纸的理论将一些模糊不清的具体现象用极度抽象的方法去统一、描述、解释。 这是值得惊喜的事:近代数学家在数学不同的分支取得巨大的成果,与文学家的手段极为类似。所以好的数学家最好有人文的训练,从变化多姿的人生和大自然中得到灵感来将科学和数学完美化,而不是禁锢自己的脚步和眼光,只跟着前人的著作,做少量的改进,就以为自己是一个大学者。 我们需要培养一些能望尽天涯路,又能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学者,这需要浓郁的文化和感情的背景。中国数学家太注重应用,不在乎数学严格的推导,更不在乎数学的完美化。因此至明清时,中国数学家实在无法跟文艺复兴的数学家相比。直到如今,除了少数两三个大师外,中国数学家走的研究道路基本上还是萧规曹随。在创新的路上提不起勇气,不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这一点与中国近几十年来文艺教育不充足,对数理感情的培养不够有关。 到今天,中国的理论科学家在原创性还是比不上世界最先进的水平,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科学家在人文的修养还是不够,对自然界的真和美感情不够丰富。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感情和富有深度的民族。上述的文学家、诗人、小说家的作品,并不落后于世界!但是,我们的科学家对人文的修养却不大注意,一些管理教育的官员们却有很奇怪的教育政策,他们似乎认为语文和历史的教育并不重要,转而用一些浅显而没有深度的通识教育来代替这些重要的学问,大概他们以为国外注重通识教育的缘故吧。这种做法其实是舍本逐末。 坦白说,我还没有看到过一个有水平的国家和城市不反复地去教导国民们本国或本地的历史。我两个孩子在美国一个小镇读书。他们在小学、中学,将美国三百年的事情念得滚瓜烂熟!因为这是美国文化的基础。我敢说,不懂或是不熟习历史的国民,必定会认为自己是无根的一代。一般来说,文化的根基比较肤浅的人容易受愚弄和误导,因为他们看不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 史为明镜,它不单指出古代伟人成功和失败的原因,它也将千年来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感情传给我们,我们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创下的丰功伟绩感到骄傲,为他们的子孙走错的路而感叹!中国五千年丰富的文化使我们充满自信心!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地利用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 或许有人说,我不想做大科学家,所以不用这样学。其实这并不矛盾。当一个年轻人对自己要学习的学问怀有浓厚的感情后,学习任何学问都会变得轻而易举。至于数学和语文并重,在先进国家一向是理所当然的。美国比较好的大学招生时,都注重看待SAT中语文和数学部分。 除了考试以外,美国好的中学也鼓励孩子多元化,尽量涉猎包括人文和数理的科目。美国有很多高质量的科普杂志,销量往往都在百万本以上。而中国好的科普杂志不多,销量也少得可怜,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希望在未来能够渐渐改进。 最后要指出,数理人文和所谓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有着莫大关系。博雅教育的目标广阔,既着眼于基础知识、鉴古知今、推理分析,又能培养学生在艺术上的创造性,兼且对科学的概念和实验的精准性有所了解,同时也强调因材施教,反对重复不断的操练,防止出现过早学科化和专业化的潮流。 以培养专业人才为目标是许多名校的优良传统,但这绝非哈佛大学的使命。哈佛学子在专注于某门学问的同时,学校更希望他们成为一个事事关心、善于分析和独立思考的人,毕业后有志贡献于社会,并不断学习。 美国名校的教育使得不少的学者跨越不同的领域而得到极大的成就。有些学生在本科时读英文系,毕业后却可以成功地创立高科技公司。当代数学物理有极为杰出成就的威腾(Edward Witten)教授在本科时念历史。这些例子在美国名校不胜枚举,但在华人社会却不多见。这应当归功于美国博雅教育的结果,也就是数理人文并重的结果。 中国的教育始终离不开科举的阴影,以考试取士,系统化的出题目,学生们对学问的兴趣集中在解题上,科研的精神仍是学徒制,很难看到寻找真理的乐趣。西方博雅教育的精神确实能开阔我们的视野,激励我们的感情,更能够培养大学问的成长。我写过一本叫作《大宇之形》的科普书,有些物理系教授也用来作为通识课本。多读多看课本以外的书,对我们做学问,为人处世都会有大帮助。 好的文学诗词发自作者内心,而将人与人的关系、人对自然界的感受生动呈现出来。激情处,可以惊天地泣鬼神,而至于万古长存不朽不灭!伟大的科学家不也是同样地要找到自然界的真实和它永恒的美丽吗? 丘成桐 当代数学大师,现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1971年师从陈省身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发展了强有力的偏微分方程技巧,使得微分几何学产生了深刻的变革。解决了卡拉比(Calabi) 猜想、正质量猜想等众多难题,影响遍及理论物理和几乎所有核心数学分支。年仅33岁就获得代表数学界最高荣誉的菲尔兹奖(1982),此后获得MacArthur天才奖(1985)、瑞典皇家科学院Crafoord奖(1994)、美国国家科学奖(1997)、沃尔夫奖(2010)等众多大奖。现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和俄罗斯科学院的外籍院士。 (本报记者陈鹏整理,本文内容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数学的艺术》内容有重合,已得到作者认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