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新道教的是他! 汤一介谈北魏道教领袖寇谦之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10 学衡 汤一介 参加讨论
 寇谦之,北魏道教领袖,南北朝时期北方天师道改革者 一、生平与著作考证 寇谦之(365—448),北魏道教领袖及思想家,《魏书·释老志》和《北史·寇赞传》中均载有其生平事迹。原名谦,字辅真,祖籍为上谷昌平(今属北京),后徙居冯翊万年(今陕西临潼北),是当时北方的大族豪姓。“早好仙道,有绝俗之心,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无效。”(《魏书·释老志》)后来遇到自称为“仙人”的成兴公,跟随成兴公到华山、嵩山修道,前后共七年。神瑞二年(415)得《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泰常八年(423)又得《录图真经》六十卷。始光初(424)寇谦之带着他的书献给魏太武帝。时北方大族左光禄大夫崔浩以“辞旨深妙”,上疏盛赞,后为太武帝所崇信。崔浩为旧儒家的领袖,寇谦之为新道教的教宗,两人互相利用,相得益彰。太延六年(440)寇谦之声称太上老君降临,授太武帝以太平真君之号,帝信之,遂改元为太平真君。太平真君三年(442)寇谦之上奏书说:“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未之有也。应登受符书,以彰圣德。”太武帝从之,于是亲自赴道坛,受符箓,并封寇谦之为国师。太平真君九年(448)寇谦之卒,葬以道士之礼。 据《魏书·释老志》谓,《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为太上老君所授;《录图真经》六十卷,为太上老君玄孙牧士上师李谱文授。《隋书·经籍志》亦谓:“嵩山道士寇谦之,自云尝遇真人成公兴,后遇太上老君,授谦之为天师,而又赐之《云中音诵科诫》二十卷。……其后又遇神人李谱,云是老君玄孙,授其《图录真经》,劾召百神,六十余卷。”然今两书均已佚失。今《道藏·洞神部·戒律类》力字帙中有《太上老君戒经》、《老君音诵诫经》、《太上老君经律》、《太上经戒》、《三洞法服科戒文》、《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女青鬼律》等七种,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作九卷,阙作者。《道藏》与字帙中有《混元圣纪》(题为“宋观复大师高士谢守灏编”,然《犹龙传》则题为“宋崇德悟真大师贾善翔编”)卷七中记谓:“时老君停驾云中三日,赐谦之经戒凡九卷。”经近人考证其中《老君音诵诫经》当即《云中音诵新科之诫》的一部分。但上列力字帙或全系寇谦之所得之书,或大部与该书有关。今略考之如下: (1)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谓上列七种为九卷。宋贾善翔《犹龙传》谓太上老君所赐寇谦之书为九卷。又宋谢守灏《混元圣记》亦谓:“(老君)赐谦之经戒凡九卷。”而力字帙中除《女青鬼律》分六卷外,其他各种均不注卷数,但按每种的分量看,原来每种戒经或均应分若干卷。《太上老君戒经》文至“夫为恶者始起”下有“原缺文”三字。已有二十九页,且在标题下有“戒上”两字,于文中不见“戒下”,故知原文当较现存者为多,所分卷数当亦有不同;白云霁详注言分三章。其余各戒经原当亦较现存者为多,所分卷数当亦与现存者不同,如《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与《大道家令戒》今同在一卷,原可能为两卷,其他有些戒包括了若干种经戒,并有阙文。如《太上老君经律》为《道德尊经戒》、《老君百八十戒》、《太清阴戒》、《女青律戒》之总名。今《道藏》所存上述各戒经大体上是寇谦之的著作,其文在辗转抄录中必有错落,或有为后人增改者,白云霁详注中于《三洞法服科戒文》下有“三洞弟子太清观道士张万福编录”等字,可见该书是经过后人编修的。张万福是唐朝玄宗时人。 (2)《魏书·释老志》言:《云中音诵新科之诫》的主要内容为“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査今本《老君音诵诫经》、《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之主旨即与之同。按“三张伪法”或有两指,一指张陵、张衡和张鲁三代天师,一指张角、张宝、张梁三位农民起义领袖。甄鸾《笑道论》云“汲世三张诡惑于西梁”,此处三张当是指张陵等三代天师。在当时佛教攻击道教多是攻击张陵等三代天师,特别是攻击张鲁,并于攻击张鲁的同时也攻击张角。唐释法琳《唐废省佛教箴》引《魏志》云: ……鲁遂据汉中,以鬼道化民,符书章禁为本。其来学者初名鬼卒,受道者用金帛之物,号为祭酒,各领部众,众多者名治头,有病者令首过。大都与张角类相似。 按在佛教看来,张鲁行事大都与张角相似,故不加区别。但在道教中,则多见攻击张角者。如葛洪《抱朴子外篇》中说: 曩者有张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称千岁,假托小术,坐在立亡,变形易貌,诳眩黎庶,纠合群愚。进不以延年益寿为务,退不以消灾除病为业,遂以招集奸党,称合逆乱…… 或认为张鲁与张角所行相同。《三国志·魏志·张鲁传》谓: 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 据《魏书·释老志》谓:寇谦之“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不成”,故可知寇谦之所反对的“三张”或兼指两者。而据《道藏》力字帙各经,也往往把张鲁和张角看成一类而加以攻击,如《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中之《大道家令戒》说: 汉安元年五月一日于蜀郡临邛县渠停赤石城造出正一盟威之道与天地券要,立二十四治,分布玄元始气治民。汝曹辈复不知道之根本,真伪所出,但竟贪高世,更相贵贱,违道叛德,欲随人意。人意乐乱,使张角黄巾作乱。汝曹知角何人?自是以来,死者为几千万人,邪道使末嗣分气,治民汉中四十余年。道禁真正之元,神仙之说,道所施行,何以想尔。 又其中之《阳平治》谓: 吾以汉安元年五月一日,从汉始皇帝王神气受道,以五斗米为信,欲令可仙之士皆得升度。汝曹辈乃至尔难教,叵与共语,反是为非,以曲为直。千载之会,当奈汝曹何?吾从太上老君周行八极,按行民间,选索种民,了不可得,百姓汝曹无有应人种者也。但贪荣富,钱财谷帛,锦绮丝绵,以养妻子为务,掠取他民户赋,敛索其钱物……房室不节,纵恣淫情,男女老壮,不相呵整,为尔愦愦,群行混浊,委托师道。老君太上推论旧事,摄纲举网,前欲推治诸受任主者,职治祭酒,十人之中诛其三四名,还天曹考掠治罪,汝辈慎之。 以上两段引文都把张鲁的“五斗米道”和张角的“太平道”看成同类的反叛者。 (3)据《魏书·释老志》言,《云中音诵新科之诫》的主旨在“除去三张伪法”,文中说: (太上老君)谓谦之曰:“……赐汝《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号曰‘并进’。”言:吾此经诫,自天地开辟以来,不传于世,今运数应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大道清虚,岂有斯事。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炼。 査《老君音诵诫经》与上引内容相同者有五点: 第一,“老君曰:吾得嵩岳镇土之灵集仙官主表闻称言:‘地上生民旷官来久。世间修善之人,求生科福,寻绪诈伪经书,修行无效,思得真贤,正法之数。宜立地上系天师之位为范则。今有上谷寇谦之,隐学嵩岳少室,精炼教法,掬知人鬼之情,文身宜理,行合自然,未堪系天师之位。’吾是以东游临观子身,汝知之不乎?吾数未至,不应见身于世。谦之汝就系天师正位,并教生民,佐国扶命,勤理道法,断发黄赤。以诸官祭酒之官,校人治箓符契,取人金银财帛,众杂功愿,尽皆断禁,一从吾《乐章诵诫新法》。其伪诈经法科,勿复承用。”按:“系天师”即“继天师”。 第二,“老君曰:吾以汝受天官内治,领中外官,临统真职,可比系天师同位。吾今听汝一让之辞。吾此乐音之教诫,从天地一正变易以来,不出于世。今运数应出。汝好宜教诫科律,法人治民。” 第三,“太上老君《乐音诵诫令》文曰:我以今世人作恶者多,父不慈,子不孝,臣不忠。……今世人恶,但作死事,修善者少。世间诈伪,攻错经道,惑乱愚民,但言老君当治,李弘应出。天下纵横返逆者众,称名李弘岁岁有之。其中精感鬼神,白日人见,惑乱万民,称鬼神语。愚民信之,诳诈万端,称官设号,蚁聚人众,坏乱土地。称刘举者甚多,称李弘者亦复不少。” 第四,“老君曰:男女道官,浊乱来久。……吾故出《音乐新正科律》,依其头领,欲使信道,以通人情,清身洁己,与道同功。太上清气,当来覆护。” 第五,“老君曰:男女道官,浊乱来久。有作祭酒之官,积勤累世,贪浊若身,化领求复,经数余载。赃钱逋说(按:“说”当作“”),贪秽入己。此是前造,诈言经律。此等之人,尽在地狱。若有罪重之者,转生虫畜,偿罪难毕。吾故出《音乐新正科律》,依其头领,欲使信道,以通人情。清身洁己,与道同功。太上清气,当来覆护,与民更始,改往修来。一从新科为正。明慎奉行如律令。” 以上五段引文就其内容看与上引《魏书·释老志》中内容全同,有些地方连文字也一样。这可说《老君音诵诫经》为寇谦之著作之明证。又《诫经》中有反对佩带黄赤,或与汉末黄巾起义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有关。《诫经》中又反对“操木束薪投石治病”,而“五斗米道”之张修尝“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修法略与角同”。可知寇谦之改革道教之措施都是针对汉末之“太平道”和“五斗米道”而发的。 其中说到“李弘”和“刘举”,且言“称名李弘者岁岁有之”,按:查《晋书》中载有五个“李弘”,均为起义农民的领袖,《宋书》中亦载有一“李弘”。《魏书》中载有两“刘举”。现条列于下: (1)《晋书》卷五十八《周礼传》:“时有道士李脱者,妖术惑众。……弟子李弘养徒灊山,云应谶当王。”事并见《册府元龟》第十二册10886页。此事当约在元帝永昌元年(322)王敦举兵之后。灊山为今安徽霍山。 (2)《晋书》卷一百六《载记》文称:石虎时“贝丘人李弘,因众心之怨,自言姓名应谶,遂连结奸党,署置百僚,事发诛之,连坐者数千家”。事亦见《资治通鉴》卷九十七,晋成帝咸康八年(342)。贝丘在今山东。 (3)《晋书》卷八:“广汉妖贼李弘与益州妖贼李金根聚众反,弘自称圣王。”“圣王”亦作“圣道王”。时在海西公太和五年(370)。广汉在今四川地区。 (4)《晋书》卷一百十八《载记》:“(姚)兴寝疾,妖贼李弘反于贰原。贰原氐仇常起兵应弘。”按其时约在姚兴死(义熙十二年,416)前数年,地当在今川陕地区。 (5)《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又遣江夏相刘岵、义阳太守胡骥讨妖贼李弘,皆破之,传首京都。”按其事在永和十二年(356),地在荆州,今属湖北西部。 (6)《宋书》卷七十六《王玄谟传》:“寻复为豫州刺史。准上亡命司马黑石推立夏侯方进为主,改姓李名弘以惑众,玄谟讨斩之。”按事当在孝建二年(455),时寇谦之已卒。豫州为今安徽寿县。 (7)《魏书》卷七上《高祖纪》:“妖人刘举自称天子,齐州刺史武昌王平原捕斩之。”《魏书》卷十六《河南王曜传》:“有妖人刘举,自称天子,煽惑百姓,复讨斩之。”事并见《北史》卷三、卷十六,《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二。按事在延兴三年(473)。齐州即今山东历城县。 (8)《魏书》卷十《孝庄帝纪》:“光州人刘举,聚众数千,反于濮阳,自称皇武大将军。”事并见《北史》卷五、《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二。按事在永熙二年(533)。濮阳在今山东鄄城北。以上刘举二事均发生在寇谦之之后,但亦可间接说明北魏时期用刘举名义起义者亦颇有其人,兹姑不论。 据《晋书》所载五条“李弘”的材料,可以看出:(1)从322年到416年前数年,前后不到一百年,东起山东,西至四川、陕西,南到安徽等地,均有人以李弘名义组织农民起义,正如《老君音诵诫经》所言:“称名李弘,岁岁有之。”(2)“李弘”一名当为其时利用道教组织农民起义的代名词。按道教认为得道者可以分身(事见《三国志·吴志·孙策传》,葛洪《抱朴子内篇·祛惑》所言帛和亦类此),此处想必以“李弘”名义来号召群众,故两处言“应谶当王”。而“李弘”又是老子之化名(参见《三天内解经》及《老子变化无极经》等)。(3)《老君音诵诫经》攻击“妖贼”李弘主要之点在其“事合氓庶”,“惑乱万民”,然李弘的道教之所以能“合氓庶”,当因它破坏着农民所反对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坏乱土地”),颠覆着农民所痛恨的政权而自立政权(“称官设号”)。由此可见,其言“李弘”事,如非南北朝时之作品,当不可能说“称名李弘,岁岁有之”。进而若非寇谦之的作品,当不可能有攻击李弘“坏乱土地”、“称官设号”与《魏书·释老志》记载的寇谦之改革道教之主旨相合也。(4)《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中说: 昔汉嗣末世,豪杰纵横,强弱相陵,人民诡黠,男女轻淫。政不能济,家不相禁。抄盗城市,怨枉小人,更相仆役,蚕食万民。民怨思乱,逆气干天。故令五星失度,彗孛上扫,火星失辅,强臣分争,群奸相将,百有余年,魏氏承天驱除,历使其然。载在河雒,悬象垂天。是吾顺天奉时,以国师命武帝行天下,死者填坑。既得吾国之光,赤子不伤。身重金累紫,得寿遐亡。七子五侯,为国之光。……从今吾避世,以汝付魏,清政道治,千里独行,虎狼伏匿,卧不闭门……。 按文中所言“魏”当是“北魏”,从汉末到北魏(220—385)实只有一百六十余年(魏太武帝即位则在424年),故所言“……百有余年,魏氏承天驱除,历使其然”,年代大体相近。我们知道,这些戒经一方面斥起义者及李弘等为“恶人”、“愚民”、“诈伪”、“人人欲作不臣”等等,如上文所诬蔑汉末人曰:“人民诡黠,男女轻淫。政不能济,家不相禁。”但另一方面,文中又歌颂北魏政权,认为魏得政权是上合天意,“载在河雒,悬象垂天”,下应民心,“虎狼伏匿,卧不闭门”。寇谦之“顺天奉时”,出为魏太武帝之国师,在魏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这点和《魏书·释老志》所言寇谦之的行事大体相合。(5)《魏书·释老志》云: 寇谦之……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无效……(老君)使王九疑人长客之等十二人授谦之服气导引口诀之法,遂得辟谷,气盛体轻,颜色殊丽……。 按《老君音诵诫经》第二十七段亦谓靠服食饵药不得长生成仙,而“能登太清之阶”者是因有仙人玉童玉女从天降迎也。故其文曰: 案药服之,正可得除病寿终,攘却毒气,瘟疫所不能中伤,毕一世之年。可兼谷养性,建功斋靖,解过除罪。诸欲修学长生之人,好共寻诸《诵诫》,建功香火,斋炼功成,感彻之后,长生可克。……欲求生道,为可先读五千文,最是要者。 《老君音诵诫经》所言与《魏书·释老志》相同,寇谦之反对“药石”,一则因服食不但不能长生,如不得其正,反有丧生的危险。两晋以来,因服药而丧生者为数不少。又道教长生之术分若干派,“服食饵药”为其一也。寇谦之“清整道教”,于长生修炼之术,亦有修正。“服食饵药”本为“养生”之术,合于早期道教“养身”之主张,然南北朝时佛教大行于中国,道教在养生术方面也颇受佛教之影响,寇谦之的新道教当为例证。寇谦之除主张“服气导引”、“辟谷”(“兼谷养性”)外,又把若干佛教修养的方法引入道教,如认为“持戒修行”、“诵诫”、“造经”可得“成仙”。又《混元圣记》卷三载《老子》书的各种记载,中说:“魏太和中道士寇谦之得河上公本。”元玄巢子《谷神》篇(收在《道藏》光字帙下)亦谓“北魏寇谦之尝集道经”云云。这点也或与《老君音诵诫经》所说“欲求生道,为可先读五千文”不无关系。(6)《女青鬼律》卷六引天师曰: 自顷年以来,阴阳不调,水旱不适,灾变屡见,皆由人事失理使然也。……末世废道,急竞为身,不顺天地,伐逆师尊。尊卑不别,上下乖离。善恶不分,贤者隐匿。国无忠臣,亡义违仁。法令不行,更相欺诈,致使寇贼充斥,洿辱中华,万民流散,荼毒饥寒,被死者半,十有九伤,岂不痛哉!岂不痛哉!乱不可久,狼子宜除,道运应兴,太平期近,今当驱除,留善种人。…… 从这一段话看来,这位天师意在“专以礼法为度”来“清整道教”。他反对“尊卑不别”、“上下乖离”,诅咒“寇贼”,旨在“破除三张伪法”。汉末魏晋以来,颇多战乱,中原人口大减,故“天师”曰:“万民流离,荼毒饥寒,被死者半,十有九伤。” 按今《道藏》力上力下诸诫经,当即为寇氏之著作,而《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当原为这些诫经之总名。然从现存《道藏》力上力下各卷中之诫经残缺不全的情况看,当仅为寇谦之原书的一部分,有的仅存篇目,有的一篇散失大半,文字错落亦复不少,或有后世纂入者,但大体上都保存了原书面目。《云中音诵新科之诫》的成书,当是寇谦之假借“老君”之名传授给他的,所谓“人神接时,手笔粲然”。因为这些东西不一定是一次写成,因此有先有后,文体不一。由于每次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因此其“诫经”的形式与具体内容亦不尽相同。这些就是他和“天神交接”、“天神”借助他的手笔写下来的东西了。 又,《道藏》光字帙下有《谷神》,元玄巢子林辕神风述,文中批评了三种混入道教的思想,以为违道甚远,其二谓:“北魏寇谦之尝集道经,为其书少,遂将方技、符水、医药、卜筮、谶纬之书混而为一。”按道教经书自张道陵、于吉以降,孳乳增益,层叠积累。两晋后,历经道士搜录编纂,卷帙浩繁,内容日趋庞杂,或寇谦之欲张大道教,转亦尝搜集道教,并将“方技、符水、医药、卜筮、谶纬”等混入道经。按南北朝时道教徒为与佛教抗衡编纂书目,《玄都经目》谓“道经传记符图论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云云。北周甄鸾《笑道论》批评说:“道士所上经目,陆修静目中见有经书药方符图止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本无杂书,诸子之名,而道士今列二千余卷者,乃取《汉书·艺文志》目八百八十四卷,为道书之经论,据此状,理有可疑。”可见一斑。而寇谦之编纂书目与《魏书·释老志》所载,尽与寇谦之重视“服食、闭炼”、“服气导引口诀之法”有关。更可注意者,寇谦之于《老子》之注解或颇为留意。宋彭邦《道德经集注杂说》谓:“安丘望之本(《老子》),魏太和中道士寇谦之得之。”又《混元圣记》卷三:“魏太和中道士寇谦之得河上丈人本(《老子》)。”按,安丘望之本即河上公本。故可证《老子》之注本《老子想尔戒》之入于其《老君音诵新科之诫》中,亦非偶然。  道教画像(资料图) 二、对道教的改革 寇谦之建立新道教、改革旧道教,事见《魏书·释老志》,他书如《混元圣记》、《犹龙传》等亦多言及,但大多出于《魏书·释老志》。据《魏书·释老志》并参照他书,可知寇谦之对道教所进行的改革及其新道教的基本内容,大体可分以下数点: 第一,寇谦之建立新道教的目的在于“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以服气闭炼”。 东汉末年以来,农民起义多以道教作为组织群众参加反对官府和地主阶级斗争的形式。据刘勰的《灭惑论》说:道教“事合氓庶,故比屋归宗。是以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卢悚、孙恩,乱盈晋末。……爵非通侯,而轻立民户;瑞无竹虎,而滥求租税”。可见汉末以来,农民起义多以道教为组织形式,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自立政权,自收租税。释玄光《辩惑论》把“制民课输”列为六种极恶之一。释道安《二教论》亦以“制民课输”为张氏妄说。统治阶级对农民的自收租税当然要极力反对,因此一些佛教徒也就抓住这一点对道教进行攻击。寇谦之要改革道教,使其更加符合地主阶级的需要,自要“除去三张伪法”的“租米钱税”了。 《二教论》又说:“自于上代爰至符姚,皆呼众僧以为道士,至寇谦之始窃道士之号,私易祭酒之名。”(释法琳《辩正论》亦引姚书,文略同)“祭酒”本汉末农民起义张角和张鲁政权所立之各级领导之号,《三国志》注引《典略》谓:“(张)修法略与角同……使人为奸令祭酒。”《三国志·魏志·张鲁传》说:“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汉末张角起义、张鲁政权,以祭酒代州官,自立政权,“不置长吏,皆以祭酒治”,故“民夷便乐之”。寇谦之废除“祭酒”之名,主要目的当不在窃取“道士”之名号,而在于“破除三张伪法”的“自立政权”。按寇谦之行事“专以礼度为首”,而视三张所立的政权,使礼法受到破坏,故必除去之。葛洪反对原始道教亦以其不合礼法,引《礼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抱朴子外篇·省烦》)又说:“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废,则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抱朴子外篇·良规》)君臣上下之礼如可废去,那岂不等于说“天”可改变,“父”可换易吗?寇谦之所言之“礼法”不详于《魏书·释老志》,而颇载于《老君音诵诫经》中,如其文说道:“谦之汝就系天师正位,并教生民,佐国扶命”,使道教徒“不得叛逆君王,谋害国家”,说张角、李弘等人“违道叛德”,“攻错经法”,“渴乱清真”,“惑乱愚民”。因此,寇谦之把农民起义描写为:“愚人诳诈无端,人人欲作不臣,聚集逋逃罪逆之人,及以奴仆隶皂之间,诈称李弘,我身宁可入此下俗臭肉奴狗魍魉之中,作此恶逆者哉!”据此,可知其新法的另一目的则在巩固地主阶级的政权,反对三张伪法的自立政权。 寇谦之又反对原始道教的“男女合气之术”。如果说寇谦之反对“三张伪法”的自收租税和自立政权是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那么他反对“三张伪法”的“男女合气之术”则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伦理道德。按:有关“男女合气之术”的记载在早期道教史材料中很难找到。《后汉书·刘焉传》中说:“(张)鲁母有姿色,兼挟鬼道,往来焉家。”故可知当时道教中女子亦可传道,因此原始道教男女界限不甚严格,或亦有之。且道教中三张一派可以在寺院中与其眷属同居,《燕翼贻谋录》中说:“黄冠之教,始于汉张陵,故皆有妻子。虽属宫观而嫁娶生子,与俗人不异。”早期道教并不要求“出家”,而且批评佛教的“去父母,捐家室”,“不好生,无世俗”。按早期道教有“房中术”一派,《抱朴子内篇·微旨篇》中说: 凡养生者,欲令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偏修一事,不足必赖也。又患好事之徒,各仗其所长,知玄素之术者,则曰唯房中之术,可以度世矣;明吐纳之道者,则曰唯行气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则曰唯导引可以难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则曰唯药饵可以无穷矣,学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 可见早期道教或有此“房中术”一派,因此葛洪在《释滞》篇中也说:“一涂之道士,或欲专守交接之术,而不作金丹之大药,此愚之甚矣。”据《弘明集》卷八释玄光《辩惑论》“合气释罪三逆”条注谓: 至甲子诏冥醮录,男女媟合,尊卑无别,吴陆修静复勤勤行此。 这就说明,所谓“男女合气之术”并非为“三张伪法”之特有,而与早期道教均有关系。査今《道藏》中有关“房中术”之撰述有许多种,这是因为道教重“养生”,而视“房中术”有益于养生也。但道教“男女合气之术”或与“留善种人”有关。按在早期道教中有所谓“种民”,“种民”或即为“男女合气”所产生者,如《上清黄书过度仪》中说: 谨按师法与甲共奉行道德三五七九之化,阴阳之施,男女更相过度。……愿令臣等长生久视,过度灾厄,削除死籍,更著生名玉历,为后世种民辈中,以为效信。 据此推想,“种民”则是“天生的道教徒”。所以在《老君音诵诫经》中也说:“其有祭酒道民,奉法有功,然后于中方有当简择种民,录名文昌宫中。”由于早期道教有这种“男女合气之术”,在实行中就会发生种种问题,以致破坏伦常关系,所以北周和尚甄鸾在《笑道论》中有如下之记载: 又道律云:“行气以次,不得任意排丑近好,抄截越次。”又玄子曰“不鬲戾,得度世;不嫉妒,世可度;阴阳合,乘龙去”云云。臣笑曰:“臣年二十之时,好道术,就观学。先教臣黄书合气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两舌,正对行道,在于丹田。有行者度厄延年。教夫易妇,唯色为初。父兄立前,不知羞耻,自称中气真术,今道士常行此法,以之求道,有所未详。” 甄鸾的这段话不见得都合乎事实,但总也多少反映早期道教的某些实际情况。(按:早期道教男女往来较自由,《后汉书·刘焉传》谓:“(张)鲁母有姿色,兼挟鬼道,往来焉家。”《三国志·魏志·张鲁传》注引《王恭传》谓:“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之术,常衣黄衣,状如天师,王甚悦之。”)从这方面看,寇谦之反对“男女合气之术”,应是针对“三张伪法”违背伦常关系而发的,故认为其当在“清除”之列。 总之,以上所言可以看出寇谦之的新道教以反对农民起义利用道教为目的,他所攻击的主要之点即在“三张”之“租米钱税”和“男女合气之术”,这是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经济利益和维护封建的伦理道德。道教自葛洪到寇谦之、陶弘景等,逐渐完成了它的“改革”任务,使原来在一定程度上能为农民起义所利用的原始道教变成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 第二,寇谦之的新道教企图把北魏政权建成一政教合一的机构,以巩固封建统治。《魏书·释老志》中说: 谦之守志嵩岳,精专不懈,以神瑞二年(415)十月乙卯,忽遇大神,乘云驾龙,导从百灵,仙人玉女,左右侍卫,集止山顶,称太上老君,谓谦之曰:“往辛亥年,嵩岳镇灵集仙宫主,表天曹,称自天师张陵去世以来,地上旷诚,修善之人,无所师授。嵩岳道士上谷寇谦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轨范,首处师位,吾故来观汝,授汝天师之位,赐汝《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号曰并进。”言:“吾此经诫,自天地开辟已来,不传于世,今运数应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大道清虚,岂有斯事。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炼。” 寇谦之所创造的新道教,事非偶然,按上引文所言,自张道陵以后,从封建统治者的观点看来,信道教的多非“修善之人”,常为农民起义所利用。汉末以来,不少统治者已经看到道教这种为农民起义所利用的可能,因此他们一方面对道教采用限制和控制的办法,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仅仅用限制和控制的方法是不行的,因此还对原始道教采取改造的办法,以改变其某些内容,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汉桓帝时,襄楷上《太平经》,其目的就是要求当权的统治者来利用道教。但由于当权的统治者一方面还没有认识道教作为宗教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因《太平经》内容庞杂,不完全适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因此未被采用。在三国西晋时,当权的统治者虽然用了多种方法限制道教,使道教势力有很大削弱,但是一种宗教产生了并为时代所需要,用政权限制的办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道教仍然在民间流行,而为农民革命所利用。因此,从东晋以后,当权的统治者开始采取利用道教的办法,从原始道教中清除其不利于维护封建统治部分,所以据史书记载上说:汉末以来“从受道者,类皆兵民,胁从无知名之士,至晋世则沿及士大夫矣”(《三国志·魏志·张鲁传》注引)。而且由于宗教本身的消极作用,它总会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到南北朝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道教形成的客观形势已经存在,孙恩、卢循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已经失败,统治者深惧农民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道教,因此“清整道教”已是刻不容缓的事了,故《魏书·释老志》说,寇谦之的新道教是“运数应出”。 寇谦之时,北朝社会较为安定,崔浩当时颇有改革政治的野心,《魏书·卢玄传》说: (崔)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 寇谦之为崔浩所信任,推荐给魏太武帝,据《魏书·释老志》说: 世祖即位,富于春秋,既而锐志武功,每以平定祸乱为先,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 寇谦之与崔浩之间虽有宗教上的关系,但他们之间主要是政治上的关系。他们都想利用宗教来实现其政治理想,即利用“礼法”来“齐整人伦,分明姓族”。故《魏书·崔浩传》说: 天师寇谦之每与浩言,闻其论古治乱之迹,常自夜达旦,竦意敛容,无有懈倦。既而叹美之曰:“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当今之皋繇也。但世人贵远贱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谓浩曰:“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泰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而学不稽古,临事暗昧。卿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浩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迹,大旨先以复五等为本。 寇谦之和崔浩都是有抱负有野心的政治家,他们实际上都是想用儒家的“礼法”思想来治理天下,使皋繇治世的绝统得以继承。因此寇谦之让崔浩研究总结自古以来的统治经验,他提出“学不稽古”则“临事暗昧”。但是采取什么形式来实现其治世的理想呢?寇谦之企图把道教定为国教,建立一政教合一的国家,所以他是以“辅助泰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为己任的。(按:魏太武帝之所以称“泰平真君”,其原因之一为因太武帝继位前封为“泰平王”)《魏书·释老志》谓: 真君三年,谦之奏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未之有也。应登受符书,以彰圣德。”世祖从之。于是亲至道坛,受符箓。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家之色也。 按寇谦之的道教之得以推行,全赖当权统治者的信奉。魏太武帝虽明知道教的某些行事具有欺骗性,但他仍然要利用道教,当非偶然,故《魏书·释老志》载曰: 恭宗见谦之奏造静轮宫,必令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功役万计,经年不成。乃言于世祖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谦之欲要以无成之期,说以不然之事,财力费损,百姓疲劳,无乃不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东山万仞之上,为功差易。”世祖深然恭宗之言,但以崔浩赞成,难违其意,沉吟者久之,乃曰:“吾亦知其无成,事既尔,何惜五三百功。” 魏太武帝虽知所建之静轮宫“与神交接”未必可信,但利用道教则是必要的,可见寇谦之所创立的新道教已完全符合当权的统治者的要求了。 寇谦之利用政治力量统一道教,宣扬新科,以儒家礼法充实道教之内容,以佛戒律为其形式,把宗教戒律宣布为法律的信条,故其《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实可成为道教国家之法典也。按佛教戒律至南北朝已大行于中国,《十诵律》已传入,并盛行于关中。任何戒律对于信其教的人,都是带有强制性的,因此寇谦之用宗教戒律来补充和加强国家法令,这样的戒律就可以起双重作用,即强制的作用与信仰的作用,并可把强制的作用建立在信仰的作用基础上,以便人们不易察觉强制作用的强制性。按上文所言,今本《道藏》中的《老君音诵诫经》等,当即《魏书·释老志》中所言之《云中音诵新科之诫》杂以道教修身成仙之术,并吸收若干佛教戒律之条文也。 总而言之,魏太武帝身为国君又披上道教领袖的外衣“泰平真君”,寇谦之是道教教主又充当北魏朝廷的“国师”,且太武帝登坛受符箓,以彰圣德,所用全系道教仪式;谦之造戒律,用宗教信条补充国家法律,以巩固封建王朝,又前引《女青鬼律》更可证寇谦之这位天师意欲利用道教“拯救”天下。故可知寇谦之企图建立一政教合一的政权,当可信也。 第三,寇谦之与佛教的关系。据各种史料看,寇谦之并不反对佛教,且颇欲借助于佛教,至于他之所以与佛教对立,纯系因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种种矛盾关系所致,因之使他始终未能制止排佛活动。 魏太武帝毁佛法之事,多系出于崔浩之意,寇谦之并不赞同。据《魏书·释老志》所载,关于太武帝毁法事如下: ……会盖吴反杏城,关中骚动,帝乃西伐,至于长安。先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驺牧马于麦中,帝入观马。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便室,见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闻,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屈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帝既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始谦之与浩同从车驾,苦与浩诤,浩不肯,谓浩曰:“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 法琳《破邪论》及道宣《古今佛道论衡》亦载此事。后二者当均根据《魏书·释老志》,都是从佛教的立场叙述了这一事实,当可证明事不会假。 寇谦之不反对佛教,不仅因其所创立的新道教在理论上和形式上颇受佛教的影响(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一文谓,寇谦之所遇之仙人成兴公“与当时佛教徒有密切之关系也”),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是从政治上来考虑这一问题。他深知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不仅不利于统治阶级政权的巩固,而且往往会对被统治者有利。所以寇谦之建立新道教的目的很明确,不是在排佛,而是在“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他和崔浩的结合虽与宗教有关,但主要都在于他们主张“齐整人伦”,“以礼度为首”。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寇谦之曾向牧士上师问及“幽冥之事”,牧士“一一告焉。《经》云:‘佛者,昔于西胡得道,在三十二天,为延真宫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断绝人道,诸天衣服悉然。’”可见并无诋诽佛教之意。寇谦之从统治阶级立场出发,深知当时的社会矛盾主要是地主阶级和广大农民之间的矛盾,因此主张与统治阶级中其他集团妥协,没有必要排斥佛教,然崔浩不听,终遭杀身之祸。 崔浩排佛,纯系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集团之间的斗争,自不待言。然而为什么寇谦之身为道教之领袖反而不排佛,崔浩为当时儒家思想的提倡者反要排佛呢?我们必须懂得,寇谦之与崔浩虽然都想利用宗教来实现他们政治改革的目的,其目标在主要方面也是一致的,“齐整人伦”,但是崔浩较之寇谦之更多地注重了民族问题,他的改革目的之一也企图通过排佛的活动来巩固汉族豪门大族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因此形成了与鲜卑族大族长孙嵩之间的尖锐矛盾,然而寇谦之的重点是放在改革道教本身,建立一个完全可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宗教团体,因此没有更多地去注意民族之间的矛盾(参见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查《道藏》中《老君音诵诫经》等亦未见对佛教诋毁的言论。相反,从《老君音诵诫经》等著作内容看,寇谦之所受佛教影响至为明显,其戒律之形式当取自佛教之戒律;上述各种戒经中多有取佛教之意者,如“十善十恶”、“六尘六识”、“因缘轮转”、“生死轮转”、“读经斋戒”、“道士世尊”等等,这些内容在南北朝以前的道教经典中较为少见,当然这些内容或有为后世辗转传抄中纂入者,但从寇谦之的整个思想看,受佛教影响最主要之点当在“生死轮回”的问题上。 道教本来主要讲“长生不死”、“肉体飞升”,不讲“灵魂不死”,更无“轮回”的思想。然而寇谦之却把与道教养生成仙的理论相对立的“轮回”思想引入了道教,原来道教和佛教在生死和神形问题上的看法是有着根本不同的(参见汤一介:《略论早期道教关于生死、神形问题的理论》,《哲学研究》,1981(1))。在神形问题上,佛教提倡“灵魂不死”;而道教提倡“肉体飞升”,故佛教主养神,道教主炼形。在生死问题上,佛教主张涅槃寂静,故求永灭,超脱轮回;道教主张无死入圣,故求永生,长生不死。佛教养神,入于涅槃境界,当依觉悟;道教养形,入于仙境,当靠积功。寇谦之在这些问题上虽然还没有离开道教的基本立场,但由于实际上,道教求“长生不死”、“肉体飞升”之不可得,因此他根据佛教若干理论,特别是有关轮回的思想为他的新道教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1)道教主张养形,本注重今世之修炼,但寇谦之把轮回观念引入道教,认为前世对今生的修炼颇有影响,《太上老君戒经》中说:“本得无失,谓前身过去已得此戒,故于今身而无失也。”又如《老君音诵诫经》中说:“死入地狱,若转轮精魂虫畜猪羊,而生偿罪难毕。”这显然是受佛教的“六道轮回”的思想影响而有。(2)寇谦之认为,只靠炼形养生不一定就能成仙,成仙之首要在于积有善功。(3)养生之术虽在“服食闭炼”,但靠“诵经万遍”亦得“白日登晨”(《太上老君戒经》)。(4)寇谦之认为成仙不待外求,主要靠自己,证得大智慧,持上品大戒,也可以成仙,所以《太上经戒》中说:“故有道之士,取诸我身,无求乎人;道言修身,其德乃真,斯之谓也。夫学道不受大智慧,道行本愿,上品大戒,无缘上仙也。”这些思想本与道教的思想不相合,但寇谦之为了建立他的新道教,补充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在思想理论上的不足,就把它们生硬地拉扯在一起,这只能说明他在理论上尚未能解决佛教和道教在生死神形问题上的根本不同。稍后,南朝的陶弘景也想在这个问题上结合佛道,同样没有成功,直到他临死前所作的《告游》一诗仍然反映出这一矛盾。可见佛教和道教虽然都主张“出世解脱”,但是由于立足点不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难以调和。 崔浩与寇谦之不同,他本身并非道教的宗教领袖,他并不关心道教本身的理论和教规教仪,而是作为一政治家来利用宗教,使之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因此崔浩和寇谦之的关系有似一阶级的政治家与思想家的关系。崔浩的主张往往更多地受到现实的政治斗争的影响,与其自身的政治上的利害关系至为密切,在北魏太武帝在位时不是崔浩成为政治上的领袖,就是长孙嵩成为当时的政治领袖。《魏书·穆崇传》中说:“高祖曰:世祖时,崔浩为冀州中正,长孙嵩为司州中正,可谓得人。”在封建社会的统治集团中,两雄并立,必伤其一。故崔浩推尊道教,反对佛教,是和他反对长孙嵩相联系的,是势在必行,不得不然。据《魏书·长孙嵩传》记载: 世祖即位……诏问公卿,赫连、蠕蠕征讨何先。……尚书刘洁、武京侯安原请先平冯跋。帝默然,遂西巡狩。后闻屈丐死,关中大乱,议欲征之。(长孙)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劳,大檀闻之,乘虚而寇,危道也。”帝乃问幽微于天师寇谦之,谦之劝行,杜超之赞成之,崔浩又言西伐利。嵩等固谏不可。帝大怒,责嵩在官贪污,使武士顿辱。 又《魏书·崔浩传》记载崔浩对长孙嵩的评论说: 长孙嵩有治国之用,无进取之能,非刘裕敌也。 可见崔浩和长孙嵩之间确存在势不两立之矛盾也。寇谦之虽与崔浩一起进行政治改革,但他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家,就可以更多地考虑他的阶级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并企图用宗教的力量把他的那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巩固下来。因此,他反对把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放在第一位,而主张集中力量改革道教,实现其政教合一的理想,使农民不能再利用道教来危害封建统治,因此在《老君音诵诫经》有下列一段: 今世人恶,但作死事,修善者少,世间诈伪,功错经道,惑乱愚民。但言老君当治,李弘应出。天下纵横返逆者众,称名李弘者岁岁有之。其中精感鬼神,白日人见,惑乱万民,称鬼神语,愚民信之。诳诈万端,称官设号,蚁聚人众,坏乱土地,称刘举者甚多,称李弘者亦复不少。吾大嗔怒,念此恶人,以我作辞者乃尔多乎? 可见寇谦之的思想感情完全集中在对付“叛逆之人”上,而且企图借教主身份,呵斥那些“不肖之徒”。他看到这些“叛逆者”利用道教破坏了封建制度,自己建立了政权,“称官设号”;剥夺了地主阶级的土地,“坏乱土地”;搞乱了伦常关系,行男女合气之术。因此,寇谦之以改革道教为己任,这说明他更能从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方面来考虑问题。道教经东晋以来葛洪、陆修静、寇谦之、陶弘景等人的改革,与原始道教相比已有很大不同,而更加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了。 综观上述各点,当可明寇谦之的新道教的目的和基本内容。向来治史者多注意寇谦之与当时佛教的斗争,认为魏太武帝灭佛法之因在于寇谦之要兴盛道教,殊不知寇谦之并不怎么反对佛教,其建立新道教的目的是在于巩固封建统治,使之更加适合统治阶级的要求,实现他所企图建立的政教合一的封建王朝。 第四,寇谦之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寇谦之为北方之豪宗大族,其兄寇赞“少以清洁知名”,重儒术,《北史》本传谓其“姿容严嶷,非礼勿动”。《魏书·崔浩传》记载,寇谦之常与崔浩论古治乱之道,《北史·崔浩传》略同,谓: 天师寇谦之每与浩言,闻其论古兴亡之迹,常自夜达旦,竦意敛容,深美之,曰:“斯人言也惠,皆可底行,亦当今之皋陶也。但人贵远贱近,不能深察耳。”因谓浩曰:“吾当兼修儒教,辅助太平真君,而学不稽古。为吾撰列王政典,并论其大要。” 可见寇谦之对儒家思想颇为重视,而且他认为应把儒家的理想实现于现实社会之中。 寇谦之的新道教实为儒、释、道三家思想的产物,其形式虽为道教的形式,但其内容多为儒家的礼法、佛教的戒律,并且吸收了某些当时流行的以老庄思想为中心的玄学思想。 自葛洪以来,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就企图系统地以儒家礼法改革道教,充实道教的内容,寇谦之在这方面则更有所发展。他企图使封建主义的礼法宗教化,成为宗教信条。根据《道藏》力字帙各种经戒所包含的内容看,多为封建主义的礼法,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制,论证“公侯卿相伯子男”的“封土”的合理性,攻击农民起义“坏乱土地”、自收“租米钱税”,在《老君音诵诫经》中说:“从(张)陵升度以来,旷官寘职未久,不立系天师之位……惑乱百姓,授人职契箓,取人金银财帛,而治民产,恐动威逼,教人颐,匹帛牛犊奴婢衣裳,或有岁输全绢一匹,功薄输丝一两。众杂病说,不可称数。” (2)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权机构,“不得叛逆君王,谋害国家”、“于君不可不忠”。被统治者不得使用暴力造反,攻击领导起义、推翻封建统治政权、“称官设号”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并辱骂这些造反者为“臭肉奴狗魍魉”。 (3)巩固贫富贵贱的封建等级制度,提出“戒勿以贫贱求富贵”,而要求种民“勿怨贫苦,贪富乐尊贵”。 (4)巩固封建的伦常关系,如言“不得违戾父母师长”,处处皆是。《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中所载奉道不可行之事二十五条,其中有十六条是为巩固封建伦常关系所设,如说“诸欲奉道不可不勤,事师不可不敬,事亲不可不孝,专君不可不忠”等等。故寇谦之以其道教严戒“败乱五常”之事,并曰:“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内无二心,便可为善得种民矣。” (5)为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礼法范围之内,因此寇谦之认为那些反对封建统治思想的言论是“惑乱愚民”的“诈伪邪说”,那些书籍是“伪书”,是“切坏经典”,“攻错经道”,而他提出的戒经则是“教生民佐国扶命”的“大道”,故其科律能使“诸男女……心身开悟”。 从以上五点看,寇谦之的思想是很明显地吸收了儒家的某些思想内容。不仅如此,他还把道教的“中和”思想和儒家的“中和”(“中庸”)思想结合起来,作为他上述巩固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按“中和”思想要求统治者对老百姓采用“威猛”和“宽惠”的两手,因而老百姓则应安分守己,不逾礼法,不能对统治者采取“过激”的行动。为此,寇谦之提出“主人”对其奴婢不得任意“纵横扑打”;但是奴婢有“过”,主人要告诉他们,做此事应受罚,然后要奴婢“自愿”受杖,而且不得“有怨恨之心”(按:《笑道论》中亦言及道教主张奴婢受杖“不得怀恶心”)。《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中说: 道以冲和为德,以不和相克。是以天地合和,万物萌生,华英熟成;国家合和,天下太平,万姓安宁;室家合和,父慈子孝,天垂福庆。贤者深思念焉,岂可不和!天地不和,阴阳失度,冬雷夏霜,水旱不调,万物干陆,华叶焦枯。国家不和,君臣相诈,强弱相陵,夷狄侵境,兵锋交错,天下扰攘,民不安居。室家不和,父不慈爱,子无孝心,大小忿错,更相怨望,积怨含毒,鬼乱神错,家致败伤。此三事之怨,皆由不和……善积合道,神定体安。 在《太平经》中也多言“中和”思想,如说:“中和者,主调和万物者也。”(《太平经钞》乙部)然寇谦之则把“中和”思想更紧密地和维护封建统治联系起来。他认为,破坏封建统治的根本原因在于上下“不和”,这些“不和”之产生是由于在下者不安于位,因此才有“坏乱土地”、“称官设号”、贫者欲富、颠倒伦常、诈伪乱真等等思想和行为。而寇谦之认为他的任务就是要利用宗教的力量来调和阶级矛盾,以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寇谦之的理论也受到当时流行的玄学的影响,魏晋以来所讨论的“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对寇谦之来说当然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道教要求“出世”,当主“自然”,而寇谦之却要建立一政教合一的政权,必依“名教”。因而他在解决“名教”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和郭象的观点大体相近。在《太上老君戒经》中说: 夫上士学道在市朝,下士远处山林。山林者,谓垢秽尚多,未能即喧为静,故远避人世,以自调伏耳。若即世而调伏者,则无待于山林者也。 又《太上经戒》中说: 十善遍行谓之道士,不修善功徒劳山林。…… 寇谦之对山林与朝市的看法和郭象对“名教”与“自然”的看法一样,郭象说: 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庄子·逍遥游》注) 与郭象约同时的辛谧在《遗冉闵书》中也说: 昔许由辞尧以天下让之,全其清高之节。伯夷去国,子推逃赏,皆显史牒,传之无穷,此往而不返者也。然贤人君子,虽居庙堂之上,无异于山林之中,斯穷理尽性之妙,岂有识之者耶。 正是这样,寇谦之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机构的构想才有了理论根据,身为道士的寇谦之虽身在“朝市”,为魏太武帝的国师,亦能调心制性,为道教教主,以求长生不死,因而宗教的王国也就可以在现实的王国中实现了。  本文作者:已故著名学者汤一介先生 三、为道教建立教规教仪 宗教虽然不就是一套仪礼,但仪礼却可以表示一部分宗教观念。如基督教有所谓“洗礼”、“圣餐”等仪式。接受了洗礼的人才可以算是基督教徒。佛教也有许多教仪,入教当和尚要举行受戒的仪式,叫受具足戒,还有诵经的仪式、坐禅的仪式和法会的仪式等等。道教原来也有一些简单的且不大固定的仪式,如有所谓“请祷之法”,人有病或有过错,就由祭酒(道教组织的神职人员)把这个人的名字写在纸上,并说明他的病状或说明他认错了,然后把写好的一份送到天上(即高山上),一份埋入地下,一份沉入水中,以求免祸得福。但那时这种仪式不仅简单,而且对神秘主义的宗教来说显然也很不完备。佛教到东晋后,不仅翻译了大量的“经”,而且把佛教的“戒律”也翻译过来了。东晋以来,《十诵律》、《四分律》、《僧祇律》都有了译本,这就说明佛教的戒律大部分都被译出来,而广为流传了。因此,到寇谦之时在佛教的影响下,他为了“清整道教”,为道教建立了一套较完备的教仪,现分别叙述于下: 1.奉道受戒的仪式 据《老君音诵诫经》谓: 老君曰:烦道不至,至道不烦,按如修行。诸男女官见吾诵诫科律,心自开悟,可请会民同友,以吾诫律著按上,作单章表奏受诫。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道官箓生初受诫律之时,向诫经八拜,正立经前。若师若友,执经作八胤乐音诵。受者伏诵经意,卷后讫后(按:吴世昌谓“后”当作“复”)八拜止。若不解音诵者,但直诵而已。其诫律以两若(按:杨联陞谓:“若”疑当作“函若”)相成(按:“成”当作“盛”)之。常当恭谨。若展转授同友及弟子,按法传之。明慎奉行如律令。 这两段的意思是说:无论男女如果看到了《老君音诵诫经》,使他觉悟到应该信奉道教,就可以找已入道的人请他们向道官(即祭酒之类)说明愿意按照“诫律”的要求受戒奉道。在举行受戒的仪式时,开始向《诫经》行八拜之礼,然后正立《经》前。接着由参加仪式的师友,捧着《诫经》用“八胤乐”朗诵(按“八胤乐”未详,或即“八音乐”,阮籍《乐海》:“昔圣人之作乐也……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阴阳八风之声。”中国古代乐器有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作八胤乐音诵”或是由乐器伴奏朗诵)。然后由受道者伏地用一种特殊的腔调朗诵《诫经》的内容,完毕之后再行八拜之礼,就算完成了入道仪式,如果不会“音诵”的,“直诵”(即读出经文)。《诫经》用两个相套着的盒子盛着,要对它十分恭敬谨慎。 2.求愿时所行的仪式 “求愿”有两种,一为厨会求愿,一为烧香求愿。 厨会求愿:就是举行一种斋会(施舍之会)来祈求消灾降福。而厨会又有三种。上斋行会七日,中斋行会三日,下斋行会一夜一日。斋会的方法是,素饭菜,一日食米三升,房室、五辛、生菜、诸肉尽断,勤修善行,就会时向香火行八拜之礼(按:《陶隐居内传》谓:“佛堂有像,道堂无像。”或因其时道教尚无悬像事,故向香火行礼拜),并说明求愿的人所请求的内容(如免除病痛、原谅过错)以及举行这次厨会的要求等等。然后请“大德精进之人”(道教中德高望重的人)坐在首座上,把做好的饭用饭盘送上,一般共有三道菜饭:第一道是小食(小菜,为喝酒用),中间一道为酒,最后上饭。这种求愿的斋会一般在求愿者的家里进行。 烧香求愿:求愿者要在自己家中设一靖舍(深闲的馆舍)。烧香求愿者先到靖舍,站在东面向上恳切地上三炷香,然后行八拜礼,脱帽九叩头,三搏颊(按:据汤用彤先生《读太平经书所见》注二七谓:“搏颊不知即《太平经》所言之叩头自搏否?《弘明集》七宋释僧愍《戎华论》斥道教云:‘搏颊叩齿者,倒惑之至也。’是搏颊之事南北朝道士犹行之。”《辩正论》卷二引《自然忏谢仪》云:“下谢东卿无极世界五岳四渎神仙正真九叩头九搏颊也。”故叩头、搏颊似为二事。又陆修静《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中有:“礼拜叩搏,每事尽节。”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中有:“各叩头搏颊”,“长跪大谢,弟子叩头,搏颊无数”。可见“搏颊”是早期道教谢罪忏悔的一种形式),在行了这种礼节之后,就把自己祈求的事加以阐说,请求“过罪得除,长生延年”。然后再上香求愿说自己的三宗五祖七世父母等以前死去的那些人,使他们免离苦难,得在安乐之处。再上香求愿现在活着的家中大小平安和富足。甚至还要上香求愿“仕官高迁”、“县官口舌疾病除愈”等等。一愿一上香。在这个斋日要于六个不同的时辰上香。 “靖舍”又称“靖室”,《老君音诵诫经》谓:“靖舍外随地宽窄,别作一重篱障,壁东向门,靖主人入靖处,人及弟子尽在靖外。香火时法,靖主不得靖舍中饮食,及着鞋袜,入靖坐起言语,最是求福大禁。”陆修静的《道门科略》也对“靖舍”作了详细说明:“奉道之家,靖室是至诚之所。其外别绝,不连他屋。其中清虚,不杂余物。开闭门户,不妄触突。洒扫精肃,常若神居。唯置香炉、香灯、章案、书刀四物而已。” 3.为死亡人请祈的仪式 道官道民有死亡,在七天内办完丧事。家中要为死亡的人散其生时的财物而举行斋会。参加人可多可少,非道民也可以参加。在为死亡的人设斋会烧香时,道官一人在靖坛中正东向,箓生(司仪者)和主人也东向,各行八拜九叩头九搏颊,共三遍而止。如果参加的人很多也可以坐着,行礼时再起而叩头。主人口称官号姓字,并向无极大道禀启,要多次上香,为亡者解罪过。当一切仪式行完之后,靖主要为主人求愿收福。客人离开时要向靖舍八拜等等。 4.为消除疾病祈请的仪式 道民家中有人得病,可以把道官(师君)请到家里来,师君先让道民在靖舍中点燃香火,道民在靖舍外面西向散发叩头,把病状写在纸上,请求宽恕,使所患疾病痊愈,然后再按照规定行礼。 5.为宥过的祈请仪式 道民因不慎而犯法或其他过错,先要计算应罚多少钱,并让其归还受害者,然后用举行厨会的办法来请求免除过错。做会时,先由主人向香火八拜九叩头,三十六搏颊,共三次;然后再拜,并用手捻香放入香炉中,同时说明自己因无知而犯过错,请求宽宥,并愿出钱做厨会,请参加者证明,以后不敢再犯。 6.三会仪式 按道教有所谓“三元会”,南朝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为三会日(参见陆修静:《陆先生道门科略》),唐朝以正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十五日为三元日,这三天道民要举行斋会。在上述三元日时,道民要到他们所属的“治”(道教的一级教区)举行集体的斋会。开始在靖舍前面送上章籍(道民的祈祷词),正立在南面,面向北面,并且各就各位,排列好队伍,八拜九叩头九搏颊,然后再拜伏地,这样送章籍的仪式就算完成了,于是大家互相祝贺。 还有其他一些教仪,就不一一列举了。举行这样一些仪式的意义对于宗教来说,一方面是增加宗教的神秘性和庄严性;另一方面也是要求教民对教会服从,所以在每种教仪规定的最后都有一句“明慎奉行如律令”,要求道民非常谨慎小心地奉行这些教仪,应如奉行法律和法令一样。 寇谦之除制定了若干道教的仪式之外,还为道教制定了一套教规。从他所制定的教规看,既有大量儒家所要求维护封建统治的礼教,如三纲五常之类,又有不少从佛教戒律中吸取的东西,如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等,但也有一些是应属于道教作为一种特殊宗教所有的教规。下面举两种戒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在《道藏·洞神部·戒律类》中有《道德尊经想尔戒》和《道德尊经戒》两种,这两种戒律是否寇谦之的作品很难确定,但它们是早期道教的戒律当无疑问,故很可能为寇谦之吸收到他的《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中。《道德尊经想尔戒》当和《想尔注》有关,其全文如下: 行无为,行柔弱,行守雌勿先动(此上最三行); 行无名,行清静,行诸善(此中最三行); 行无欲,行知止足,行推让(此下最三行)。 此九行二篇八十一章,集会为道舍,尊卑同科,备上行者神仙,六行者倍寿,三行者增年不横夭。 这里无非是把老子《道德经》中的“无为”、“无名”、“无欲”、“柔弱”、“守雌”、“清静”、“知止足”等等内容抽出作为戒律,并认为能行上行者可以成神仙;能行中行以下者可以使寿命延长一倍;行下三行者可以增加寿命而不夭折。这些戒律内容都比较多地表现了道教的特点,一是取自《道德经》,二是可以长生或增寿。而且从戒律的内容看,它应是道教较早的作品,因为从内容上看它还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也还没有杂入儒家思想。 《道德尊经戒》共二十七条,分上、中、下,各九戒,其中大部分属“少思寡欲”之类的道家的要求,但已吸取了若干儒家思想内容,如“勿以贫贱强求富贵”等,不过也还看不出佛教戒律的明显影响,而其中有几条戒律作为道教的戒律则是有代表性的: 戒勿费用精气; 戒勿为伪彼(按:当作“技”字); 戒勿忘道法。 这三条是在最上九戒之中。列于二十七条之后也有如下一段: 此二十七戒,二篇共合为道渊、尊卑通行,上备者神仙,持十八戒倍寿,九戒者增年不横夭。 看来《道德尊经戒》当为《想尔戒》变化而成,故和《想尔注》有密切关系。 按:《想尔注》中有多处批评“伪伎”,如说: 人等当欲事师,当求善能知真道者,不当事邪伪伎巧,邪知骄奢者。 按:“伪伎”当为“邪伪伎巧”之省文。又如:对“载营魄抱一能无离”的注说: 魄,白也,故精白,与无同色,身为精车,精落故当载营之。神成气来,载营人身,欲全此功无离一。一者道也,今在人身何许?守之云何?一不在人身也,诸附身者悉世间常伪伎,非真道也;一在天地外,入在天地间,但往来人身中耳,都皮里悉是。……世间常伪伎指五脏以名一,瞑目思想,欲从求福,非也,去生遂远矣。 又有如: 道至尊,微而隐,无状貌形象也。但可从其诫,不可见知也。今世间伪伎指形名道,令有服色名字、状貌、长短,非也,悉邪伪也。 世间伪伎,不知常意,妄有指书,故悉凶。 真道藏,邪文出,世间常伪伎称道教,皆为大伪不可用。 《想尔戒》之“勿为伪伎”当来自《想尔注》。盖《想尔注》中虽已把“道”人格化,但反对把人格化之“道”视为有形象可见、有尺寸可量以及有名号可呼(陈世骧《〈想尔〉老子道经敦煌残卷论证》已论及)。但以为“道”有“姓字服色”以及长短等等见于葛洪之《抱朴子内篇·地真》,而葛洪这一思想又是来源于《太平经》,如有说“神长二尺五寸,随五行五脏服饰”。此恰为《想尔注》所批评之观点。这正说明,由于道教中之不同派别对“道”的性质的不同了解,而有不同之戒律也。至于“勿费精气”实亦见于《想尔注》中,如说“宝精勿费”,“人之精气满脏中,苦无爱守之者,不肯自然闭心而揣搅之,即大迷矣”等等。 寇谦之不仅制定了道教的教规,而且还说明了一种宗教需要戒律的原因。他认为,第一,宗教有了戒律才可以使奉道的人成为有“道德之人”,他假借老君的话说:“老君曰:人生虽有寿万年者,若不持戒律,与老树朽石何异?宁一日持戒为道德之人而死补天官,尸解升仙。世人死有重罪,无益鬼神,神鬼受罪耳。”(《老君音诵诫经》)第二,因为“道”的性质是“无为”,人应效法“道”,用戒律约束自己,不做“有为”的贪利之事,如他说:“诸贤者欲除害止恶,当勤奉教戒,戒不可违,道以无为为上。人过积(按,意谓“人的过错积累起来”),但坐有为,贪利百端。道然无为,故能长存;天地法道无为,与道相混;真人法天无为,故致神仙。”(《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 寇谦之为道教建立比较完整的教规教仪,并不是说在他以前道教就没有教规教仪,而是说在这以前道教的教规教仪不如寇谦之所建立的那么完整。当然寇谦之之所以能建立比较完整的道教的教规教仪也正是他吸取了前此已有的不大完整的规仪而加以完备化的。寇谦之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道教的规仪,也说明这时道教不仅有可能来建立一套教规教仪,而且也有必要了。从必要方面说,寇谦之看到了宗教的作用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宗教可以起道德教化的作用。道德问题是古代人们精神上最容易困惑的问题之一,所以宗教必须同时作为一种伦理学说,才能发挥它从精神上给人们一种慰藉的作用,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广义的而且当然是在确切得多的意义上的宗教,实际上只有当社会人为了自己的道德或一般地为了自己的行动和设施开始向神或诸神寻求恩准的时候才产生的。”(《评弗·吕根纳的一本书》,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道教要成为一种完备意义的有影响的宗教团体,在它有了一定的教会组织和较完备的教义理论之后,就不能不建立起维护其教会组织和约束其教徒行为的教规教仪。这些教规教仪对教徒来说不仅有强制作用,而且有劝善止恶的道德教化作用。 *原标题《汤一介:为道教建立比较完备的教规教仪的思想家寇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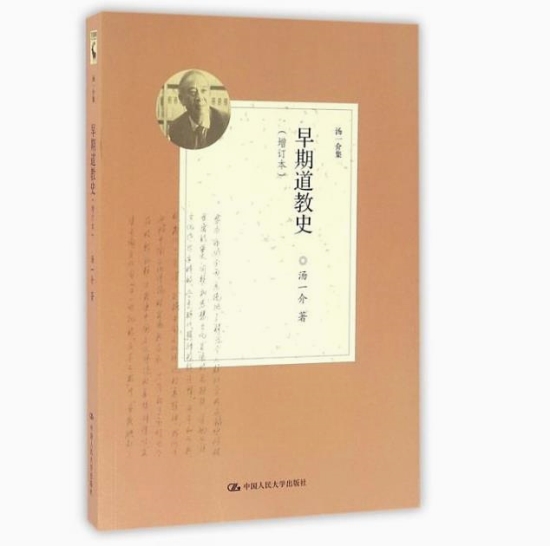 本文来源“学衡”公众号(the-critical-review),原载于《汤一介集·早期道教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图片为编者加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