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瑜:新的中国通史新在何处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1:11:15 国学网 newdu 参加讨论
 赵世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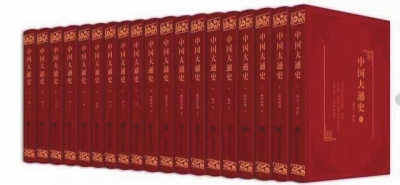 《中国大通史》,学苑出版社出版 “从太史公作《史记》以来,修撰通史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大通史》总主编之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先生在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说。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进入一个发展时期,但在20世纪末《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出版之后,再无新的大型中国通史出版。于是,由我国史学界权威学者倡议,180余位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著名学者参与的《中国大通史》撰著计划启动了。这一次,历史学家曹大为、商传、王和以及赵世瑜,共同担纲总主编,各卷分为综述与治乱兴衰、经济、国家控制、社会结构、精神文化、社会生活6编,以专题形式叙史。日前,该书由学苑出版社推出。 中华读书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等都编过“中国通史”,您如何评价中国通史的编撰现状? 赵世瑜:最近,历史学界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些刊物,围绕改革开放四十年,对于中国古代史各个不同时代的研究,请专家学者写回顾文章。不少专家提出,深入的个案研究很多,也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中国历史的宏观思考和整体把握略显不足。 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没有原因的。过去空话、教条化的东西比较多,大家接受的教训也多,于是去做具体的、个案的研究。这种情况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反复出现过。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出现“中国社会史论战”。讨论之后也有学者提出来,应该以宏观的视野去把握历史。研究就是在这样一些曲折的过程中发展,弥补以前的缺失,在此基础上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中国大通史》编撰之前,中国通史类的著作不少。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翦伯赞等编写的《中国史纲要》、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等书,成为新中国通史著作的最主要代表,构成20世纪中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几座丰碑。这些通史都带有个人鲜明的特点,不同时期的主编者观点不同,描述叙述的方式不同,写作的方式不同,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通史的编撰样式。改革开放后,白寿彝先生主持多卷本的《中国通史》,这个规模体量比以前的通史著作大得多,是《中国大通史》出现之前体量最大的。当时我也参与了写作。不过那时候在老师的带领和指导下参与工作,很难体现自己的想法。特别中国通史著作体量很大,不可能一朝一夕编撰完成,战线越长,越有可能无法纳入最新的学术成果。 小书靠观点取胜,大书要靠总体设计。《中国大通史》在结构上、体例上有一些新的尝试。 中华读书报:这些新的尝试体现在哪些方面? 赵世瑜:在结构上、体例上,《中国大通史》与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以及《资治通鉴》那样的编年体都不一样。《中国大通史》根据学术的发展,分成了不同的6编,各编又有自己独特的设计,吸收和反映了当时国内外多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在整体面貌上有了巨大改观,在视野上比较宏观,注重总体和长期的发展趋势,在内容上包罗万象,以同样的甚至更大的热情关注普通人民的生活,体现了更为强烈的现实关怀。在方法上是多样化的、多学科互动的、注重对深层意义的解释。新的通史编纂也遵循这样的思路。 中华读书报:《中国大通史》中有哪些比较重要的特点? 赵世瑜:第一,由于注重历史发展的长期性、连续性、渐进性,更多注意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尽量避免仅用重大的政治经济事件作为变化的标志,而更多考虑社会经济结构的长期的、较缓慢的变化。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依然充分肯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终级动因,而这种变化并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变化完成;另一方面,用个别政治经济事件作为变化的标志,既观点陈旧,又流于表面化,也是引起争论的原因之一。 第二,注重中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充分认识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人们在经济文化类型方面的差异,强调这种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在空间上的犬牙交错和在时间上的长期共存,避免截然断限和一刀切。 第三,提倡综合的观点,既注重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各种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合力”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从而显示社会发展的多重性和复杂性。 第四,倡导开放、多元、平等的历史观,从根本上抛弃汉族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 第五,重视动态的研究和空间的研究。以往的历史研究比较注重从时间的维度考察,忽视了空间的维度;容易流于静止的研究,较少注意动态的考察。这些在近年来的部分研究成果中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现在需要把它们吸收到通史中来。 第六,真正反映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史,对占人口大多数的下层人民给予较多关注。除了人民的反抗斗争外,更多注意普通人民的日常活动、行为、心态,将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 这些理论思考,都是参与这部大通史编纂的学者一致认同的,它们体现于本书各卷之中。 中华读书报:西方人编写的《剑桥中国史》比较畅销,而中国自己编写的通史却被读者冷落。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赵世瑜:当我们静下心来翻阅剑桥中国史中已出的各卷中译本,并寻找它的吸引人之处时,并没有在内容和体裁方面发现令人大吃一惊的东西,甚至感觉它并没有体现出近年来西方史学发展的最新和最有价值的成果,但是它的确与我们已经司空见惯的本土通史不同,这也正是我们的读者、甚至研究者趋之若鹜的原因之一。 在我们看来,其不同之处在于:一、其行文风格截然不同。如果读者有兴趣翻翻其隋唐史中译本描写“武后的兴起”的数段,或者其明史中译本关于“衰落期中的思想状况”一节,或是任何什么别的地方,就会发现,我们以前的通史中是极少有这样的写法的。二、各章节是由不同的作者来负责撰写的,显然他们都是该方面的专家,但同时他们又都有较大的自由度,并没有完全被捆绑在一起、完全按同一模式写作。这样两个鲜明的特点,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通史编纂多样化的问题。 西方学者在通史编纂方面给我们提供的有益经验,从指导性的理论来说,是较为开放而多样;从内容上说,是更为包罗万象,更注意以前曾忽略的诸多方面;从手法上来说,是更轻松活泼、灵活多样,较少刻板和公式化。但从史学史来看,他们并没有像中国学者那样对通史的体裁、体例进行大量研究的传统,因此在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上没有什么建树。而中国通史的编纂,还要根据中国历史以及中国史学史的自身发展特点进行。 中华读书报:本书分为15卷24册,分卷主编来自全国各地,如何把握总体水准?有没有争议比较大的部分? 赵世瑜:既然是通史,就要有一些统一的立场。我们认为划分中国历史阶段应该把握以下几个原则。第一,应以中国历史的具体发展为主体,以世界历史的多元发展为参照。这一点可以参考柯文(PaulACohen)的说法,就是“在中国发现历史”。第二,对所谓划时代的变化,不仅要考虑客观存在,也要考虑到当时人们的主观认识。这意思是说,人们往往从后世的角度观察历史,这当然有它的好处,可以避免当局者迷的缺失。但我们也要注意当时人看法。第三,历史阶段划分不是一刀切的,而通常是存在一个较长的过渡期的。过去抓住一个典型事件作为分水岭,也并不是就表明这个事件之前一天与后一天就有鲜明的差异。选择一个标识性事件总是要冒把历史简单化的风险,而且与历史实际不符。第四,宏观观照与微观研究缺一不可。 历史分期问题曾成为中国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但人们又不满足以往的探索,所以像冯天瑜提出的《“封建”考论》,也得到了各界的关注和争论。以往关于中国“封建社会”起点的不同意见是由于学者们对社会转型的认识存在分歧,各有各的道理,现在大家不会用某种现成理论来做唯一的权威依据了,也不会拘泥于某个用作分期的“符号”是否正确了。但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比如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期”,假如存在的话,也算是一次社会转型了,那么它与秦汉帝国建立的那一次是什么关系?说它是低一层次的转型好像也没什么道理。过去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除了受理论的束缚以外,还是因为人们过多地专注于“社会转型”,而忽略了“历史进程”,所以要想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推进,就要对这个一般的过程进行认真的研究。这个认真的研究不仅是在事实或者材料的层面上说的,还包括我们必须先摆脱以往的分期理论的影响和束缚,否则很容易在一种先设的理论框架下去解释事实和材料。 中华读书报:疆域和族群是中国通史中非常复杂的问题,在编撰中,需要特别注意什么? 赵世瑜:作为中国学者,既要秉持学术良心,也要担负责任。要按历史的实际去描述,只会有利于我们今天的现实考量。现在有一种现象非常不好,比如大汉族中心主义。这也是媒体发达造成思想混乱的局面。要说成吉思汗、皇太极的好话,很多人就会有非常激烈的反应;对岳飞一定要戴上“民族英雄”的桂冠,说他是一个抗金英雄都嫌不够。这些都带有强烈的主观情绪,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什么叫大国心态?大国心态是建立在每个国民的个人心态基础之上的。每个中国国民都有宏大的包容万象、兼容并蓄的心态,我们对历史对现实就会有冷静客观的立场,这才是大国的心态。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理解人心”对于从事历史研究有何重要性? 赵世瑜:我总觉得,只留在书斋里的学者不太容易理解材料中的真谛,多少还是有局限。当然做历史主要是通过材料,但历史是人写的,怎么理解人写材料时的思想活动和动机?如果不理解这个,就不理解史料的生产过程。如果不理解史料的生产过程,怎么去相信并使用这些史料?尤其如果历史写得曲折隐讳,怎么理解? 我们需要经常不断地去乡村行走、与人聊天。也许不会对历史研究直接有用,但对于理解普通人有帮助。有些学生已经努力尝试超越我们。我有个学生在做晚清民国浙江农村的司法案件。她试图找到这些打官司的人的后代,跑到山里边,通过走访,了解他们的祖先怎么打官司。过去官员在判案的时候,要依据老百姓的惯习。那么官员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把百姓形成的俗例作为判案的依据?老百姓的生活习惯,怎么变成了国家司法审判制度的一部分?这就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认识,过去认为制度是国家制定的。在学术的认识上,有田野调查和书斋里只看条文是不一样的。结合了田野调查的的历史研究,呈现出来的学术成果是接地气的。 1978年,安徽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地方到中央,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类似的事情,比如万历年间张居正的财政改革,也是从基层到中央。一个国家的巨大变动是怎么来的?很多时候,是根据百姓的生活经验创造出来的。(本报记者舒晋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