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老师:作为语言学家的启功先生
http://www.newdu.com 2024/12/29 05:12:13 章黄国学 newdu 参加讨论
“葛郎玛”重要还是语言现象重要?让我们看看作为语言学家的启功先生关于汉语语言学的新思路吧! 汉语现象和汉语语言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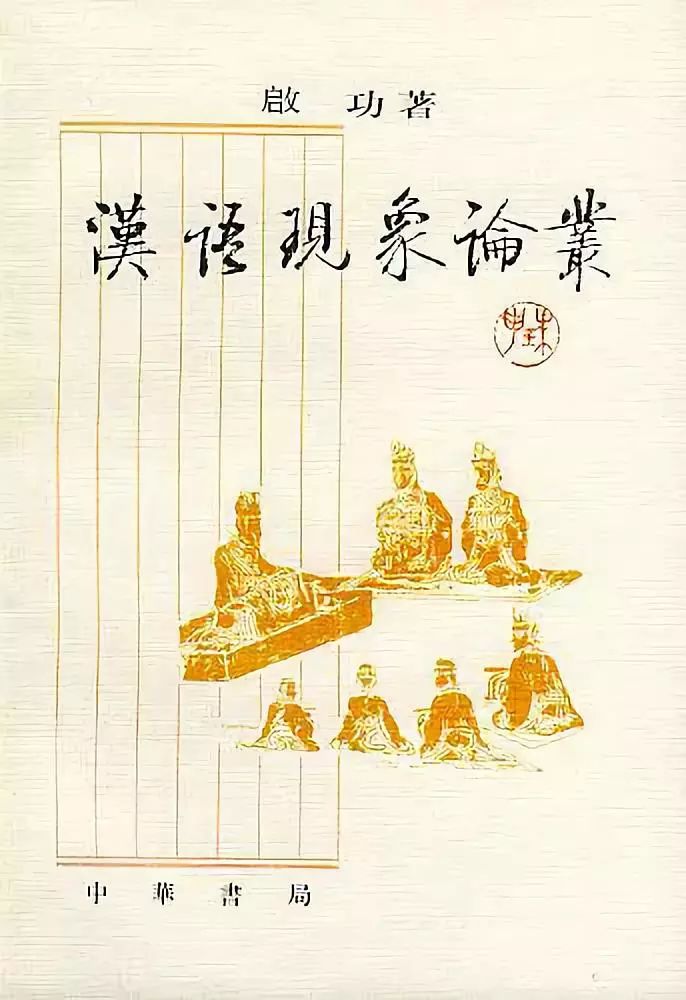 启功先生《汉语现象论丛》(后文均简称《论丛》)1991年12月在香港出版,内地的读者看到这本书的不多。后来有了大陆版,又收入了启功先生的全集,才有了更多的读者。能读过本书,都感到新颖动人、妙趣横生。书中涉及到的有关古代典籍文化、诗文音律的知识,年长者如逢故交,亲切逼真;年轻者瞠目诧异,闻所未闻。这种书,只能是中国文化通家的大手笔所为。 在现代学科的分布中,启功先生的专业并不属于语言学,他的专业被界定为“古典文学”或“文献学”,启先生对称他的专业是“文献学”很不以为然,所以我们成立“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时,启功先生不愿意用“文献”来指称他的学术,才改成了“典籍”。启功先生的出身、早年经历和自己的好学深思,造就了他睿智的学术眼光。青年时代得遇陈垣校长和其他几位名师,又推动他学识的精进,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独到的体验比比皆是。他在字画碑帖鉴定上的精准、对传统诗词书画的美学价值和内在规律的深入探究、对汉语汉字特点的独到见解、对书法问题富有个性的态度……都可以用‘身怀绝技’来形容。尤其是他在表达上富有个性的言语方式,总让我们想起一句话,叫做“读破万卷书,下笔如有神”。他的学养带有综合性,带有经验性,一旦把这些框到无论哪一个小格子里——如古典文学、文献学等等,原有的知识内涵就无法充分体现了,反而不如那些一开始就在小格子里培养出来的人那么适应。在汉语问题上,启功先生并非不懂西方,但他对汉语的感觉是纯正的、不含杂质的。《汉语现象论丛》是一位深刻体验过古今汉语的通家对自己本国语言的真实体验。  《汉语现象论丛》语言平易,如同闲聊;但是细观本书,读者自会发现,《论丛》绝不是为忆古拾趣而著的,而是针对着一个讨论多年而不得解决、现时代又不能不解决的问题而发,这就是如何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汉语语言学问题。读了启功先生这本书,会引起我们对一些问题的深入思考。 一 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汉语语言学的显学就慢慢变成语法,研究者们遵循《马氏文通》来建立以语法为中心的研究体系和教学体系,希望通过对《文通》体系的修补,使古今汉语较为合辙地嵌入拉丁文总结的“葛郎玛”中去,整整一个世纪不停地将二者磨合,甘苦说犹未尽,成败论而难分。能不能另找一条路来建立一种完全从汉语事实出发的汉语语言学或文学语言学呢?《论丛》正是以这个宏大的论题作为全书的宗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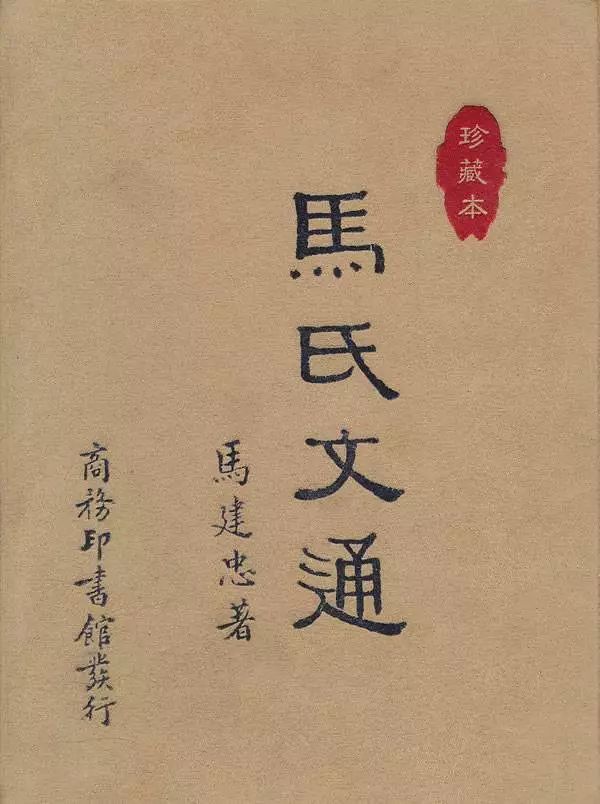 中国的传统语言学是从“小学”演化来的。“小学”研究的语言单位主要是书面语的词,更偏重于其中的意义。汉字是表意文字,古汉字的形音义是统一在一起的,于是“小学”分成文字学(讲形)、音韵学(讲音)、训诂学(讲义)。《文心雕龙.章句》说: 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淸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 古人的观念很明白:要把汉语讲懂、读懂,把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所有的词都弄懂了,句子、篇章当然也就懂了,挨个儿解释对了所有的词,就串成了句子;词讲错了,连起来就不象汉语的句子,这叫“不辞”。他们不着重去把句子拆成多少块儿来讲结构,因为觉得没有必要,既然词义通了句子也就明白了,何必还要去从形式上分析句子呢?汉朝人作的章句,是以句为单位来解释古书的,但也还是着眼在词义。比如: 《孟子·梁惠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赵岐《孟子章句》:“老犹敬也,幼犹爱也。敬吾之老亦敬人之老,爱我之幼亦爱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转之掌上,言其易也。” 这段话也就讲了三个词:一个“老吾老”的第一个“老”,一个“幼吾幼”的第一个“幼”,一个“运于掌”的“运”,意思全清楚了。所以中国传统语言学最丰富的是讲义训、义理,并没有一套成体系的句法。 《马氏文通》把“葛郎玛”引进了汉语,不论文言文还是白话文,可以把句子划成“成分”分析它们的关系,这确乎是一个进步,但问题接着也就来了。启功先生对这个问题有个十分形象的说法。他在《汉语现象论丛·前言》里说,英语的词有固定标志,所以因性分类;但汉语的词,用法太活,性质太滑,以英语套汉语,每有顾此失彼的情况,拿英语的办法套汉语,如同用小圈套大熊猫,很难合辙。 此话不假。“老吾老”、“幼吾幼”第一个“老”、“幼”得讲成动词,而且是意动用法 ,第二个“老”“幼”得讲成名词。用这种格式一翻译就成了“把我家的老人当成老人”,“把我家的小孩当成小孩”,意思并不跟古书的意思一样。至于说“孟子将朝王”的“朝”是“受动”,“欲辟土地,朝秦楚”的“朝”是“使动”,得先把意思讲出来才能判断。《左传》一个“门”字,可以当“城门”讲,可以当“攻城门”讲,也可以当“守城门”讲,究竟如何区分三种讲法,“葛郎玛”实在无能为力,还得靠前后文把意思分析出来。最不好办的是被“葛郎玛”称作“动宾短语”的那一堆词语,“指示王”是“指给王看”,“争杯酒”是“因一杯酒而争斗”,“颔之”是“向他微微点头”,“拦道哭”是“在路上拦着哭”,“五月鸣蜩”,干脆是“蜩鸣”……用一个“动+宾”格式一概括,原来读文言文凭着语感已经弄懂了的句子,这一下反而不懂了。这并不是说,语法总结出的那些法则没有用处或不正确,而是说,仅仅有“葛郎玛”,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套不上是一个方面,即使套上了,也不能解决主要的问题。 这些还大半是散文,如果说起诗词,那就更是套不上。不用说“红豆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这样的奇怪诗句用“葛郎玛”分析不了,就是“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这种本来看得明白、想得出来、感受得到的句子,如果用“主谓宾定状补”这么一套,诗的意境也就烟消云散了。  既然“小学”从根儿上被否定了,只认为语法才是“真正的语言科学”,近现代的语法学家,想了各种办法,创出了许多体系,增加或改换了好多术语,想让“葛郎玛”和文言、白话合榫头儿,实际上能合上的马建忠早就合上了,合不上的----马建忠就合不上的,他之后的语法学家也合不那么准,或根本合不上。 从“葛郎玛”延申出来的构词法,想把双音合成词的两个成分的关系用句法格式描述出来,不少词是合上榫头儿了,可也有些依然合不上。例如:“海拔”,“亲戚”、“缄默”、“刻苦”……头一个字(语素)和第二个字(语素)是什么关系?要是不把每个字(语素)的意思弄清楚,再把来源出处弄明白,它们是“主谓式”、“动补式”还是“联合式”?一下子还真说不出来。这些词有的书面语味道浓一些,有的干脆就是大白话,可是要追究组成它们的语素意义,大半还得找到文言里去,这一下连白话、文言的界限都得打乱!总之,“葛郎玛”提出的那些格式用到汉语里既有多余的,又有不够用的、非另想办法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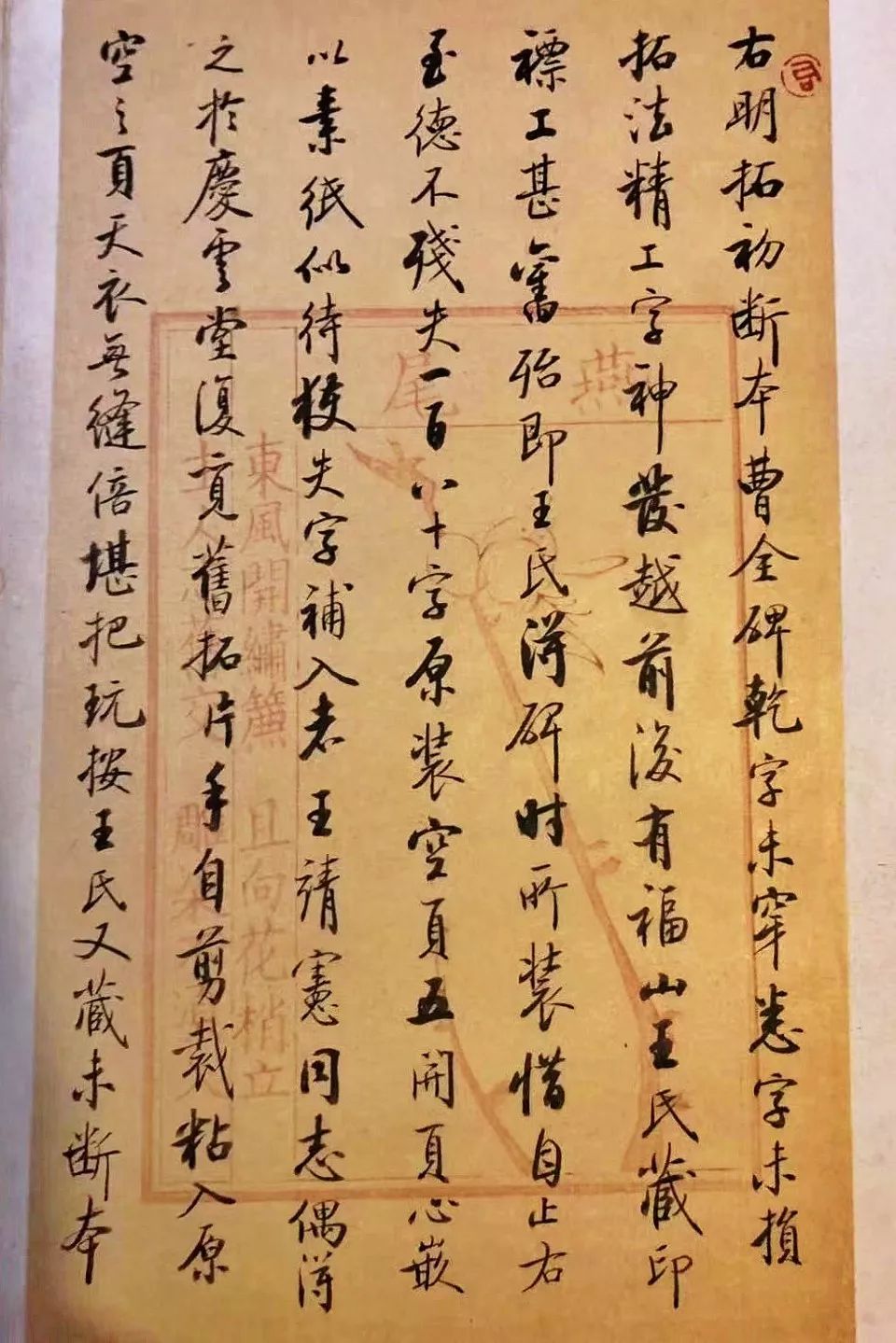 二 汉语语言学以语法为中心——而且走向单纯从外部形式上搞“葛郎玛”,也已有些年头儿了。内容的贫乏和方法的不适应,已经引起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关注。特别是文学界,因为“葛郎玛”管不住丰富的文学语言事实,解释不了五采斑烂的文学现象,便弄得文学家不买语言学的帐。按道理说语言规律应当能解释语言的艺术,语言的艺术里也应当能总结出语言的规律,可是好些语言的规律总是跟语言艺术的欣赏拧着。“葛郎玛”说句子得有主语、谓语,而且主语多半应在谓语的前面,又说定语、状语是附加在中心语上的,而且定语、状语多半应在中心语的前面……可是到文学作品里去查一查,不这么摆的句子绝非一个两个。于是语法学家管不符合“葛郎玛”的那些句子、段落的安排都叫“修辞”,语法是正常,修辞是反常。这正和有些文艺美学、文学语言研究者的结论走到一条道儿上去了。美学家认为,要想文学丰满、涵意深刻,必须“超越语言”。“超越”当然就是“反常”。这两家的共同认识是:正常的语言准确而不美,没有欣赏价值;非得反常才美,才经得起欣赏玩味。这不能不使人感到费解:为什么正常的语言规律管不住文学作品的语言呢?是因为文学根本不是语言的艺术,而是超语言或反语言的艺术呢?还是那些被称作“规律”的条条框框总结得有些问题呢?应当说,语言的变通是有的,但变通本身也应当符合一种规律。看来,要改造的不是那些能够懂又能使人产生感受的语言材料,而是那些套不上汉语事实的“葛郎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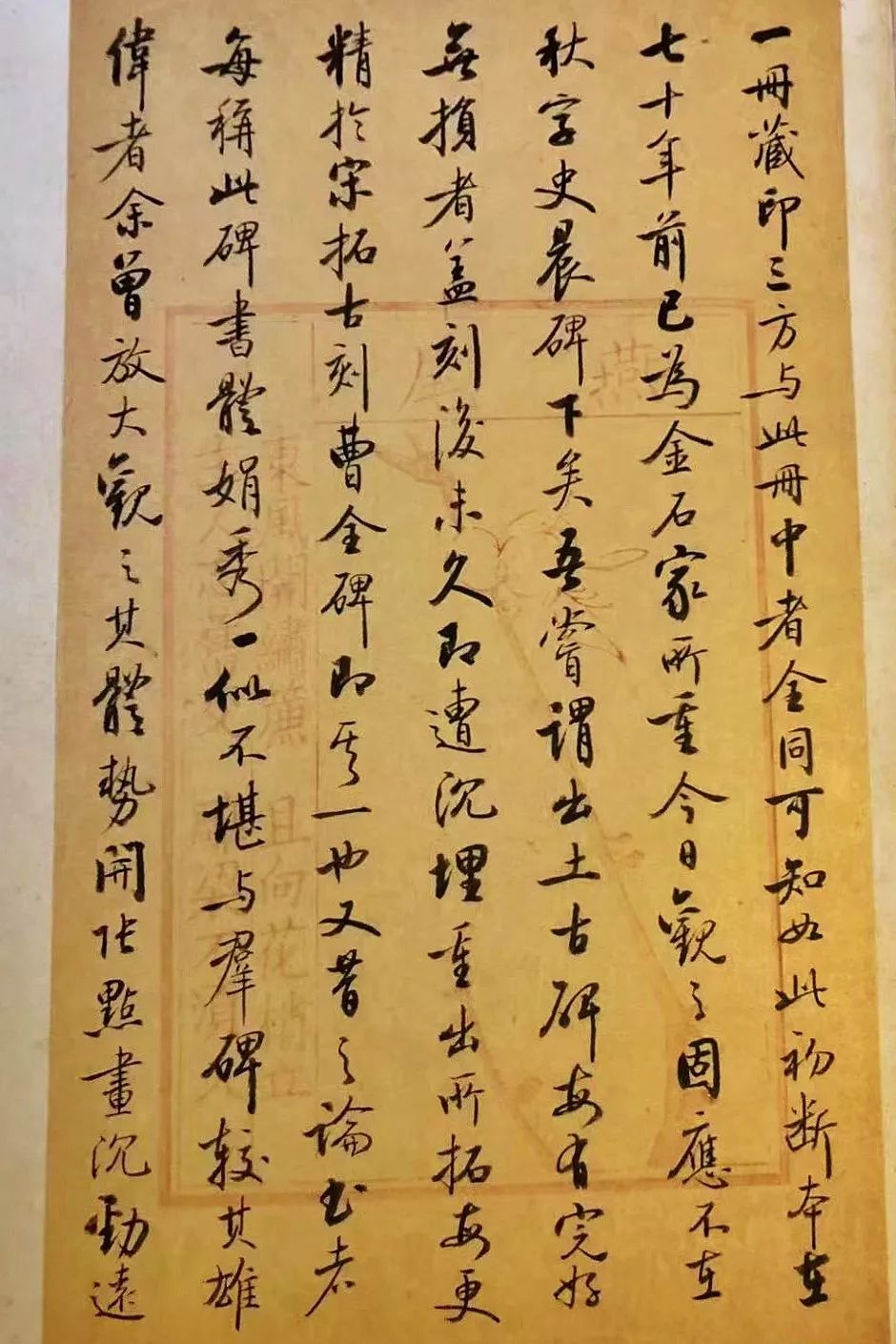 近年来,继承汉语语言学的传统,提倡“重视民族文化特点,建立切合汉语实际的汉语实际的汉语言学”的呼声越来越高,很多人朝这方面努力,成效当然是日渐其大,但在有些领域里,仍有两种方法上的错误导向在起作用:一种是抓住几条汉语的特例就奢谈汉语特点,其实仍然没有和汉语事实对上号;另一种则提倡考释孤立的生语料,有的是一个一个考,也有的是一片一片考,但都是单个儿的语料堆砌,难以从中生出一种可称作规律的条例。这两种导向造成了两种后果:前一种造成空泛,后一种造成烦琐,应当说,都是研究方法的误区。 怎样走出空泛与烦琐的误区,尽快创建成熟的、切合汉语实际的汉语语言学?启功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从汉语现象出发。一种法则切不切合汉语实际?看它能不能涵盖汉语语言现象;还有没有新的分析汉语的法则?也只有从汉语语言现象去观察。 现象是事物在发展、变化中所表现出来的外部状态和联系。通过外部现象来观察内在规律,这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普遍方法,但是在语言学领域,还提倡得很不够。语言学界强调的“第一手材料”,和“语言现象”并不是同义语。含有规律的现象并不是单个语言材料的堆砌,而是一种存在在许多语言材料之中共同的外部状态。一种形之于外的状况,如果不断出现,想躲也躲不开,一不小心就“掉进去”了,这才可以称作是一种有意义的现象,那里面似有一种冥冥的力量在制约着它,这力量就来自语言的规律。把它捕捉到,概括出来,就是语言的法则。总结这种法则,才能适合汉语实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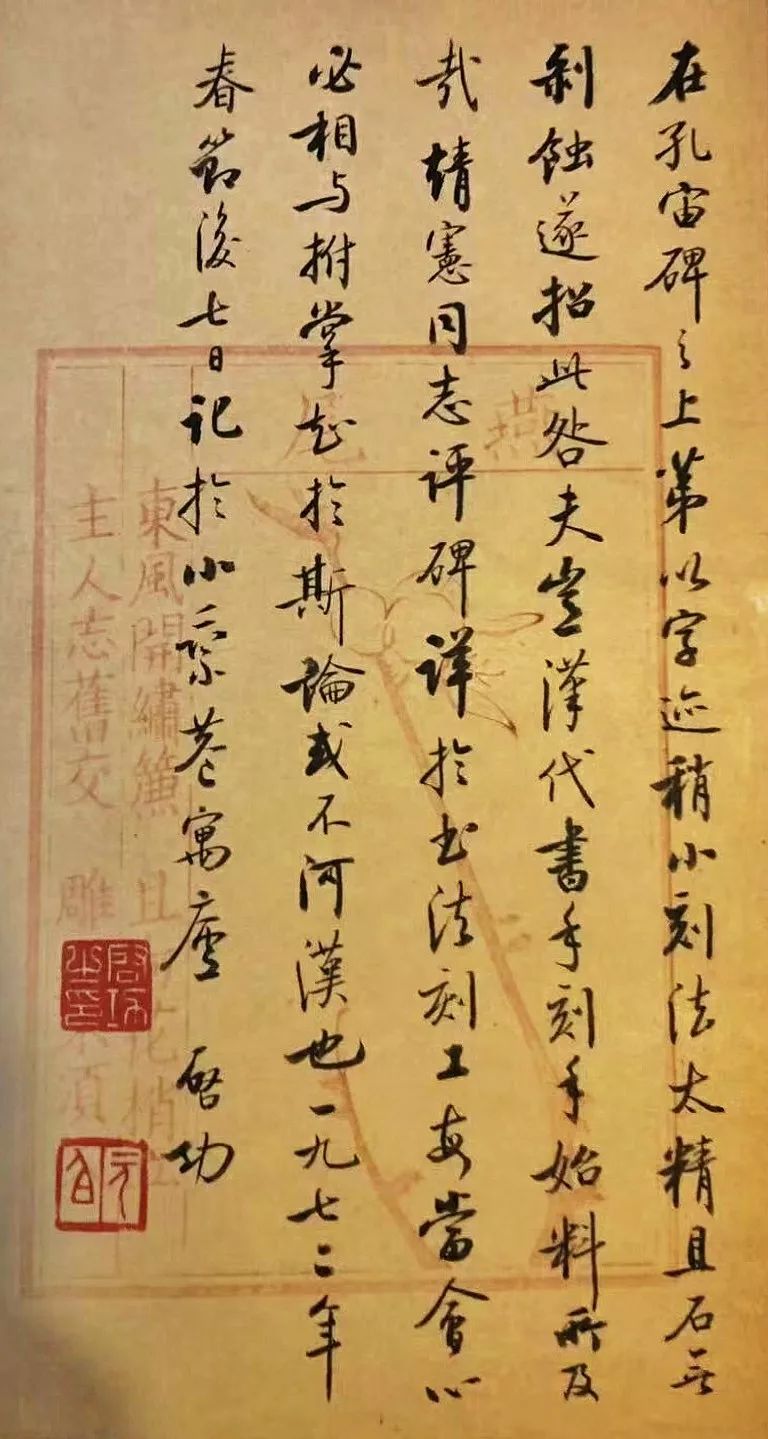 启功先生在《论丛》里说起他如何注意到汉语规律。他在《文言文中“句”、“词”的一些现象》说: 历年教古典文学作品,目的和方法不过是要让学生了解古今文词的不同。“五四”以后文言已不习用,讲文言文必须说出个道理,说明那些话为什么那样说,变成另一样为什么意思就不同了……因此留心观察那些文言文中有哪些现象,又从那些现象中探索它们的共同常态。 这就是从反复出现的现象中观察出的法则。《论丛》还指出,从正面观察现象可以得到法则,从反面观察现象也可以得到法则: 任何医生,都要从‘病象’入手。看不懂古文,是病象;从不懂到懂,是治疗过程;现在探索怎么懂的,是总结治法。评选最有效的医方。证明治百病的单方无效,也由此得到根据。(《前言》) 这一番话,把从现象出发来研究汉语的问题说得再透不过了:只有从现象出发,得到的法则才能解释汉语的问题:只有从现象出发,才能讲出符合汉语的规律;只有从现象出发,才能对付得了言语作品纷繁复杂的事实,而不致用“葛郎玛”这个单一的药方去治百病。这些说法都可以看出,启功先生并不是认为语法绝对无用,只是认为,要真正符合汉语实际,套不上的不要硬套;而且,不要就用“葛郎玛”一种办法来研究、解释、教学汉语,不要拿他来治百病。  三 从言语作品中出现的语言现象出发,宣告了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必须扩大。这样一来,仅仅从形式上归纳出的几条公式和定律显然不够用了。仅仅以词句为单位进行的语言本体研究着眼点显得太窄了。把语言学限制在只管通不通、不管美不美的狭小领地里当然更不符需要了。过去的汉语言学只能运用于散文,不能运用于诗词骈文;只能分析形与义相应的词语,不能分析形式压缩、内容积蕴的典故之类,这自然显示了当今语言学的一种贫血现象。 《论丛》从十分宽阔的领域里,提出了探索汉语特点的新思路。我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1、从“僵死”的形式中追寻鲜活 《论丛》指出: 历史上历次的打倒,都只是‘我不理它’而已,它的存在‘依然如故’焉。我们作文章不用它的样式,毫无问题;如探讨汉语的种种特点,正视汉语的种种现象,就不能用‘我不理它’的办法去对待了吧!(《前言》) 八股文是汉语语言作品中被否定得最彻底的一种文体,但它是吸取古代若干项文体陆续沉淀积累而成的。定型以后,又加以人为的挤压,加上一些苛刻的条件,并且规定用来表述被统治者规定下来的僵化思想,因而导至这种文体的枯竭僵死。但是,这种文体中积累的那些文章技法、语言运用格式,仍然可以追溯到它鲜活的时期。 如果说得更透一些,一种世世代代被使用汉语的人接受、采用、推广、生发的形式,正是因为它蕴藏着一种精华的东西,才能被人利用,利用得过分了,人为的限定多了,便容易僵死。对研究者来说,不应当因其僵死而忘掉追寻其中的精华。《论丛》举出许多例子说明那些符合汉语特点的语言格式想扔也扔不掉,想躲也躲不开。比如唐宋古文家反对骈体,去偶求单,可是他们的散文一不小心就掉到对偶句里去。又如,八股文的起、承、转,合,接与比的格式,规定死了,限制人的创造性,可是没有八股的限制,有些文章和语段,仍然跑不出这样的格式。正是这种不自觉掉进去的地方,反映了一种民族语言的习惯甚至是一切语言的通则。 2、从变动的事实中寻求定则 语言在应用中是多变的,句法成分时常增减、颠倒,虚词在语言中异常游离,用法都不那么固定。可是,汉语的表达并不如有些人所说的“缺乏准确性和完整性”。在前后语、上下文的制约和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说话,从来都是明确的。因为变动,就使人抓不住定则,《论丛》指出: 所谓愈分愈细,常见有时把一个小虚词翻来覆去,可列出若干个说法……如果将来规范化彻底完成,或说书面语十分固定之后,把这类游离的小细胞画出区域,不许乱动,那时才容易分析;否则它们常常把人搞得眼花缭乱,如在水里抓泥鳅,稍松即跑了。(《文言中“句”“词”的一些现象》) 又说:从一个小虚词到整个口里说的话,都给它固定住。怎样固定,固定成什么样子?无非是想使它们一一都符合‘葛郎玛’而已。其实泥鳅也有它们的生活动态的规律,有待于细心观察罢了。(同上) 这里提出了研究语言完全不同的两种思路:一种是按别人总结的法则来套汉语,希望把活语言框住;而另一种则是按活的语言现象来归纳法则,承认变动之中也有定则。  所谓从变动中归纳定则,首先要承认变动不居不等于随意而为,变动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受一定条件的限制、按自身变动的可能性来进行的。找到变动的范围,提出变动的条件,把它们与语言自身的可变因素结合起来,便归纳出了定则。这种“则”,可以管住汉语中的各种现象,是属于活的汉语的法则。如果不这么做,看见一个变化套不上“葛郎玛”,就列出一条“例外”,“例外”一多,就宣判汉语不具备准确性、规律性,岂不是倒行逆施! 3、从所谓的“超常”中发现正常 前面说过,因为用“葛郎玛”来套汉语,“超常”的“变例”就出现得很多。可是“变例”又反而具有巨大的表现力,常常能构成优美的诗词作品,耐人欣赏,激人遐想。从“葛郎玛”出发研究语言形式的人看不起修辞,认为那不过是经验之谈,无理性可言,不能入语言学的主流。而研究修辞学的人,也有一部分自居于语言学之外,从一星半点的语料甚至三流作品生造出的语句中归纳格式,让人们学着去写作。结果正为《论丛》所说,按着修辞标准去做,常常写出蹩扭的句子。  《论丛》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古代文章和诗词作品)句式真是五花八门,没有主语的,没有谓语的,没有宾语的可谓触目惊心。……我努力翻检一些有关讲古代汉语语法修辞的书,得知没有的部分中作‘省略’,但使我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省略之后的那些老虎(王按:指诗句)还是那么欢蹦乱跳地活着?(《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 在说到诗歌和骈体文时,《论丛》又尖锐地提出:我还没有看到过对诗歌和骈体文语法修辞的探讨,只看到过骈体文头上一大堆帽子,什么形式主义的,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不科学的,甚至更简便地说是反动的。奇怪的是,既然那么不合理,而竟然在二千多年来,有人写得出,也有人看得懂,起过不少表达思想的交际工具作用。这是为什么?……有无它们自已的法则?……有没有生活上的基础?还是只由一些文人编造出来的?(同上) 《论丛》指出,存在在诗词和骈体文中的一些语言格式和表现手法,都是有实际语言作基础的,很多是口语中本来就存在而被文人提炼出来的,这些语言格式不应被判处为“反常”和“超常”,而应当承认为正常的法则,而且它们恰能反映出汉语不同于西方语言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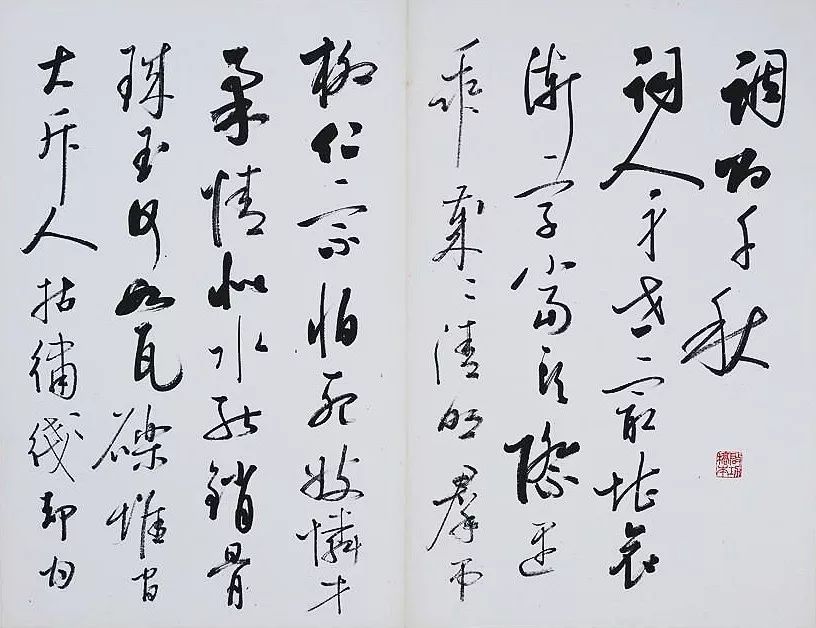 口语中用字可以伸缩加减,重迭可以加强语气,缩减也能加强语气,在语言环境中说话,可以少说许多成分还能被听懂,这就是汉语的特点。 口语中局部词汇颠倒而大意不变;诗句和骈句中由于字数、声调和为了增强效果而有所强调时,特别要倒着说;这是“倒装”的基础。汉语里凡是正着、倒着都可以讲通的句子,多半由于侧重点不同。故意放在前面的是突出点,例如“导之以政,齐之以刑”不等于“以政导之,以刑齐之”。故意放在后面的又是落脚点,例如“屡战屡败”是失利,而“屡败屡战”是勇敢。 口语中就有对句,虽然不一定整齐,但具备整齐的基础。诗词与骈文总结出各种对偶的详细条款,无非是为了对得工,对得美,那是因为汉语具有这种条件。 至于“比喻”,《论丛》指出,“语言根本都从比喻而来”,比喻不但不超常,简直就是词汇发展的经常性规律 。 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通常所说的“修辞”本来就寓于语言的正常法则之中,有一大部分应当回归到汉语语法中去。文学家所说的超越语言的种种现象,其实正被语言的正常法则在冥冥之中控制着,所以《论丛》说:有些诗歌、骈文的句、段、篇中的修辞作用占绝大的比重,甚至可以说这些部分的修辞即是他们的语法。(《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 当然,这样一考虑,对语言法则的归纳总结无论如何不能简单化,更不能套现成,这不正给汉语语言学的研究拓宽了道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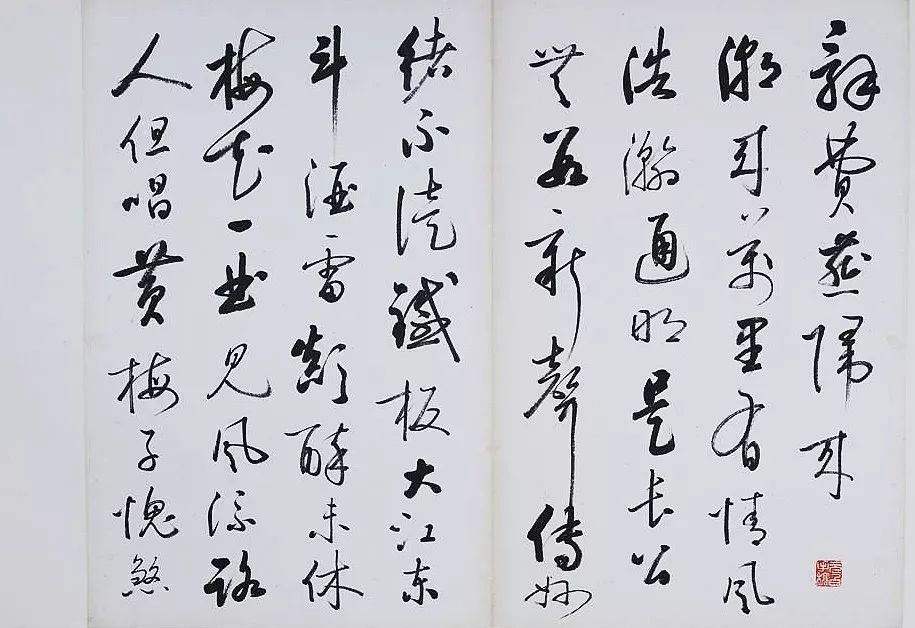 4、从单纯的形式结构研究中走向多维的探讨 《论丛》并不是绝对反对“葛郎玛”,只是反对不顾汉语的语言事实而对拉丁语法硬性套用。而且,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比如一句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其中仅有一句不通。要解释这种现象,“葛郎玛”无能为力。又如汉语里动不动就出现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这种现象也不是语法形式能解释得了的。《论丛》提倡从多维的角度来观察汉语现象。其中对语言学最具有启发性的应当是“意义控制说”和“音律配合说”。 《论丛》指出,句中词与词的关系“总是上管下”,又延展说:“不但词与词之间是这样,句与句之间也是这样”。什么叫“管”,《论丛》说,所谓的“管”,不只是管辖、限制,也包括贯注、影响、作用等意思和性质。很显然,这里所说的“管”,指的不是结构关系,而是意义关系。汉语的词语组合和句子排列,很少有形式上的成分来衔接,大部分都是意合,而话又要一个词一个词、一个句一个句地说出来,形成一种线性,这就迫使说话的人先提出主要的话题,然后顺着话题承接着往下说。一句话里有许多词,先说哪个后说哪个,全看说话的人如何组织那些词的意义关系。句子更是如此了,把重要的意思说在前头,相关而次要的意思说在后头,让前面已经说了的意思贯下去,影响后面的意思,才能让人听明白、听懂。本来,任何民族的人说话都应该这么说,只是拉丁语系的语言因为有语法形式的限制,任意组织意义的自由比较少;而汉语没有语法形式的限制,反而得到了这种自由。用意义控制——前面的控制后面的,来解释汉语的语序,的确是个非常深刻的想法。这就是“意义控制说”。  “音律配合”说就更符合汉语实际了。文言文以单音节为主,组合又是二合法,凡是三音节,大半是二合之后再与一个相合,凡是四音节,大半是两个二合再往一块儿合。这种两层二合最匀称,也最容易把韵律谐调得好听,所以最容易出现。为什么不接着往下合,到三合、四合、五合?《论丛》说,那是人的生理限制住了,一口气吐三个字、四个字,已经到了需要喘气的时候了,再往下说,就要停顿一下。所以许多虚词经常用来把三个字或四个字之外的句子成份隔开。散文的句式已经看出了这种音律配合现象,诗词的句式不过是把这种自然形成的格式再加以人为的规定罢了。汉语的阴阳顿挫、双声迭韵开始时只是人们说话时追求朗朗上口而自发形成,一旦被文人们发现了,规定出来,便成了格律。不信你去研究现代汉语双音词的语素配合,为什么A非配B,而不配B的同义词C?如果没有意义的原因,那多半是有韵律在起作用。 《论丛》的意思很明白:对汉语来说光一个语法结构解释不了那么多现象,更应重视的是意义和音律的配合关系,三者合而观之,多维度地观察语言事实,这样的语言学才能更加符合汉语的特点。 四 其实,语言形式与内涵之所以有民族性,是文化的多样性形成的。从文化的积蕴看语言的形式与内涵,才能明白汉语的特点。 《论丛》在谈到八股文和典故的时候,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那就是,语言形式是从不同时代的语言运用经验中陆续积蕴而成的。许多典故,典面虽压缩成两三个字,可内涵却是“一件复杂的故事、一项详细的理论”,而且典故用过一回又增加了一些文化的积蕴,越积越厚。能不能理解这些语言形式和词语内涵,全取决于听话的人文化素养高不高。现代符号学提出,要建立三个新的语言观:第一是语言能够规定思考的方式;第二是语言应对美学功能加以关注;第三是语言以最典型的形式表现文化。 这三个语言观都涉及语言与民族历史文化的关系。《论丛》从分析八股文、分析古代诗词、骈体文和分析典故中所阐发的思想,比这些提法要深刻得多也具体得多。西欧语言学家把汉语称作“孤立语”,后来觉得带有贬义,改称“词根语”,这是针对汉语缺乏语法形式,因而也很少有结构的外部手段而言的。他们针对汉语词汇缺乏词形变化这一点,又称汉语为“分析语”,认为这种语言的词汇没有综合概括的外部条件。二十世纪初打倒文言文的时候,宣告汉语落后要改用世界语的呼声早已有过,也无非是因为西方语言学家对汉语的这种判决。其实,只要认清那些从贬低东方的语言出发而判定东方民族落后的态度,认清那些要同化之、侵略之的恶劣动机(这当然不是多数语言学家的动机),西方语言学家从对比中总结出的汉语特点,倒是相当准确的。问题在于缺乏词形变化和语法结构形式的语言,便随之产生另一方面的优越条件,这一点普通语言学里却很少讲到。 象英语、俄语这些种语言,一个词象一根小铁钩,一边有环,一边带钩。这个钩钩进那个环,连成一条,就是一句话。钩和环得对合适了,大钩穿不进小环,大环挂不牢小钩,词的结合自由度很小,错了一点就被判为“语法错误”。可汉语的词象一个多面体,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胶,面面都能接,而且用点心都可以接得严丝合缝。比如回文诗,干脆接成一个圈儿,从哪儿都能念。这虽是文字游戏,可难道不启发人去想汉语的特点吗? 汉语的词没有词形变化,不给结构提供各类语法形式,但是,汉语词的意义容量却非常大。在文言文里,一个单音词的讲法真是“烟云舒卷,幻化无方”。虚实相生,动静互易,正反相容,时空互转,换一个地方有一个讲头儿,即使再高明的训诂大家,也难穷尽性的表述描绘。如果有一个讲头就列一个义项,连工具书也没法编了。所以启功先生说汉语工具书得重编,一个“书”字概括起来只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书写”,一个是“所写”。别的词也一样,比如“间”字,概括起来也只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当中”,一个是“隔离”。“间杂”、“中间”、“间谍”、“间厕”都是夹在当中。“间隔”、“离间”、“房间”、“间居”都是隔离开。所以需要从特点上概括,就是因为每个特点下的容量太大,列得太烦琐了根本没法选用。 词的意义容量极大,与别的词发生关系时结合的能量自然也就很大,加上句子结构的形式限制极小,所以就产生了一个五言诗句可以改为十个句式而只有一个不通的现象。这当然都是汉语的特点。 词的意义容量为什么会那么大?这不能不说是悠久的历史文化积蕴的结果。其实,典故的浓缩方式,在许多汉语的一般词汇里也都存在。周代的相见礼仪中,主方有上傧、承傧、绍傧管回话,宾方有上介、次介、下介管通报,绍傧与下介是主宾双方的第一接交人员,于是凝成双音词“介绍”。“介绍”不是典故,但文化积蕴不能说不深。“夜深前殿按歌声”,“朱门沉沉按歌舞”,张相说,在唐宋诗词里“按”当“排练”讲。其实,排练的意思是从击鼓来的,《楚辞》已有“陈钟按鼓”之说。如果中国的国乐没有用鼓来司节奏而暗中充当指挥的习惯,“按”引申为排练也就不会有可能。“按”不是典故,同样有文化积蕴在其中。  影响词的结合能量的,除了意义和文化的因素外,还有音律这个重要的因素。文言文的单音节词直接进入到现代汉语里充当语素,被汉字这种承负“音节——语素”的表意文字所书写,字也好、词也好,都离不开音节的声、韵、调。声、韵、调的配合加上节拍构成音律,也是控制词的结合能量的。 启功先生的这些独到的见解,对汉语语言学的发展指出了一个方向,那就是应当建立一套切合汉语事实的理论和操作方法,从只重视语法结构,转回到传统语言学更加重视词的音义的道路上去,对语文教学和社会应用有所指导,对文学创作和语言艺术有所贡献。 这些见解对语文教学也是很有启发的。前些年,有些老师提出在语文教学中要“淡化语法”,一开始不少人很难接受。其实所谓“淡化语法”,无非是针对把“葛郎玛”当成几乎是语文教学里唯一语言知识的倾向说的;针对让学生套语法、教学生背语法、出题考语法的这种片面应试的做法说的。面对那么丰富而有特色的汉语,是不是还应当从意义、韵律和文化这些角度来认识他、鉴赏它、运用它?是不是应当重视汉字在汉语发展和运用中的作用?是不是应当给文言文阅读应有的地位?——总之,是不是应当启发学生从汉语的事实出发来学会运用自己祖国的语言文字,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在语文问题上,一味模仿西方、追随西方会产生什么后果?这些问题早已经提到日程上,让我们不能不考虑了。在这种时候,读一读启功先生的这本书,确实可以对我们多所启迪。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李山老师:《诗经》与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线索
- 下一篇:刘宁老师:唐诗的自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