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大一统” 的 “三时一贯” 论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5:11:47 中国儒学网 黄玉顺 参加讨论
中国“大一统”的“三时一贯”论
【提 要】中国“大一统”的观念并不仅仅是自秦至清的帝国时代所特有的意识形态,而是中国政治文明中的一个源远流长的根本传统,它“一以贯之”地存在、而又显现为“三时”即三个不同时代的历史形态——王权时代的大一统、皇权时代的大一统和民权时代的大一统。 (原载《学海》2009年第1期) 黄玉顺 (四川大学哲学系 成都市610064) 【关键词】中国;大一统;三时一贯;王权时代;皇权时代;民权时代;民族国家 中国“大一统”的观念并不仅仅是自秦至清的皇权专制帝国时代所特有的意识形态,而是中国政治文明中的一个源远流长的根本传统,它“一以贯之”地存在、而又显现为“三时”即三个不同时代的历史形态——王权时代的大一统、皇权时代的大一统和民权时代的大一统。其“不易”与“变易”,皆渊源于中华民族的生活情感。然而今天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其“民权大一统”观念之建构,却还是一个亟待探究的重大课题。 一、中国“大一统”的三个时代 要理解“大一统”的观念,当然首先必须理解这个观念的历史背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可划分为有案可稽的三个时代,其间经过两次社会大转型、以及伴随的观念大转型,“大一统”这个一以贯之的政治文明传统也随之发生历史形态的转移[1]: 王权时代(夏商西周)——王权大一统 第一次大转型(春秋战国)[2] 皇权时代(自秦至清)——皇权大一统 第二次大转型(近现当代)[3] 民权时代(未来中国)——民权大一统 众所周知,“大一统”的明确概念[4]乃是由汉儒正式提出的。《公羊传·隐公元年》对孔子《春秋》所载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的解释: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5] 何休注:“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天](夫)王者始受命改制[6],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徐彦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 这里的关键就是:受命改制,布政施教;奉之为始,共系一统。换句话说,就是重建一套制度规范,其核心是重建一种政治秩序(“政教”体系)。这也正是孔子在谈到“礼”(制度规范)时所提出的“损益”原则(《论语·为政》[7])。中国“大一统”的三种历史形态——王权大一统、皇权大一统、民权大一统——及每一个形态内的“改朝换代”,都是这样的“元”“始”。 这里应注意分辨的是:《公羊传》是继孔子《春秋》而言“王者”之事,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在讲王权时代的事情;但事实上,“大一统”概念的形成过程正值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而该概念的最终完成则是在皇权时代的大汉帝国时期。具体来说,“大一统”的概念是在董仲舒那里得到透彻的理论表达、并得到汉武大帝采纳而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这一切决不是偶然的。董仲舒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天人三策》[8]) 这里尤须注意者:此时的“大一统”理论实际上是在为皇权时代的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加以论证。董仲舒指出,“大一统”的根本要义乃是“一元”;他认为《春秋》最重“元”,而“谓一元者,大始也”(《春秋繁露·玉英》[9]);“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春秋繁露·重政》)。我们知道,在政治层面上,这里的“元”具体就是皇权时代的“君”亦即皇帝。“元”就是“始”,“汉承秦制”,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皇帝,乃“始皇帝”,诗人李白赞叹道:“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始皇作为“元”“始”,乃“千古一帝”(李贽《藏书》[10])。李斯初见秦王就明确提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史记·李斯列传》[11])可见皇权大一统其实并不是董仲舒个人的观点,而是那个转型时代的一种普遍的观念,正如《汉书·王吉传》所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这种普遍观念,就是建构皇权专制的帝国政治秩序。所以董仲舒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春秋繁露·玉杯》)又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此之谓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总之,“大一统”概念的正式提出,是以帝国时代的来临为历史背景的。 但以上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大一统”观念有其更为悠远的历史。不少人误以为“大一统”只是皇权专制的专利品,到秦始皇才真正实现了“大一统”,那实在是极大的误解。“大一统”其实并非专制政治哲学所特有的意识形态,而是中华政治文明的一个普遍的观念。《诗经》便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诗句(《小雅·北山》[12]),《左传》亦有“封略之地,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的观念(《昭公七年》[13]),然而这都不是说的后来的皇权大一统,而是说的三代的王权大一统。这就是说,中国的政治文明从来是大一统的。比如《史记·五帝本纪》中说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这也是一种大一统。这就表明,“大一统”并不一定意味着皇权专制的政治体制,这个政治文明传统也可以表现为非皇权专制的政治体制、甚至民权时代的政治体制。 春秋战国时期乃是中国社会及其观念形态第一次大转型、也包括“大一统”观念转型的时期,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环节: 周公 → 孔子、孟子 → 公羊寿[14]、董仲舒 而我们注意到,皇权时代的董仲舒的观念与王权时代的周公的观念颇为不同。在民、君、天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周公所制定的乃是一个权力循环结构:  在这种关系中,民、君、天三者是相互制约的,这是“王道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15] 然而在董仲舒制定的结构中,人、君、天三者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简单的线性决定关系: 天 → 君 → 民 在这种关系中,假如所谓“天”是虚悬的,那么这就是极典型的君主专制的集权体制了。但这种线性结构只是董仲舒的表达方式,或者说只是皇权政治的表达方式;事实上,中国政治文明的权力关系从来是周公式的循环结构,即便皇权时代亦是如此,只不过这种结构的具体的历史形式是有所不同的,而这也正是大一统的三种历史形态之间的区别所在。唯其如此,当我们谈到“大一统”时,尤其是在诉诸现代“民权大一统”的建构时,必须割断“大一统”与“王者”的固定联系,因为皇权时代的、尤其是民权时代的大一统与王权时代的“王者”无关。但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当前一些儒者的认识存在着误区。 周公虽没有明确提出“大一统”的概念,但他“制礼作乐”之“礼”正是显然的大一统,只不过那不是皇权的大一统,而是王权的大一统。学者指出:华夏政治大一统虽时断时续,但观念形态的大一统则是由“周孔之道”构成的亲和力、向心力、凝聚力起了决定性作用。[16] 然后,誓愿“从周”的孔子继承并发展了周公的大一统思想。有学者从五个方面论证了孔子的大一统思想: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作《春秋》以尊天子;参与“堕三都”维护统一;维护“周礼”的统一思想;提出“正名”的统一思想。[17] 事实上,汉代“大一统”概念的明确提出乃是出自于其解释孔子所作《春秋》的“春秋学”,这个事实就已经充分表明了“大一统”理论与孔子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 孔子处在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的时期,他的政治思想正是从王权大一统到皇权大一统的转枢。有学者已指出:汉代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间的一个实质区别,就是古文经派用《周礼》中的分封制来反对孔子的大一统学说。[18] 这是一个颇有见地的观点。过去总有人说孔子试图“恢复”周礼,据此批判孔子“复古”、“保守”、“倒退”等等,殊不知这个判断与孔子本人的思想、尤其是关于礼的“损益”原则格格不入,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后来汉代建构新的大一统历史形态的问题必须根据孔子的思想资源加以解决这个事实(秦、汉均意在建立皇权大一统,然而秦反儒而失败,汉尊儒而成功)。倒是康有为说孔子“托古维新”[19],抓住了孔子“春秋大义”的根本特征。但为“维新”而“托古”并不是什么外在手段,而是最具有实质性的道路,就是在过去的“变易”的历史形态中追寻那个“不易”的、“一以贯之”之道,由此开展出一种新的“变易”形态。所以,“托古”并不是现成地“法先王之法”,而是“法先王之所以为法”。 总而言之,中国“大一统”并非皇权时代所特有的东西,而是一个贯通了上自王权时代、下至民权时代的中国政治文明历史的传统。 二、中国“大一统”的一贯之道 简而言之,大一统既是一,也是多:是一,而表现为多。所谓“多”,是说它表现为不同的历史形态;而所谓“一”,则是它的一以贯之的政治文明精神。这令人想起汉儒在谈《周易》之“易”时提出的“易有三义”之说[20]:变易、不易、简易。大一统历史形态的“多”是其“变易”,大一统精神的“一”是其“不易”;而此不易之道是很“简易”的,也就是上文所谈到的: 受命改制,布政施教;奉之为始,共系一统。 所以,在董仲舒看来,“大一统”不仅是帝国的理念,也是超越历史时空的“通义”:“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汉书·董仲舒传》)因此,帝王“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也就是说,制度规范是可以、也应当因时制宜地加以改变的,然而其“所以然”之道却是不必、也不能改的。那么,此“所以然”之道、“通义”究竟何谓? 《礼记·礼运》记载,孔子在谈到“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王权时代之通过“谨于礼”(制度规范)而达于大一统时说:“圣人耐(能)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孔子紧接着解释了这里所说的情、义、利、患、及其与礼的关系: 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女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21] 这段议论深刻地揭示了“改制”—— 改定礼制、亦即重建制度规范——的道理。要理解这段话的深刻意义,我们必须合孟、荀而观之,这里只能简要地谈谈: 孟子建构了“仁→义→礼→智”的观念(《孟子·公孙丑上》[22]),其中显然包含着解释“礼是何以可能的”意图:制度规范(礼)是由正义原则(义)导出的,而正义原则又是由仁爱精神导出的。但孟子在这里并没有谈及“利”的问题,也没有谈及“仁”何以导向“义”的问题。对此,荀子另有阐明:首先,仁或者爱会导致“欲”、并导致“利”,此即荀子的“爱利”(爱而利之)的思想(《荀子·儒效》[23]);然而由于“爱有差等”,这种利欲必定导致利益争斗,而有害于群体生存;于是,这就需要引入正义原则,在这种原则指导下进行制度规范的建构。这也就是荀子所说的“爱利则形,礼乐则修”(《荀子·强国》)。所以,合孟、荀而观之,我们可以大致领会孔子的思想。 上引《礼记》所载的孔子的议论(事实上当然是后儒的转述),也是解决“礼是何以可能的”问题的。孔子首先诉诸“人情”或者“七情”。关于“七情”之中的前面四情,传统文本中有两种大同小异的说法:此处是说的“喜怒哀惧”;《中庸》则说“喜怒哀乐”。合而论之,我们可以说有八情:喜怒哀乐惧、爱恶、欲。然而这八者实际上并非同一层次的:喜怒哀乐惧是情绪;爱恶则是感情(“感情”属于、但不等于“情感”);而欲乃是情欲,亦即由感情所导出的欲望,其实可以不算作情。[24] 儒家所讲的“仁”亦即“爱”,是对应于其中“爱恶”这个层次的。 爱恶必定导出欲望,欲望必然导向利害。孔子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然而“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论语·颜渊》)利害冲突当然是不利于群体生存的,这就需要制度规范。然而究竟应当建立一种怎样的制度规范呢?那当然是:适宜的、适当的、恰当的、正当的、公正的、公平的……这些也就是“义”的基本语义,荀子谓之“正义”(《正名》《儒效》《臣道》)。换句话说,制度规范的建构需要依据正义原则。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见利思义”(《论语·宪问》)。于是我们得出这样的观念架构: 仁→利→义→礼 按儒家的正义观念,我们可以说:不是出于仁爱的,那就是不正义的。但我们不能说:凡是出于仁爱的,就是正义的。对此,荀子已有深入的讨论。这就是说,仁爱只是正义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正义的充分条件。然而,我们可以进一步换一个角度发问:按照孔子的“仁爱”思想、“损益”原则,那么,夏、商、周三代的制度都出于圣人对于群体的仁爱,但三代的制度却是不同的,这是为什么? 我们由此进入儒家的另外一个思想视域:“生”与“生生”的思想视域;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生活”或者“存在”的思想视域。在儒家思想中,一切出于生、入于生;一切源于生活、归于生活。如果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25] 第40章),那么,生活就是“无”(先在于任何存在者的存在),而显现为“有”(唯“一”的形而上者的存在)以及“万物”(为“多”的形而下者的存在)。《周易》谈到“生”之“不易”的实情,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传》[26]);谈到“生”之“变易”的实情,谓“生生之谓易”(《系辞上传》)。事实上,“七情”或“八情”都是生活情感,或者说是生活的情感显现。大一统的具体历史形态的建构,就是渊源于生活情感的:一方面是仁爱的情感;另一方面则是要合乎时宜地适应于变动了的生活方式。这也就是古训“义者宜也”之意,也是正义原则的基本意义。生活是“不易”而“变易”的。由其“不易”之“生”,我们才能理解大一统精神的“一以贯之”;由其“变易”的“生生”,我们才能理解大一统形态的历史转变。 三、中国“大一统”的现代建构 对于大一统的历史形态转变,我们今天面临的就是今日中国的大一统问题。现代中国的“大一统”,集中体现为作为现代“民族国家”(nation)的“中国”(Chinese Nation亦可译为“中华民族”)的建构。此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最关键的两个问题是: (一)主权问题 主权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主权的主体问题;二是主权的统一问题。 在主权的主体问题上,作为现代大一统的中国,必须是一个民权社会,主权在民。(所谓“三权分立”不是一个根本的国体概念,而是一个具体的政体概念。)现代性的中国已不可能再是王权社会或皇权社会,而是民权社会。这就是说,民族国家的权力来源既不再是“天”,也不再是“君”,而来自“民”——“国民”或曰“公民”。首先是国民选择国家权力,然后才是国家权力管理国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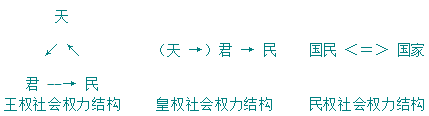 这种君权民授的观念,其实也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个传统。《尚书·泰誓》就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27] 如果说君权是由天意决定的,那么天意就是由民意决定的。上文谈到周公设计的权力循环结构,实际上正是中国大一统的传统当中的一个重要传统的体现,这个重要传统就是“民本”传统。中国典籍中关于“民本”的经典论述是人们非常熟悉的,这里不再赘述;我在这里尤其想指明的是: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其实也是、或者也应当是中国“民本”传统的一种体现。我的意思是:“民主”只是“民本”的一种特例,或者说“民主”是“民本”的一种历史形态而已;在中国的政治哲学传统中,不仅王权政治、而且皇权政治都是某种“民本政治”,对此,历代儒者是有高度自觉的意识的。 上文谈到,在董仲舒所设计的权力关系中,所谓“天”是虚悬的,那是典型的君主集权。然而在周公的权力结构中,假如“天”同样是虚悬的,那么它就变成了民权时代的权力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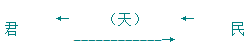 这就是说,君尽管是管理民的,但君的这种权力恰恰是来自于民的。“天”在政治权力结构中之虚悬,在周公那里还不是非常自觉的(周公所谓“天命”还存在着人格化、位格性的神的意味),而到了孟子那里就是相当自觉的了: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 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孟子·万章上》) 所谓“天与之,人与之”,也就是说:所谓“天与之”,其实乃是“人与之”。在民权时代里,这种“人与之”就是“民与之”。 至于民本、民权的具体实现途径、也就是“天”究竟意味着什么,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放眼世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历史告诉我们:国民主权在政体上的具体实现方式其实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例如,在一个君主立宪国家、或者某种变相的君主立宪国家里,这个君主应当具有怎样的权力?拿破仑皇帝何以代表了当时法国的国民主权?鼓吹专制制度的马基雅维里何以成为了启蒙思想的先驱?等等,都是应当另外专文讨论的问题。这里只是简要地指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具体政体的选择,既在共时性方面涉及这个民族国家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又在历时性方面涉及这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发展阶段。 在主权的统一问题上,现代中国必须追求在宪政制度下的统一,绝不容许任何形式的分裂。这就是现代中国的“大一统”。事实上,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常表现为统一与分裂的斗争:一个民族国家削弱另外一个民族国家的一种有效手段,就是造成后者的分裂;反之,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战略,首要的课题之一就是维护自己的统一。这与以下问题密切相关: (二)民族问题 我在多篇文章里都讲过,这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关键问题。我曾多次提出: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民族?这要看是在什么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在前现代概念的意义上,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但这不是“nation”的“民族”或者“国家”概念,而是“nationalities”或者甚至“ethnical”的概念;在现代性概念的意义上,中国只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是“中华民族”或者“中国”,这才是现代性的“nation”概念。[28] 因此,说到中国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那么,这个“民族”就是统一的、单一的中华民族,这个“国家”就是这个中华民族的国家。这就是在民族问题上的中国现代“大一统”观念。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值得一提:儒家所主张的“大一统”理念与其“和而不同”的和谐观念的一致。由儒学所传导的中国智慧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差异和谐”的原则:差异的存在并不一定和谐,然而没有差异的存在必定不是和谐。“礼乐”文明的精髓也就是这两个方面:礼以别异,乐以和同。而“大一统”正是这种文明传统在政治文明层面上的体现。
On “the Consistency Through Three Times” of Chinese “Great Unified Domain”
Abstract:The idea of Chinese “Great Unified Domain” is not only the ideology peculiar in the Times of Emperorship from Qin to Qing Dynasties, but a basic tradition having a distant source and a long stream in the political civilization of China which goes back to the remote antiquity. It exists as “the Consistent Tao” through and manifests itself as different formations in three times, i.e. the Great Unified Domains of the Times of Kingship, Emperorship and Citizenship. by Huang Yushun Key Words:China; Great Unified Domain; The Consistency through Three Times; the Times of Kingship; the Times of Emperorship; the Times of Citizenship; Nation [1] 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容当另文讨论。 [2] 此即雅斯贝斯所谓“轴心时期”,我称之为“原创时代”。见《生活儒学导论》,载《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 我称之为“再创时代”。见同上。 [4]“概念”与“观念”是不同的:一个概念是某个观念与某个具体词汇符号的固定结合,此时该观念成为这个符号的“所指”(概念的内涵)。“大一统”的概念是在汉代才正式成立的,然而大一统的观念却是与中华文明同步产生的。 [5]《公羊传》:《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6]“天”当作“夫”,据《春秋公羊传注疏校勘记》改。 [7]《论语》:《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8]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9] 董仲舒:《春秋繁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10] 李贽:《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11]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12]《诗经》:《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13]《左传》:《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14] 这里是指《春秋公羊传》的作者,具体是否公羊寿,这不是我们这里所关心的问题。 [15] 黄玉顺:《周公“德治”思想简论》,《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16] 元震:《周孔之道、礼乐文明:华夏文化传统人之物》,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 [17] 孙开泰:《孔子的大一统思想》,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e37f260100a2kx.html)。 [18] 何新:《简论古代儒学思潮的演变史》,中国国学网(www.confucianism.com.cn/html/zhexue/5665242.html)。 [19]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 [20]《周易正义》卷首《论易之三名》引《易纬乾凿度》:“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又引郑玄:“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21]《礼记》:《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22]《孟子》:《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23]《荀子》:王先谦《荀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8年版。 [24] 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讲“爱的观念”。 [25]《老子》: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本,《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7年版。 [26]《周易》:《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27]《尚书》:《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28] 黄玉顺:《儒学与生活: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探索的生活儒学》,《人文杂志》2007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07年第10期全文转载。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微孔子 我们将 “无家可归”
- 下一篇:孔子祭祀思想的现代人文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