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孔夫子共同助推中国梦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8:11:18 未知 佚名 参加讨论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曲阜视察并在孔子研究院发表了一段讲话。许嘉璐先生后来在讲话中将习近平的曲阜讲话与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视为具有同等意义——中国文化的弘扬与发展被列入国家战略的高度与日程上来。  一、马克思和孔夫子并非水火不相容 诞生于190年前的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象征符号,诞生于2600年前的孔夫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认为马克思与孔夫子水火不相容,必欲以马克思打倒孔夫子为快,所以上演了一场举世罕见的“古今大战”,并最终出现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闹剧—这既是严重的思想误解,也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批判。事实上,马克思和孔夫子的思想学说有着许多的相通性,不仅可以“道并行而不相悖”,而且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关系。  郭沫若 郭沫若在1925年写了篇题为《马克思进文庙》的小说,情节虽有些荒诞,但却不失正题戏说:文庙中的孔夫子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开场欢迎远道而来的马克思—这一格言早已成为中国文化包容性的隐喻;经过交谈,孔夫子发现马克思的理想社会与自己的大同理想“不谋而合”,马克思也发现自己对世界与人生的看法与孔夫子“完全相同”;最后,马克思慨叹说:“我想不到在两千多年前,在遥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一个老同志!”  梁启超 说两者思想“完全相同”未必确切,但中国文化的某些思想,如哲学上的唯物论倾向和辩证法色彩、政治上的以民为本诉求、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主张等,尤其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含有某些社会主义的原始因子却是事实。 毛泽东曾把三国时期汉中道教治下“路不拾遗、门不闭户”的现象称为“社会主义”。所以清末民初的许多人,如维新派的康有为和梁启超、革命派的孙中山和朱执信,也包括像郭沫若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认定“社会主义本是中国自古有之”。孙中山不仅把马克思称为“西方的圣人”,还认为自己的“民生主义”上承大同理想、外同社会主义,而康有为写的《大同书》甚至“比社会主义还社会主义”!  瑞士哲人布克哈特说:“一个民族的特性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渐积累而形成的,是无数经验的结晶,是一个国家及其民族命运的反映。”如果说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性的一种稳定而又持久的文化反映的话,那么直到如今,国内还很少有人注意到马克思和孔夫子思想学说的相通性对现代中国道路的重大影响。美国学者伯纳尔在《1907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一书中敏锐地提出:源自西方的社会主义之所以会在中国大地迅速传播开来,和厚重久远的中国文化为中国人提供的学理铺垫、心理预期、情感基础是分不开的。同样也可以说,社会主义之所以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并屹立不倒,甚至安然渡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际共运危机,也和中国文化与社会主义的这种天然的相通性不无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前,马克思和孔夫子相安无事且彼此谦让。毛泽东深谙传统文化,抗战期间曾在短短一句话中接连运用“不为天下先”、“退避三舍”、“礼尚往来”等格言典故来阐明自己的军事思想,还曾亲自撰写祭文并派员代为致祭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也正是他告诫人们不要“言必称希腊”,更不能教条化理解马克思,而是应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进行革命和建设。毫无疑问,中国文化是中国基本国情中的无形的、精神的要素,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弥足珍贵的遗产,所以毛泽东主张:“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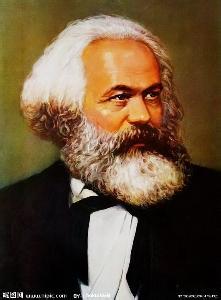 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直接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毛泽东的观点无疑符合马克思的主张,也符合孔夫子“因革损益”的历史文化观。即是说,无论时空如何转换,后人对历史文化传统都要保持一份温情和敬意,都要继承和发展之,而不能断然割裂和抛弃之—马克思需要如是对待孔夫子,今人也需要如是对待马克思和孔夫子。  二、马克思与孔夫子何以会“握手”? 抛弃了对传统的温情和敬意,必然会导致菲薄古人和盲目自大。“文革”不仅延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更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人为制造了一个“文化荒漠”和“信仰危机”。就此而言,改革绝非单纯地向西方学习和与世界接轨,而是也必须包括重新认知和续接中国自身的传统,因为这个传统在经过了一两代人的猛烈批判质疑和颠覆解构后,人们对它的陌生程度并不亚于对西方的陌生程度。 事实上,改革开放的第一波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潜存在人们心底的传统意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活的是农民勤俭持家的传统,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经营方式则体现了家族本位的伦理传统。整个20世纪80年代,外商投资的75%以上来自华人资本,因为中国文化有着强烈的“安土重迁”传统和“落叶归根”意识,华人华侨虽然身处异国,但心念旧邦—印度和俄罗斯对此羡慕不已,因为它们的国民一旦走出去就和母国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了。所以香港学者甘阳说:“中国传统本身就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中国陆续把“小康社会”、“以德治国”、“和谐社会”等传统理念应用于现实政治时,没有人再怀疑中国正在回归传统和孔夫子正在回归中国。如今,国学热风靡华夏大地,官方高调、高规格公祭孔夫子和黄帝陵,孔子学院遍及全球—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孔子再次周游列国”,十七大发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号召。而就在30多年前,“红卫兵小将”还曾试图对孔夫子挖棺鞭尸!今昔对比,不禁使人想起中国的一句俗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抛开表象不谈,至少有五大因素促进了马克思和孔夫子的“握手言和”。  首先,改革开放的灵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它要求也必然导致客观公正地重估中国自身的传统。 很显然,把凝结着千百年来古人经验和智慧的巨大传统说得一无是处和毫无用处,既不能合理解释中国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明,也容易身陷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潭。更为主要的是,如果缺乏传统的支撑,会使改革的思想资源和视野变得过于单一,即唯西方模式马首是瞻。这恐怕既非马克思所情愿,亦非孔夫子所乐见。可以这样说,30年来逐渐复苏的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而且是避免中国“西方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中国传统本身就蕴含着强烈的变革意识。 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常为后人包括毛泽东所误解,实际上他是指人类、社会以及政治的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应该是稳定而持久的,而具体的制度和器物则可以变化与求新,这就是《尚书》所强调的“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的本意。基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忧患意识与自强意识,中国传统非常重视变革求新,所以《周易》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而《诗经》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所蕴含的变革意识,启迪并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也把改革开放纳入到中国变革传统的历史谱系之中。  第三、虽然历史积淀传统,但传统并不完全等于过去,而是也必须活在当下并必须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有效的思想资源,否则就失去了生命力。 孔夫子云:“如有所誉,必有所试。”改革开放30年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令人忧虑的问题,比如环境恶化、贫富分化、官吏贪腐、道德滑坡、伦理失范、精神空虚等,而天人合一、贫富均衡、德法兼治、修身养性等传统思想资源无疑对于诊治这些弊病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和实践意义。当然,“药方只贩古时丹”是不行的,但“药方不贩古时丹”同样也是不行的。中国传统思想资源需要的是今人创造性地转换而不是盲目地复古,孔夫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斯之谓也。  第四、改革开放使中国踏上了国家崛起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征程,虽然这还是一个现在进行时,但业已取得的成就足以使中国人走出百余年来“事事不如人”的心理阴霆,从而极大地恢复了包括文化自信在内的民族自信心。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过程,正是通过与他者的辨异,国人才逐渐意识到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黄皮肤黑眼睛等生理特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语言文字、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独具特色,从而强化了自身的文化认同感—身处异国他乡的华人华侨往往比国内的人更为崇敬、也更加需要孔夫子。 最后,在国际交往过程中,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容易导致猜忌和对抗,而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虽然也有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但更容易为人们所彼此了解和相互包容,或者说,传统已成为表达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念与利益诉求的天然语言和有效工具。 美国可以在海外设置许多语言文化机构,但却不会在海外设置“自由、民主和人权办公室”—至少不会明目张胆地这样去做。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在海外建的却是“孔子学院”,而不是“马克思学院”。  孟子 三、“儒家”社会主义开始浮出水面 西方人虽然常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却固执地认为由传统社会通向现代社会或现代文明的大路只有一条,即实行资本主义。一战前夕,当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定只有新教伦理才能催生资本主义时,几乎等于从理论上关闭了非基督教国家迈向现代文明的大门—当然,接受基督教除外。一战后期,他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正式宣称儒教不具备催生资本主义进而迈向现代文明的思想资源。  马克斯·韦伯 但马克斯·韦伯生前似乎忽略了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并没有经过基督教化就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突飞猛进,创造了“东亚奇迹”,同样是对韦伯命题的一个颠覆,因为“四小龙”也是身处儒家文化圈之内,所以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都出现了“儒教资本主义”的探讨热潮。这一例子说明,传统社会通向现代文明的模式不再是唯基督教化一条道路,而是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朱熹 然而,“儒教资本主义”只是打破了“新教资本主义”的神话,并没有打破资本主义的神话,仍然是把现代文明的标志假定为资本主义,从而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视为现代文明的“异数”和“孤儿”。实际上,这既是“西方中心论”在作祟,也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偏见在搞鬼。抛开这些因素并且从理论上采用“自我定义”的方式,把本来就具有相通性的中国文化和社会主义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的发展模式,或者像甘阳那样干脆说“儒家”社会主义,完全可以视为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王阳明 虽然儒家从文化上拒斥“西化”,社会主义从政治上拒斥“西化”,但提倡“儒家”社会主义并不是完全排斥西方文化,更不是闭关锁国,而是反对西方文化反客为主、喧宾夺主。事实上,中华文明本性上就不具备排斥外来文化的传统,而改革开放以前包括今后也会一如既往地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的有益养分。德国前驻华大使康拉德·赛茨在2000年出版的《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一书中曾说,由邓小平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为中国社会创造了一个罕见的现象,即中国文化、社会主义和西方文化的融合。“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开放和包容既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动力,也是中华文明的优势所在。  “儒家”社会主义命题的理论意义在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固然有西方“刺激”而作出“反应”的外源型特征,但同时也具有自发和自生的内源型特征。“儒家社会主义”命题的实践意义在于,在经历了百余年激烈的反传统从而致使传统荡然无存的情势下,中国传统再一次焕发出生命的活力,进而使中国发展奠基在并融入到中华文明数千年连续一贯、生生不息的血脉之中。布克哈特说:“没有哪个民族是完整的,因此所有民族都设法补充自己。一个民族发展的程度越高,它就越有必要补充自己,因而也就越有活力。”“儒家”社会主义不古不今、亦古亦今,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博大精深、兼容并蓄,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既不同于传统中国亦不同于现代西方的具有强大活力的人类文明发展新模式、新路径。  “儒家”社会主义最终能否站得住脚,主要是看中国社会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世人普遍认为,改革30多年来中国人干得不错,这是对此命题事实上的支持。如今中国的内政外交不仅具有中国传统的深厚底蕴,也吸收融合时代发展的精华,正如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演讲时所说:“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 胡锦涛同志的演讲曾被外界解读为是一篇“中华文明的宣言书”,是一个马克思与孔夫子正式“握手”、共创美好未来的宣言书,也是“儒家社会主义”正式浮出水面的宣言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