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情感现象学比较研究(三):论“一体之仁”与“爱的共同体”
http://www.newdu.com 2025/05/24 10:05:27 中国儒学网 黄玉顺 参加讨论
论“一体之仁”与“爱的共同体”
[提 要] 阳明通过对《大学》的阐释,揭示出儒学“一体之仁”的观念。这与舍勒的“爱的共同体”观念之间存在着比较的可能:明德的本源性与爱的人格性;亲民的差等性与爱的等级性;至善的一体性与爱的共同体。阳明这种“一体之仁”的观念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念,却源于孔孟的一种本源的生活情感观念:仁爱首先并非形而下的道德情感、或者形而上的人性本体,而是先行于这一切的生活亦即存在的情感显现。——儒学与情感现象学的比较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6期) 黄玉顺 [关键词] 儒学;现象学;舍勒;一体之仁;爱的共同体 儒学与西方现象学的比较研究是中西比较哲学的一个新兴领域,而儒学与舍勒(Max Scheler)的“情感现象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则应当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是因为:儒学的核心课题是情感问题、尤其是“仁爱”情感问题;而舍勒“情感现象学”的基本课题也是情感问题、尤其是“爱”的情感问题。本文将展开的是儒学“一体之仁”的观念与舍勒“爱的共同体”观念之间的比较研究,意在揭示两者的情感观念所具有的不同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渊源。 一、明德的本源性与爱的人格性 儒家“一体之仁”的思想,王阳明进行了最系统的阐述。他是通过对《大学》“三纲领”的阐释来表述“一体之仁”思想的。《大学》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如下: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1]) 综合传统各家的解释,三纲领、八条目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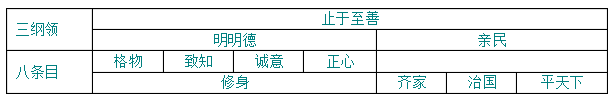 这其实也就是儒家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内圣的大纲是修身明德,其细目是格致诚正;外王的大纲是仁民爱物,其细目是修齐治平。对于《大学》这种“纲目”的理解,后儒多有歧异,尤其是在王阳明和朱熹之间。但本文无意于这种争论,而仅仅是以王阳明的解释为线索,真正的意旨在于:通过阳明心学与舍勒现象学的比较而还原到孔孟的思想,阐明真正的“孔孟之道”。 儒者认为,《大学》所讲的乃是“大人之学”,因此,王阳明从“大人”谈起: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大学问》[2]) 阳明的意思,“大人”是说的一种境界,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而之所以可能达到这种境界,乃是基于人之所固有的本体,就是“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这就是所谓“明德”。这种明德,阳明亦谓之“良知”,也就是“知善知恶是良知”(《传习录下》[3]);具体说就是:“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上》)然而经验世界中的人往往遮蔽了自己的明德,所以就需要通过“修身”以重新“明其明德”。 按“大人”之说,乃出自孟子。但在孟子那里,“大人”一词却有两种不同的用法,这是中国原创时代的观念转型的现象。一种用法是指的社会地位,主要是指的国君,如孟子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4])又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尽心下》)但孟子那里更为重要的是第二种用法,则是指的境界。如孟子说:“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离娄上》)这里的“大人”恰恰不是说的国君,而是国君的对立面。 这样的大人就是:“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尽心上》)这里的先“正己”而后“正物”,正是《大学》的由“明德”而“亲民”、亦即由内圣而外王。孟子的说法就是“居仁由义”:“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上》)“居仁”其实就是由“明德”“正己”而固执于“至善”,“由义”就是由“止于至善”而实行于“亲民”“正物”。 首先就是正己居仁。个体的“己”有两个方面,即“小体”(肉体感官)和“大体”(心体本性)之分。孟子指出:“所以考其善不善者,岂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告子上》)“正己”就是“养其大者”,就是“存心养性”(《尽心上》),亦即下文所说的“先立乎其大者”。孟子对此有更详尽的阐述: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告子上》) 阳明的思想与此一致:“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这就是说,无论阳明还是孟子,这里都有了人性本体的设定。孔子亦如此,他说:“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5])这种“天德”亦即“明德”。孟子尽管并未明确地提出“一体之仁”的说法,但有这样的思想。比如,他说:“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滕文公上》);此“本”即是“本心”,“万物皆备于我”(《尽心上》);“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离娄上》);“事亲,事之本也”(《离娄上》)。阳明所说的万物一体、无间形骸、不分尔我的一体之仁,也是这样的本体。这种本体具有强烈的形而上学色彩,也就是说,这种本体观念乃是对“存在者整体”、“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把握[6],本质上乃是主体性的事情[7]:既是人的相对主体性,也是关乎所有存在者的绝对主体性。 仅就设定了某种人性本体而论,舍勒的思想与儒家思想是不无相通之处的。在舍勒那里,这种本体就是他所谓“人格”(person):“人格价值才是最高的价值。”[8] 那么,究竟何为“人格”呢?他这样说:“我们现在可以陈述这样一个本质定义:人格是不同种类的本质行为的具体的、自身本质的存在统一,它自在地(因而不是为我们的)先行于所有本质的行为差异(尤其是先行于外感知和内感知、外愿欲和内愿欲、外感受和内感受以及爱、恨等等的差异)。人格的存在为所有本质不同的行为奠基。”[9] 对于人来说,人格就是“伦常人格”,亦即成年的、心智健全的、能体验到自己是其身体主宰的人的那种“行为的具体统一”。[10] 这种人格观念极类似于朱熹的“心统性情”的观点。朱熹认为:“心主于身;其所以为体者,性也;所以为用者,情也。”[11] 又说:“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12] 还说:“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13] 首先是身心的分离,而以心为主;然后是性情的分离,而以性为本。舍勒也是如此:“当我们评价‘人’时,我们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不依赖于生命价值的价值:神圣之物的价值和精神价值。…… 一个优越于所有生命的行为与内容(价值)的秩序在这个裂缝中显现出来,而且同时还有这个秩序的一个新的统一形式显现出来,即那个我们必须视为‘人格的’统一形式(不同于自我、生物体等等),而联结它们的是爱,以及奠基于其上的纯粹正义。”[14] 当然,朱熹所谓“心”并不等同于舍勒所谓“人格”,“性”也并不等同于“精神价值”;但毕竟“心”和“性”与“人格”一样是主体性设定。尽管舍勒宣称:“我也已经驳回了这样的主张:价值的存在预设了一个‘主体’或‘自我’,无论这是一个经验的自我,还是一个所谓‘先验的自我’或一个‘意识一般’等等。”[15] 但事实上他所谓“人格”仍然还是一种主体性设定:尽管舍勒不承认人格是经验的主体或先验的主体,人格这个所谓“存在统一”仍然不外乎是“作为行为进行者的人格”[16]、即各种不同行为的统一的主体。 然而我曾一再强调:事实上,在孔孟那里,诸如“大人”的“明德”这样的绝对主体、本体的确立,乃是有本有源的,亦即有其更为本源的生活情感:大人的明德作为本体是“本”,然而它还更有其“源”。[17] 如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离娄下》)所谓“赤子之心”,是比作为本体的德性更其本源的恻隐之情,这是作为本体的仁心善性的渊源所在。这也就是孟子所说: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18]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公孙丑上》) 孟子实质上是给出了这样一种渊源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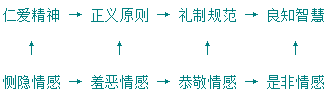 这里,恻隐情感作为最本源的情感,是“仁义礼智”那样的人性本体的大本大源、源头活水。“明德”本体事实上是在这样的本源上确立起来的;然后,我们才谈得上“正己”“居仁”。 这样“正己”“居仁”、亦即“修身”“明德”达成“内圣”之后,大人就能“外王”,亦即“由义”“正物”,在《大学》中,就是“亲民”、亦即“修齐治平”: 二、亲民的差等性与爱的等级性 孟子所说的由“正己”而“正物”、或者由“居仁”而“由义”,阳明解释为《大学》中的由“明德”而“亲民”: “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人之兄与天下人之兄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夫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谓“家齐”“国治”而“天下平”,是之谓“尽性”。(《大学问》) 这里,阳明采用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架构“体→用”来讲“明德→亲民”。但与此同时,阳明也强调两者的统一性、同一性,这就是阳明的“知行合一”而“致良知”的思想:“明德”之体是一种“知”,就是“良知”之本体;“亲民”之用是一种“行”,就是“良知”之发用;而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 阳明关于究竟怎样“亲民”的思想,与孟子的“推恩”思想是一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梁惠王上》)孟子又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这里存在着这样一种“推”的程序:亲(亲)→ 仁(民)→ 爱(物)。这就是儒家关于如何“施爱”方面的“爱有差等”的思想。 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如何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呢?在儒学,就是通过“爱有差等”的程序而最终达到“一体之仁”;而在舍勒那里,则是通过“爱的秩序”、亦即人格存在的某种等级性,而达到“爱的共同体”。爱的等级,舍勒称为“爱的秩序”:“我们在某人或某一群体身上认识到的一切道德上至关紧要的东西必须……还原为主宰它们并且在一切感性冲动中表现出来的爱的秩序。”[19] 这是因为:“存在着真正的和真实的价值质性,它们展示出一个具有特殊关系和联系的特有对象区域,并且作为价值质性就已经可以例如是更高的和更低的。但是,若果如此,那么在它们之间也就存在着一个秩序和一个等级秩序,它完全独立于一个在它其中显现出来的善业世界的此在,并且完全独立于在历史中这个善业世界的运动与变化,而且对它们的经验来说是“先天的(a priori)。”[20]“一个对于整个价值王国来说特殊的秩序就在于:价值在相互的关系中具有一个‘级序’,根据这个级序,一个价值要比另一个价值‘更高’或者说‘更低’。”[21] 这种秩序乃是由若干精神人格所组成的“精神集体”的等级结构,包括由低到高的四个价值等级:适意与不适意的价值;生命感受的价值(或高贵与粗俗的价值);精神价值;神圣与不神圣的价值。[22] 此外,舍勒又将情感感受分为由低级到高级的四个阶段:“1.感性感受或‘感觉感受’,2.身体感受(作为状态)与生命感受(作为功能),3.纯粹心灵感受(纯粹自我感受),4.精神感受(人格性感受)。”[23] 这四个阶段所对应的乃是不同等级的价值载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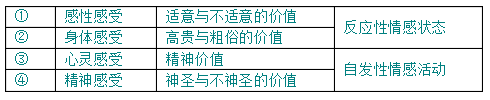 因此,舍勒的伦理学的宗旨,可以概括为:“掌握爱之秩序”,“整顿爱的秩序之迷乱”。[24] 这就是说,儒家和舍勒都在讲某种等级秩序,但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是:舍勒所讲的秩序、即“爱的秩序”乃是一种人格价值的等级划分,其中最高的价值乃是上帝位格:“爱的秩序是一种上帝秩序,而后者则是世界秩序之核心”[25];“此一本质无限的爱为着自身的满足祈求一种无限的善。换言之,上帝理念这一对象已经鉴于一切爱的这种本质特征为爱的秩序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上帝,只有上帝才可能是可爱性之王国这座阶梯形和金字塔形建筑的尖顶----大全的本源和终极。”[26] 而儒家所讲的秩序却不是这样的“人格秩序”、“上帝秩序”,而是“人伦秩序”,这种人伦秩序的等级不是人格价值的等级,而是仁爱情感的自然差等。 这里涉及一个重大问题,亦即所谓儒家伦理的宗法性质的问题。孟子与墨家有一次论辩,主张“爱有差等,施由亲始”的原则。墨家的夷子认为:“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孟子回答:“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滕王公上》)关于“赤子匍匐将入井”,这是众所悉知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公孙丑上》)这样一来,孟子的思想中似乎存在着某种矛盾:一方面是“爱有差等,施由亲始”;另一方面,将入于井的孺子却与我们非亲非故,我们对他所表现出来的恻隐也并非什么“推”的结果,即与所谓“宗法伦理”毫无关系。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矛盾”呢? 其实这里并无所谓“矛盾”。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必须还原到儒家的一种本真的“生活”“情感”观念。过去,仁爱情感往往仅仅被理解为一种形而下的主体性的道德情感,殊不知,仁爱情感首先是一种生活情感,这种生活情感不仅先行于道德情感,而且先行于人性本体的设定。这就是我们所一再强调的儒家所固有的一种“情→性→情”的观念。秦汉以后、亦即原创时期以后的儒学,往往注重于“性→情”的形而上学架构,而遗忘了原创时期、亦即孔孟那里的“情→性”的本源观念。[27] 儒家“爱有差等,施由亲始”的思想,渊源于当时的宗法社会的生活方式,即是渊源于生活的,这就导向了宗法伦理的建构,而这在当时是完全正当的;然而,那种与宗法伦理毫无关系的、由“孺子将入于井”而显现的“恻隐之心”,同样也是渊源于生活的,而这也是正义的。这里的关键在于一种透彻的本源的“生活”观念:一方面,生活即是存在,然而生活本身并不是任何存在者的存在,而是先行于一切存在者的存在本身;但另一方面,生活的衍流又总是显现为具体的历史的生活方式,因而生活又总是具体的历史的存在者的存在。因此,一方面,作为生活本身之情感显现的仁爱情感,本身是与任何具体的主体性存在者的生活方式无关的,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超越时空的、超越历史的、普适的情感,这才是“万物一体之仁”之所以可能的真正渊源所在;但另一方面,这种情感却又总是在具体的社会生活方式中显现出来的,这也就是说,这种仁爱情感,在前现代社会生活方式中可以导向一种前现代的伦理建构,而在现代性社会生活方式中则可以导向一种现代性的伦理建构。这就是说:必定“爱有差等”、然而未必“施由亲始”。上述所谓“矛盾”,便消融于这样的“生活”观念之中。 孔子所持的就是这样的情感观念。一方面,在当时那样的生活方式中,他也主张爱有差等、施由亲始,这就是“仁”的“时义”性;但另一方面,就作为任何生活方式之渊源所在的生活本身及其情感显现而论,尽管爱总是有差等的,但施爱未必由亲始,这就是“仁”的“通义”性。例如《论语·尧曰》引《尚书·泰誓》说:“虽有周亲,不如仁人。”朱熹解释:“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论语集注》[28])这里,作为他人的“仁人”比具有宗法血缘关系的“至亲”更重要。孔子之所以主张“礼有损益”(《为政》)、并由此成为“圣之时者”(《万章下》),真正的缘由乃在于此:作为社会规范建构的“礼”、包括伦理的建构,应当是随着生活方式的历史变动而因革损益的。这样就既坚持了儒家的仁爱精神、又避免了任何陷入原教旨主义的可能。 三、至善的一体性与爱的共同体 儒学之所以强调“爱有差等”,真正的终极追求乃在于达到“一视同仁”,亦即达到“一体之仁”的境界。按照阳明的看法,《大学》所谓“止于至善”就是这个意思: “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也。…… 故止至善之于明德、亲民也,犹之规矩之于方圆也,尺度之于长短也,权衡之于轻重也。…… 明明德、亲民而不止于至善,亡其本矣。故止于至善以亲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谓大人之学。(《大学问》) 阳明这里以“良知”说“至善”,仍然是归结为回复“大人”的“本体”:“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这就是儒家所说的仁的一体性。简要来说,儒学“一体之仁”的思想就是:在“本体”的层级上,万物本来一体;在“工夫”的层级上,我们应当重新回归万物一体。这种工夫存在着两个方面:实现程序上的“爱有差等”;终极目的上的“一体之仁”。 正如儒学追求这种一体性,舍勒也在追求某种一体性。然而他所说的一体性,乃是由人格所组成的“爱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存在着一种“爱的秩序”。舍勒认为存在着“各种共同体的纯粹类型,如爱的共同体(和它的技术形式:教会)、法律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生命共同体(和它们的技术形式:国家),最后是所谓‘社会’的单纯形式”[29],其中最具有终极奠基性的是根源于上帝人格的“爱的共同体”:“世界的统一性和惟一性……是建基于一个具体的、人格的上帝的本质之中,与此同时,所有个体人格的本质共同体都……仅仅建基于这些人格与人格之人格的可能共同体之中,即建基于上帝的共同体之中。”[30] 世界乃是一个“可爱性之王国”:“这个王国从基本原子和沙粒到上帝是一个王国”。[31]“爱的秩序是一种上帝秩序,而后者则是世界秩序之核心。”[32]“此一本质无限的爱为着自身的满足祈求一种无限的善。换言之,上帝理念这一对象已经鉴于一切爱的这种本质特征为爱的秩序的思想奠定了基础。”[33]“只有个体生灵和人灵以同时的(共生的)和渐进的(历史的)、按照爱的秩序整顿的价值领域之互爱为形式作出的补充才能够实现个体之独一无二的总体使命----‘人类’。”[34] 舍勒所谓具有“爱的秩序”的“爱的共同体”本质上就是基督教的共同体,“它的最高形式是宗教的爱的共同体”。[35] 舍勒分析了“基督教的爱理念”的两个方面,这两者之间是一种奠基关系,前者是第一原理,而后者是由前者引导出来的集体理念: 1、爱的律令:“爱的律令的第一条原理:‘爱上帝胜过一切。’”[36] 2、基督教的集体理念。他推导出三条“定理”:①人是集体的存在:“我们据以出发的第一条定理是如下述:人,即有精神的、有限的人格,与其他和自己同类的个人过着共同的生活”[37];②朝向最高级存在者的超越的要求;③道德的责任共负原则:“一个理性人的全部存在和行动,既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责任自负的个体现实,同样也是某个集体中有意识的、责任共负的成员现实。这乃是一个理性人的永恒的理念本质。”[38]“每一个人及每一个范围较窄的共同体,在他们作为某集体的‘成员’之必然的身份中,是同等本真与责任自负的;他们在上帝面前,为在精神和道德方面涉及任何一个包容性的集体的境遇和行为的一切共同负责。”[39] 舍勒认为西方历史上只有极个别的人物,如奥古斯丁和帕斯卡尔,曾经接近这种观念。他说:“在帕斯卡尔的著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观念像一条红线贯穿在其中,他时而用‘心的秩序(ordre du coeur)’、时而用‘心的逻辑(logique du coeur)’这些词语来标识它。他说:‘心有其理(Le coeur a ses raisons)。’他将此理解为一种永恒的和绝对的感受、爱和恨的合规律性,但这种合规律性绝不能被还原为智识的合规律性。”[40] 而舍勒自己则称之为“爱的秩序”。 其实,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例如亚里士多德提到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的观点:“照他的实义来解释事物,则我们当可确言友<爱>为众善之因,而斗<憎>乃众恶之因。这样,我们若说恩培多克勒提出了(或是第一个提出了)‘众善出于本善,众恶出于本恶’的善恶二因为世间第一原理,当不为误。”“宇宙万物由憎斗而解体,…… 又因友爱而重聚为万物……”[41] 但是,这种观念并未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想;西方主流思想是理性主义或者理智主义的,而不是情感主义的。正因为如此,舍勒的情感现象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思想意义。 但是,舍勒的情感观念与儒学的情感观念之间仍然是截然不同的。最根本的一点是:如果说在舍勒那里,“在人是思之在者或意愿之在者之前,他就已是爱之在者”[42];那么在儒学这里,这种类似“仁者”的“爱之在者”也不是最本源的存在,最本源的存在乃是生活本身及其情感显现。仁者乃是在这种仁爱情感的显现之中生成的,而不是相反;是“仁”之“诚”先在先行,然后由此“成己”(主体性存在者)“成物”(对象性存在者)(《礼记·中庸》),包括成就仁者。 因此,舍勒所说的具有“爱的秩序”的“爱的共同体”,作为人格的共同体、乃至上帝秩序,本质上是主体性存在者的世界;而儒学所说的“一体之仁”尽管也有这层意思,却具有一种更为本源的观念层级。儒学所说的“一体之仁”,固然具有伦理学的观念层级,例如原创时代孔孟儒学之后的那种“性→情”观念,此“情”即是伦理意义上的主体性的道德情感;并且具有本体论的观念层级,例如本文所述的阳明心学的“大人之学”,仁爱被理解为作为本体的良知;然而在儒学、尤其是孔子和孟子的儒学中,“一体之仁”首先乃是一种前伦理学、前本体论的事情,乃是一种前哲学、前形而上学的事情,这是更其本源头的“情→性”观念。这里,“一体之仁”是说的在本源情境中的共同存在、共同生活的情感显现;在这种本源情境中,主体性、对象性都还没有生成,乃至任何物、任何存在者都还没有显现出来。这样的“一体”恰恰正是“无体”:这是真正本源的“形而上”——“神无方而易无体”(《周易·系辞上传》[43])。 * 本课题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项目“儒学与情感现象学比较研究”,批准号:SC06B017。 [1]《礼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2] 王守仁:《大学问》,见《王阳明全集》,吴光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3] 王守仁:《传习录》,见《王阳明全集》。 [4]《孟子》:《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5]《论语》:《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6] 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见《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版,第68页。 [7] 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见《面向思的事情》,第76-77页。 [8] 舍勒:《伦理学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倪梁康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618页。 [9] 舍勒:《伦理学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第467页。 [10] 舍勒:《伦理学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第580-588页。 [11] 朱熹:《答何叔京二十九》,见《朱熹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12] 朱熹:《朱子语类》,黎靖德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九十八。 [13] 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八。 [14] 舍勒:《伦理学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第350-351页。 [15] 舍勒:《伦理学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第323页。 [16] 舍勒:《伦理学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第468页。 [17] 黄玉顺:《生活儒学导论》,见《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8] 孟子这里所说的“辞让之心”,《孟子·告子上》中又作“恭敬之心”。 [19] 舍勒:《爱的秩序》,林克译,见《舍勒选集》,刘小枫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40页。 [20] 舍勒:《伦理学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第15页。 [21] 舍勒:《伦理学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第104页。 [22] 舍勒:《伦理学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第二篇第5章。 [23] 舍勒:《伦理学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第404页。 [24] 舍勒:《爱的秩序》,见《舍勒选集》,第749页。 [25] 舍勒:《爱的秩序》,见《舍勒选集》,第751页。 [26] 舍勒:《爱的秩序》,见《舍勒选集》,第754-755页。 [27] 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讲“爱的观念”。 [28]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29] 舍勒:《伦理学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上册,第133页。 [30] 舍勒:《伦理学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第485-486页。 [31] 舍勒:《爱的秩序》,见《舍勒选集》,第752页。 [32] 舍勒:《爱的秩序》,见《舍勒选集》,第751页。 [33] 舍勒:《爱的秩序》,见《舍勒选集》,第754-755页。 [34] 舍勒:《爱的秩序》,见《舍勒选集》,第756页。 [35] 舍勒:《伦理学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第607页。 [36] 舍勒:《基督教的爱理念与当今世界》,李伯杰译,见《舍勒选集》,刘小枫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12页。 [37] 舍勒:《基督教的爱理念与当今世界》,见《舍勒选集》,第820页。 [38] 舍勒:《基督教的爱理念与当今世界》,见《舍勒选集》,第820页。 [39] 舍勒:《基督教的爱理念与当今世界》,见《舍勒选集》,第825页。 [40] 舍勒:《伦理学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第308页。 [41]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页。 [42] 舍勒:《爱的秩序》,见《舍勒选集》,第750、751页。 [43]《周易》:《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