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行与德性:怎样做个完美的人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0:10:41 《文史哲》期刊 彭林 参加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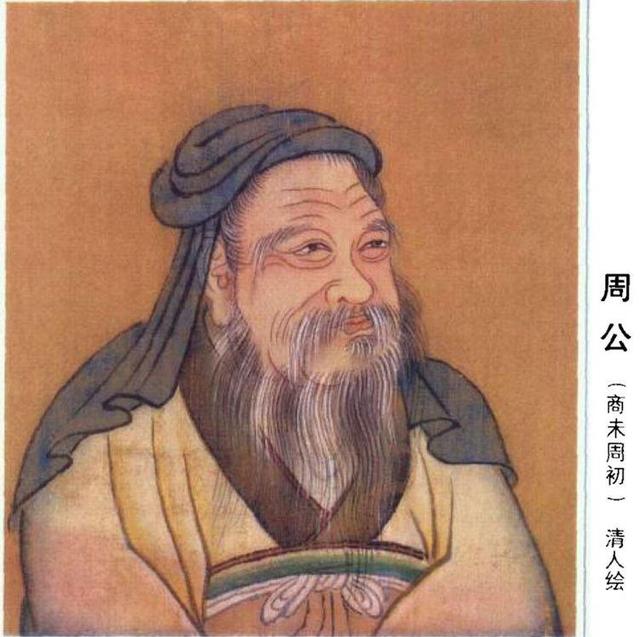 周公(资料图 图源网络) 以道德立国,始于武王克商之后周公推行的新政。钱穆先生说:“意殷末周初,实产出春秋、战国时代之文化的渊源之涵养期也。决非枯澹寂寞,而郁勃有兴国之气象焉。周公者,又其时代思想之最好的代表人也。”王国维先生云,周公制礼作乐“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杨向奎先生说,“周公之造‘德’,在思想史上、政治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大事”,“他是以德政为操持政策的机柄,因而减少了上天的权威,提高了人的地位和人的尊严”。赵光贤先生说,“把‘明德’、‘敬德’当作一个政治口号提出来,应当说是从周公开始”,并归纳《尚书》周初诸诰所见周公提倡之德,“从积极方面说,是教育、孝友、勤劳;从消极方面说,是慎刑、无逸、戒酒”。从殷纣暴政走向周代德教,无疑是一伟大的转折,但毋庸讳言,此时的道德论尚处于草创阶段,体系粗疏,尚未及于理论思维的层面,更未形成精细的理论架构。 进入春秋以后,王纲坠失,征伐四起,德治不再,世局丕变。受时势的刺激,思想界关于道德的讨论悄然兴起。就《国语》、《左传》等文献所见,社会贤达提及的德目,不仅数量大增,而且每每伴有简略的论述,以此作为对人物、事件作道德评价之标尺。如周大夫富辰对襄王说,古之明王有“仁、义、祥”三德,欲使周室内外皆利,当遵奉“尊贵,明贤,庸勋,长老,爱亲,礼新,亲旧”(《国语·周语中》)等“七德”;内史叔兴父奉襄王之命,与大宰文公同往锡晋文公命,归来后赞扬晋侯能恪守忠、信、仁、义,建议襄王善待之:“且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义所以节也。”(《国语·周语上》)晋悼公十余岁时前往周朝国都洛邑,师事单襄公,其间“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义必及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辩,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让必及敌”(《国语·周语下》),一身而兼十一德,显示了很高的素养。如此之类,不胜枚举。 及至战国,关于道德的讨论,已不再满足于就事论事或者简单的系联,而能深入腠理,开始探究道德偏颇的问题。《尚书·皋陶谟》记禹与皋陶的谈话,学界多认为此篇作于战国,至确。皋陶论帝王之责在知人与用人,“知人则哲,能官人”。人性有不同,但总括而言有九德。皋陶认为,“天命有德”,若能“日宣三德”,每日宣明其中三德,早晚谨慎奋勉,大夫就能保有其家(采邑);若能“日严祗敬六德”,每日恭敬地践行其中六德,诸侯就能保有其邦;若能“九德咸事”,普遍推行九德,使有才德的俊秀都在官位,百僚互相效法,顺应天时,就能成就所有的政务。禹请问九德品例,皋陶云: 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上述九句,均以“而”字居中,前后各有一字。前九字之义,郑玄解释说,“宽谓度量宽弘,柔谓性行和柔,扰谓事理扰顺”,“愿谓容貌恭正,乱谓刚柔治理,直谓身行正直”,“简谓器量凝简,刚谓事理刚断,强谓性行坚强”。足见前九字均是美德。既是美德,为何还要在其后再各附一字?前九字与后九字是何关系? 郑玄认为,前九字与后九字是一德之两面、上下相兼的关系:“凡人之性有异,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协,乃成其德。”孔颖达疏申述郑义:“是言上下以相对,各令以相对兼而有之,乃为一德。此二者虽是本性,亦可以长短自矫。宽弘者失于缓慢,故性宽弘而能矜庄严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注疏之说认为,前九字与后九字之义并立,两者互足,各成一德。但前九字与后九字区别何在,则语焉不详。 清儒孙星衍认为两者有轻重关系,前九字是行,后九字是德,并引《周礼·师氏》郑玄注“在心为德,施之为行”解之:“行谓宽、柔、愿、乱、扰、直、简、刚、强之行。九德谓栗、立、恭、敬、毅、温、廉、塞、义之德,所以扶掖九行。”孙氏对前后九字作整体区别,而以“行”与“德”分领之,前者属于正当行为,后者表明前者已进入道德层面,两者有精粗、高下之别。 孙说虽巧,然未必为是。其一,就《皋陶谟》文本而言,前九字与后九字并无一一对应的高下关系,如直而温,正直而温和;宽而栗,宽宏而庄栗;简而廉,刚毅而无虐等,是否就能说前者为行,后者为德?显然不能。其二,《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民,一为“六德”,二为“六行”。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两者完全没有对应关系,无法如《皋陶谟》“九德”,以“而”字前后系联成对。其三,郭店楚简《五行》篇提及行与德之行: 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智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五行》强调行有“形于内”与“不形于内”之别。形于内者,德已内化为生命体之一部分,德与行浑然一体,堪称“德之行”。反之,仅是行为符合道德要求,但非由心出,则称之为“行”。《五行》此说,既未将德与行列为具有递进层面的关系,更未如《皋陶谟》用两组文字说德行。故孙说不可从。 金履祥以上九字为资质,下九字则进修,而合为九德,并解释必以二字合德的原因: 宽者易弛,宽而坚果则为德。柔者易弱,柔而卓立则为德。谨厚曰愿,愿者易同流合污而不庄,愿而严恭则为德。治乱曰乱,乱者恃有治乱解纷之才则易忽,乱而敬谨则为德。扰者驯熟而易耎,扰而刚毅则为德。直者径行而易讦,直而温和则为德。简者多率略,简而有廉隅则德也。刚者多无蓄,刚而塞实则德也。强者恃勇而不审宜,故以强而义乃为德也。资质乃是人的德性自发流露,具有先天属性。进修,则是认知主体在后天的进德修身。从良好的资质出发,经过自身的修为而及于德性圆满的境界,方是真正的“德”。其说与郑玄之说近似。 无独有偶,《左传》有一段话与《皋陶谟》九德句式相似,可资参验。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聘鲁观周乐,乐工为之歌各国之《风》及《小雅》、《大雅》,季札逐一评说。及至乐工歌《颂》,季札听后大为赞叹: 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畣,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从“直而不倨”至“行而不流”凡十四句,皆是赞美王者的完美德行,每句“而”字之下均有一“不”字,孔颖达《左传正义》云:“皆下字破上字。”此句式与《论语》“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相若,旨在突出德行正而不失;而《皋陶谟》“某而某”句式意在强调正而不偏,有异曲同工之妙。孔颖达疏解道:人性直者易于倨傲,而“王者体性质直,虽富有四海,而不倨傲慢易”;在下之物多因曲而屈桡,而“王者曲降情意,以尊接下,恒守尊严,不有屈桡”;相近者失于相逼,而“王者虽为在下与之亲近,能执谦退,不陵逼在下”;相去远者失于乖离,“王者虽为在下与之疏远,而能不有携离倩疑在下”;数迁徙者失于淫佚,而“王者虽有迁动流去,能以德自守,不至淫荡”;去而复反则为人所厌,而“王者政教日新,虽反覆而行不为下之厌”;薄哀者近于忧愁,而“王者虽遇凶灾,知运命如此,不有忧愁”;乐者失于荒废,此“乐而能不荒废也”;用之不已,物将匮乏,此“用而不可匮也”;志宽大者多好自宣扬,“此虽广而不自宣扬也”。好施与者皆费损财物,“此能施而不费损也”。取人之物失于贪多,“此虽取而不为贪多也”。处而不动则失于留滞,此“虽久处而能不底滞也”,王者能相时而动,时未可行,虽复止处,意不底滞。行而不已则失于流放,“此虽常行而能不流放也”,王者能量时可行,施布政教,制之以义,不妄流移。由孔颖达此疏,可知《皋陶谟》“九德”与季札所论相通,都是说德性圆满。 “颂”乃圣贤至治之极的乐曲,峻峭而圆融的德性与庄严的艺术形式兼具,用于宗庙,播之万世。此十四句所涵盖的内容,比《皋陶谟》“九德”更为严密与完备。由此足见,古人追求道德完满,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要求人们既要提炼自身先天的资质之美,又要以后天的修为克服先天美质的局限,走向理性而圆融的道德境界。 节选自彭林先生《儒家乐教与德性圆满》,《文史哲》(济南)2013年6期。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古代离婚讲究“好聚好散”
- 下一篇:什么是行“周公之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