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为现代儒学定位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1:11:18 儒家网 newdu 参加讨论
为现代儒学定位 作者:任剑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来源:《科学时评》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五月初七日己未 耶稣2017年6月1日 近几年大陆新儒学的一些朋友,尤其“新儒教”的朋友把自己的立场设定为否定“新儒学”——不仅仅是港台新儒学。新儒学其实不止港台,因为新儒学第一代出去的不多,第二代最有学术成就。 回应“现代”的不同方式 整个说来,现代新儒学要应对的问题是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变之际,怎样使儒学的言说应对这种变化?这是现代新儒学之为现代新儒学最重要的理论表征,如果丧失了这个表征,可以说是处在纯粹时间概念的“现代”的儒学言说,但不等于是现代新儒学,因为你可能没有对现代转变的处境做出回应。 这其实有三种知识立场,第一,是反现代的新儒学,可不可以?可以。在这一点上,我并不认为一定要是为现代辩护的新儒学,我主张学术研究的无禁区。 第二种立场是反现代新儒学的“现代新儒学”,就是你那种现代新儒学不够现代,我这个才更现代。比如大家批评的蒋庆,蒋庆的政治儒学设计显然是现代性的,他那套言说在公羊学传统里是找不到的,而且他要应对中国国家政体建构的结构性转变,所以他的这种设计会有现代——西方的现代和西方的传统两种政体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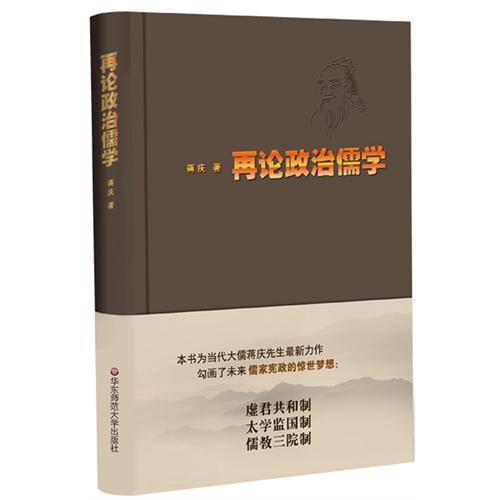 我对蒋庆儒家三院制的归纳很简单,国体院和庶民院接近于上议院和下议院,或者参议院和众议院,这种设计没有什么新颖性,特殊之处在于增加了通儒院,加在一起就是三院制。这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想法,因为通儒院说到底就是要在政治运作的实际权力之上提供直接正当性的政治控制机制,就是“只有我们儒者能够来裁制”,这实际上就是中世纪的政教合一,要注意这是一个重大变化。 无论讨论内圣还是外王的问题,其实都是儒家中人的知识立场或者政治主张,因而并不是一种政治操作。我也认为,蒋庆给予董仲舒较高的评价可以理解,因为什么?董仲舒想以儒家的混合性价值立场和主张来限制王权,但是没有一套政治建制,这正是反“现代新儒家”的现代新儒家要去解决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说他没有可行性,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是第二种立场。 东西方都经历古今之变 第三种立场就是混淆传统和现代的“现代”的立场,就是我们一方面可以把中国的现代转变时限上提得很早,空间上漫无边际,有讲“我们秦代就有现代国家的经验和基础”,加上福山出版《政治秩序的起源》,给我们以巨大鼓舞——国际知名的政治学家都这么说,现代国家的三大支柱,行政管理体制的国家、法制和责任制政府,我们春秋战国至少到秦时已经有了。 但是在我看来,这样一种时间上将现代无限提前,无论是福山或是国内同样的论著,都没有意义。因为现代之为现代,其实不单纯是中西文化冲突维度上西方的现代跟东方的传统的对峙,更为关键的是,对于西方而言,现代也是断裂的产物。我们通常以为西方“两希”融合就顺利地发展出了现代,以为其与中国的传统当然就是碰撞的、冲突的,这是汉语学界的最大误会,其实是错的。即使从古代西方的立场来看,西方的现代也是陌生的。 比如说,大家习惯将西方现代的市场经济追索于希腊雅典的商业天才,而新近的研究表明,在整个雅典做生意的人不超过百分之三,大多数以不做生意为荣。大家想象了一下,往前扩展就会把一种现代社会的结果去无限地前推,推到以往的社会群体。同样的,雅典的民主政治与现代的民主政治的差异之大简直是天渊之别,我们不用去做太多的考证,因为讨论已经相当多了,已经成为一种常识。更关键的是,学界所认为的现代之为现代的四大特征——工业、技术、军事(现代的战争手段)和惩罚的体系化,在西方古代是绝对找不到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划分古代、现代最为关键问题在哪里呢?第一就是学者赵寻强调的,试图要把儒学面对的政治史、社会史、观念史的复线勾勒出来,这个复线在中世纪晚期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城邦国家到世界社会,再到基督教帝国,这时人类社会的群体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于古人而言完全是陌生的了。因为在古代,战争是建立所谓国家的形式结构的唯一手段。 比如说汉代与匈奴的战争,匈奴人没办法了,一路扫荡到欧洲,这是西方对黄种人畏惧的第一次记忆。我们今天因为1840年以来的历史,只强调欧洲的侵略,但忘记了历史上黄种人曾让欧洲闻风丧胆。 西方现在还怯怯地讲“帝国史不是中国的朝代史”,其实他们很畏惧。按照古代的征服逻辑,如果承认黄种人跟我们有不可切断的种族和血缘关系乃至于文化关系的话,那就应该承认民族是国家建构的主体。以民族作为国家主体结构的主体,那么领土、主权、文化就变成了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形式元素,至于政体上的选择,那要看政体选择的诸因素以及民族政治发展的运气。 我们以前很少讲民族政治发展的运气问题,这个运气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民国初年,我们作为亚洲第一共和国,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共和国的架构,但是这个民族运气不够的是,所有政客都不愿意被归顺到现代政体上来,袁世凯一复辟,张勋也复辟,民国时占据国家高位的人帝王思想太浓厚了,这就是运气不够。当时知识界也认为我们应该有现代政体选择,但它就落实不下来。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上讲,它应该落实下来,但偶发性因素就是使它落实不下来。这就是运气与诸条件不匹配的问题。 对儒学必须重新阐释 今天大陆思想界讨论新儒学最大的麻烦就是,我们的视野不如上个世纪初年兴起的现代新儒家,也不如后来转移到海外的港台新儒学家,他们深刻地省悟到,现代社会的结构性转变是人们无可奈何的。因此在价值取向上,他们对儒学必须要有重新的阐释。 大陆一批新儒教朋友批评说,现代新儒学受“五四”影响太深,我认为这种说法太笼统。我一向批评国内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混为一谈。新文化运动面临的核心问题,是面对我们文化双重乱了方寸的挑战,该怎么办? 为什么说双重乱了方寸?第一,传统已经解决不了中国现代的问题;另外,一想到宏观设计就想找个靠山。我有时候提醒“新儒教”的朋友们:你们是欺软怕硬,你不知道从制度上终结制度化儒学的是清政府自己——1904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远在辛亥革命前六年,1905年正式终结科举考试。 终结科举考试的意义远比办《新青年》的那几个人进行文化批判要重要得多。为什么你们就不批判清政府在这个时候不改革呢?其实学堂制度、书院制度也可以在以前的基础上改良的嘛。可清政府就是不愿意,历来都是非常功利地拿一个有利于维持统治的法宝在手里捏着。 学者们这时也恰恰是拣软杮子捏,文化学者之间互相捏。能不能在现代国家建立时,在政治立约之际,把握住问题的核心?你去捏当时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捏不了你就是非现代的,价值非常有限,无益于促进中国的现代转变。 对中国而言,晚清是一个路口,民国是一个路口。我们今天向前挺进,可以遵循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基本价值选择,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现代新儒学的价值定位就在于,它适应了人类的现代变局。我现在已经不愿意把现代新儒学只看作是中国特有的现代转变,我特别反对中国的学者思考问题时喜欢加上“中国”两字,马基雅维利写《君主论》,没有写成《意大利君主论》,洛克没有写成《英国政府论》,为什么?因为以民族国家建立起来的这样一套价值体系或权利体系,这是都普遍适用的。 早前几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发在《开放时代》2011年第3期,后来收在台湾大学出版的《复调儒学》里,特别谈到普遍主义的形成比古典普适主义——实际上是区域主义,因而是特殊主义——在现代有巨大的拓展,因而现代新儒学之为现代新儒学,就在于它的普遍主义立场适应了现代的转变。 如果你要保有现代新儒学的“反现代新儒学”或“协调与模糊传统的新儒学”这类立场,去为中国的当下处境作一种筹划,我觉得要么就是没有良心,要么就是知识判断有相当的问题。 内圣归内圣,外王归外王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回过头来看,现代新儒学在大变局时产生了重大分裂。我现在并不想简单地去区分谁的判断更清晰,因为可能只要一得出简单的结论就会流于一个立场的宣示。但很显然,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说,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对中国现代转变的坚持,以及对现代国家建构的清醒,显然要更清晰,这不是一个价值评价,而是一个事实描述。 他们必然发现,无法沿着康有为等人所期待的道路向前挺进,只能沿着学术的道路进行文化的申辩。因而,理性的建构便成为他们唯一能够有作为的舞台。这个时候,他要解决中国传统、现代转变的压力,尤其是现实治理转变的压力,但一帮文人有多大能力去推动转变? 我常说,只要看看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在政治上的极端幼稚,就不会对康有为抱有太高期望了。我最近写了一篇《共和与国情》,专门讨论康有为两篇关于共和主义表述最明确的东西,一个《共和政体论》,一个《共和评议》。康有为完全是预设一些虚君共和理念,然后绑架国情,认为中国也应该虚君共和。我说,此国情非彼国情,英国可以搞虚君共和,在中国,当时就只能搞实君专制,虚君绝无可能。为什么?没有一种社会力量能与君王抗衡而达成契约的可能。 《洪范》是观念性的,可以达到对古典政治治理的约束,因为古典治理是伦理性的,因而可以发挥作用。但在我看来,在现代的处境下,内圣外王的问题必定要经历分裂,内圣的归内圣,外王的归外王。谁要想开出或转出,那就是一场现代迷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