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13)
http://www.newdu.com 2025/05/21 05:05:45 中国儒学网 黄玉顺 参加讨论
三、境界 下面,我就正式地来讲一下我所理解的“境界”。 通常我们谈“境界”的时候,应该说,孔夫子关于他自己的一生的回顾,一番“夫子自道”,是一种非常值得重视的表述。顺便说说:孔子虽然是按照年龄来陈述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境界跟年龄之间具有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一个人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而另一个人可能终身都处在一个很低的境界。 大家知道,孔子是这样讲的: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历代儒家对孔子这段话都是非常重视的,作出了很多解释。但是这些解释之间,却有很大的出入。当然,这里有一个“阐释学”的问题,那就是说,在解释的时候,我们带了怎样的观念去理解、把握。 要透彻地理解境界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分辨清楚观念层级之间的“生成关系”和“奠基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境界层级之间的关系。这样三种关系,对照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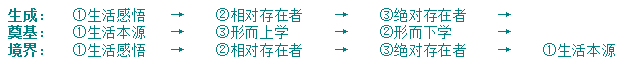 生成关系:在生活本身的本源情境中,生活感悟显现出来;在生活感悟中,形而下的众多相对存在者、“万物”得以生成;又在对万物的终极根据的追问中,形而上的唯一绝对存在者、“道之为物”得以生成。----这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一般的观念层级生成关系,就是老子所说的“无中生有”。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体验:我们在生活中原是“不知不觉”的;然后首先成为一个形而下的存在者,并且可能终身都是这么一个形而下的存在者,一个功利的人、道德的人,一个常人、君子;在此之后,我们中的某些人可能会有形而上存在者的追寻,追寻形上之“道”、天命之“性”、“天理”、“理念”、“纯粹意识”、“上帝”等等之类的“本体”、“终极实体”。 奠基关系:但是,因为在我们的追问中,形而上的唯一绝对物是作为形而下的众多相对物的根据而出现的,因此,在所谓“奠基关系”中,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原来那种生成关系被颠倒了:形而上学反倒成了为形而下学奠基的东西。不论是康德、还是海德格尔,他们在追问奠基问题时,都是从这种颠倒的观念出发的:康德说,形而上学为科学奠基;海德格尔便接着说,源始的生存经验为形而上学奠基。在这种意义上,西方哲学的“奠基”观念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倒见”,因为,这样的叙述并不符合观念层级的生成过程的事情本身。当然,如果仅就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之间在观念上的支撑关系的角度来看,说“形而上学是为形而下学奠基的”也不算错,在这个意义上,“奠基”这个概念还是有其意义的。但我们须得注意:“奠基”的观念可能妨碍我们对“境界”观念的理解。 境界关系:实际上,境界层级之间的关系是跟观念层级之间的生成关系一致的;区别仅仅在于:观念的生成关系到形而上的绝对存在者为止,不再推进,而只是就此回过头来解释形而下的相对存在者,这正是原创时期或轴心时期发生的事情,唯其如此,人们才会“遗忘存在本身”、或者“遗忘生活本身”;而境界的追求则继续可以推进,由形而上学而重新回归生活本源。 在我看来,境界问题的实质,在于个体人格的回归。首先,一般来说,境界总是说的某个人、某个个体的境界;其次,这个人的境界,是说的他在观念层级上的回归。境界就是回归,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为什么这样讲呢?这是因为:境界的进程,跟我们前面所说的观念层级的奠基关系的进程,正好是相反的过程。联系到孔子的自述、老子的观念,以及冯友兰的境界说,境界层级的提升进程和观念层级的奠基关系之间,是一种逆向关系,见下见表:  这样,我们才能够透彻地理解孔子的那番自述。孔子的自述,跟老子的说法也是具有对应性的:“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复归于无物”。(《老子》第16、14章)“万物并作”意味着众多相对的形而下存在者;“复”则意味着回归,首先是回归到那个唯一绝对的形而上存在者;最后“复归于无物”是更彻底的回归,回到“无”,回到存在本身。老子还有一段话,“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返)”(《老子》第25章),过去人们说那是在说“物极必反”的所谓“辩证法”,其实,这里还是在说境界问题。首先,这个“大”是说的作为形而上存在者的道,“有物混成,…… 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其次,从观念层级的生成看,“道大、天大、地大、王(人)亦大”,这是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过程;最后,则是境界问题,就是这个过程的逆向回归,“人(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 我们知道,在儒家的境界学说中,冯友兰的境界说是最著名的。我说过,在冯先生的新理学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境界论。但是,在我看来,这样的境界论还是不够彻底的,没有突破形而上学的观念,没有真正地回到大本大源。区别于此,我在谈自己的境界观的时候,采取了另外的说法:自发、自为、自如。这些词语的含义,下面再具体地讲。 境界这件事情,也是由我所说的“生活本身的本源结构”----“在生活并且去生活”决定了的:我们首先在生活,我们一向就在“无意识”、“无觉解”地生活着,也就是说,我们自发地生活着;然后我们去生活,我们获得了“觉解”、“自我意识”,我们成为一个形而下的存在者,追寻形而上的存在者,也就是说,我们自为地生活着(不过,通常,一般人的自为的“去生活”,只是作为形而下的存在者的生活,达不到形而上的境界);最终,我们大彻大悟,回归生活本身,回归纯真的生活情感,也就是说,我们终于自如地生活着。 1.自发境界:在生活 我首先作了一种区分。什么区分呢?我这是借用了冯友兰先生的一个词语:“觉解”。我所说的区分,就是“有觉解”和“无觉解”的区分。实际上,在“十有五而志于学”之前,孔子就已经处在了一种境界之中,那就是冯先生所说的“自然境界”,就是没有觉解的境界。冯先生说,处在自然境界当中的人,无觉解。就像一个小孩,说得好听一点,是“天真烂漫”;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浑浑噩噩”。反正是:无觉解。然后,我们才进入了有觉解的境界,诸如“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乃至“天地境界”什么的。[1] 就孔子来看,大约在他十五岁的时候,有了一种觉解,一种自觉性。这种自觉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志于学”。但是,我们不能说孔子在“志于学”之前就什么都没有,不能说孔子在这之前就没有生活感悟。那怎么可能呢?你不能说在这之前孔子就没有“在生活”,没有一种生活情感,一种生活领悟。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会说:其实恰恰相反,对于孔子来说,冯先生所说的“自然境界”,“无觉解”的,那才是他的本源处。那个十五岁而“志于学”的孔子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由生活本身所给出的。 可惜,现在这个方面的史料很少。比如,我们看《史记·孔子世家》,里面只是零零星星地对孔子早期的生活有一些记载,包括孔子和他的母亲、父亲的一些故事,很少。当然,司马迁在记载的时候,不会说孔子当时有什么“生活感悟”。但是,我们在读《孔子世家》的时候,是有那么一种“感觉”的,只是无法说清楚;就算说清楚了,可能也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承认,这个时候孔子是无觉解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那时没有生活感悟。很多事情,我们是可以设身处地去体验的。比如,孔子从小就喜欢玩什么游戏,例如礼仪的游戏,他在这些游戏中领悟到了什么。还有,孔子从小不知道父亲是谁,而母亲却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性。如此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地方。假如让我去写孔子早年的一些事情,我无法用很学术化的方式去写。但是,我可以用今天所说的文学化的、诗化的方式去写,去传达我的一些“同感”。 我们不得不承认,恰恰是在早年的那么一种生活样式当中,尤其是那么一种情感生活当中,孔子这么一个人,才被给出来了;孔子这么一个“志于学”“志”,才被给出来了。尤其是这个“志”,就跟“诗”有关。以前毛亨讲诗,这个“诗”被他形而上学化了,他说:“诗者,志之所之也。”(《毛诗·大序》)用我们今天的话语来表达,“志”表示的是心理的指向性。我们今天有很多类似的词语,比如说“意志”。意志就是一种心理指向性,就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意向性”(intention)。毛亨还说到“之”,就是“往哪里去”的意思,意味着有目的性。不仅如此,还是“所之”,这就是我刚讲过的“能-所”的结构:“志”是“能”,是主体;而“所之”是“所”,是对象。所以,我会说,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这样的一种境界,是有目的、有意志的。这就意味着:这是一种主体性的行为。所以,我说,你从毛亨这句话里面,看不出孔子所说的“兴于诗”。其实,这个“志”绝不是“诗”的前提,恰恰相反,“志”是被“诗”给出的。这也是我讲过的问题:主体性是被本源性的情感给出的。 因此,孔子必定从小就在读《诗》。这是肯定无疑的。孔子后来老是叫学生读诗,是有他自己的切身体验的。至于他晚年才开始整理《诗经》,那是一种学术化的工作。这种学术化的工作,离诗本身反而越来越远了,直到汉代建构起来的诗学,反而不行。 我只是说,笼统地说,十五岁之前,孔子有他的生活感悟,这和《诗》是有关系的,和他个人的生活情感也是有关系的。正是在早年的这么一种生活当中,孔子之所以为孔子,这么一个存在者,这么一个“此在”,被给出来了。然后才有了主体性的自觉性,这就是“志于学”。孔子讲“学”的地方太多了,要学的东西也太多了,但是无论如何,在任何意义上,《论语》里面,孔子在讲到“学”的时候,那一定是一种目的性行为、主体性行为。总而言之,孔子在生活,他一向就在生活,那么,他就不能没有生活情感、生活领悟。 这类似于冯友兰所说的“自然境界”。但我不把这种境界称为“自然境界”。我称之为“自发的境界”。所谓“自发”,也可以叫“自在”。这是我给这种境界的一个我自己的对应性的说法:这就是“自在”的问题。不过,这不是西方人、比如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那个“自在”,而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自由自在”的意思;也不是佛家所讲的那个“大自在”,而是日常口语当中的“自由自在”。这么一种“自在”,我们用冯先生所说的“觉解”这个观念去看它,当然是没有觉解的。因为,冯先生那里的觉解,要么是形而上学的,要么是形而下学的;它特别是一种认知的观念,知识的观念。那么,自在的境界当然是没有觉解的,一点儿都没有。这就是冯先生所说的“自然境界”,其实是很“本真”的境界。这样的境界也是一种自由境界,而且是本源性的、“自由自在”的自由。我经常这样讲“自由”:全部的自由的源泉,----形而下的自由、形而上的自由的源泉,就在生活本源当中,就在生活本身的那种本源结构----“在生活并且去生活”当中。我们“去生活”,去创造、去建构,那是一种主体性的活动,当然是自由;但是,那首先是因为我们“在生活”,我们这种主体性是被生活给出的。“在生活并且去生活”,这是一切自由的本源。你自在,所以你自由;也可以说:你自发,所以你自由。这就叫做“自由自在”:自在的自由,自发的自由。 2.自为境界:去生 对于孔子一生的境界的转进,跟冯友兰先生的说法相对照,我一般是做这么一种划分: 1.自发境界 ---- 自然境界 2.自为境界 ①“志学”---- 功利境界 ②“而立”---- 道德境界 ③“不惑”---- 天地境界 3.自如境界 ①“知命” ②“耳顺” ③“从心所欲” 在自发境界之后,是自为的境界。“自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主体性、目的性。在冯先生的说法中,这是对应于“功利境界”、“道德境界”的,因为不论功利行为、还是道德行为,都是主体性、目的性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君子”和“小人”或者“常人”并没有区别。 (1)志学 我刚才说了,“志”意味着一种自觉性,意味着目的性、主体性。不仅如此,“志”也意味着一种功利性。这就是我把它跟冯先生所说的“功利境界”相对应的理由所在。 “志”的功利性,应该说是不言而喻的。“功利”并不一定意味着“自私自利”,比如英国的功利主义,边沁的功利主义,那是大家知道的。以前毛泽东一边讲“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边坦然承认“我们是功利主义者”。他说的是“大功利”,不是个人的、私人的功利。过去人们总是以为儒家不讲功利,其实那是一种误解。《周易》里有一种说法,很有意思的:“利者,义之和也。”(《周易·乾文言》)《周易》古经,几乎满篇都在说“利”。《尚书》还讲“正德、利用、厚生”。(《尚书·大禹谟》)《大学》所说的“亲民”,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样是一种功利。现代新儒家也很注重这一点,把“正德利用厚生”跟“科学技术”联系起来。[2] 这些都是功利,而且是“大功利”。 孔子之“志于学”,就是一种功利。而且,在孔子那里,既有大功利,比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也有小功利,比如说,对“榖”“禄”的正当谋求。孔子教子张学“干禄”,“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这就是小功利。孔子叫学生“无见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那是谋“大事”、求“大利”。但是,孔子并不否认“小利”。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个表述里,首先是“己欲立”“己欲达”,这是小功利;然后才是“立人”“达人”,这才是大功利。 (2)而立 如果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相当于“功利境界”,那么,“三十而立”是说的达到了另外一种境界,相当于冯先生所说的“道德境界”。当然,这里的“道德”要作广义地理解,泛指一切社会规范,也就是儒家所说的“礼”。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三十而立”,你“立足于”哪里呢?孔子说:“立于礼。”(《论语·泰伯》)《论语》里面,孔子在说到“立”的时候,通常都是说的“立于礼”的意思,不信你们自己去看。那时所谓“君子”,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遵循“礼”,即遵守道德规范、政治规范、法律规范等等。按冯先生的意思,人首先是一个功利的人,然后才可能是一个道德的人。但是,严格来讲,所谓“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并不是两个不同的境界层级,不能把“功利境界”跟“道德境界”对立起来。我刚才就说过,功利未必是不道德的,道德未必是不功利的。 再者,我说,不论是功利境界、还是道德境界,处于这种境界当中的人,在观念上都是形而下的存在者。在这一点上,这两种境界是完全没有区别的,都是形而下的境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记得我谈到过的:不要把道德规范看得太高,“礼”都是可以“损益”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应该藐视道德、不要道德。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需要道德。我们总是道德地生活着,也就是说,我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某些道德原则。问题在于:那是怎样的一种道德原则?道德源于生活样式,它是历史地变动的东西。康德把道德看得那么高,那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想说的是:先行于遵守道德的,首先是建构道德。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状况来说是特别要紧的:我们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重建道德。 虽然如此,这样的形而下的境界却是我们“去生活”的开端。所谓“去生活”,就是一系列的超越:超越自发境界,进入自为境界;超越形而下的境界,进入形而上的境界。当然,我们还要继续超越:通达自如境界,回归生活本身。那么,我们首先是这样去生活的:成为一个功利的人、道德的人。 (3)不惑 “十五志学”,是“兴于诗”;“三十而立”,是“立于礼”。这时候,我们遵守着道德规范;但是,我们不一定明白为什么就该这样做。这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就像前些年人们所讲的那样:“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就是纪律、规范、道德对于一般人的意义:遵守,但未必明白。不明白,就是“惑”。孔子说自己“四十而不惑”,那意思就是说:到四十岁的时候,他对于“礼”,不仅“立”于它,“知其然”了,而且也“知其所以然”了,“不惑”了。 那么,如何才能“不惑”呢?如何才能明白、理解“立于礼”这件事呢?让我们回到我一开始就讲的“观念的层级”上去。“礼”作为规范,那是众多相对的存在者的事情,是形而下的存在者的事情。我们要理解这样的形而下的存在者,那就要寻求这种众多相对存在者的终极根据,这个根据,就是形而上的存在者。这个唯一绝对的存在者,在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观念中,就是“天地”。 “天地”作为形而上的存在者,就是本体,就是万物的根据,这样一个观念,乃是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的一个根本的观念。我刚发表的一篇文章,讲“绝地天通”的,就是讲的这个观念:天与地的分离,人与神的隔绝,叫做“绝地天通”,那是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建构的开端。[3] 这也就是《易传》所说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周易·系辞上传》) 所以,“不惑”的境界就相当于冯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他称之为“天地”境界,那绝不是偶然的。在冯先生那里,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都是形而下的;按冯先生一向的观念,我们要达到最高的境界,形而上的境界。这个最高的境界,就是天地境界。 我的看法是,在现代新儒家这里,虽然冯友兰先生正式讲“境界”问题,但实际上所有新儒家都在讲这个问题,都是在说要达到一个至高的境界。这个至高的境界,不外乎就是与“本体”同一、“与道为一”的境界。这种境界,简单来说,就是超越分别相。但是,超越分别相并不意味着通达了本源。因为,不仅本源是超越分别相的,而且作为世界终极根据的本体也是超越分别相的。所以,我把冯先生所讲的“天地境界”归为形而上的一种境界。 其实,在我看来,这个境界不是最高的。轴心时期以后,古今中外的很多宗教神学家、哲学家都表达过这样的境界。比如基督教里面的“归于天国”之类;儒家也有什么“与天地参”(《中庸》)等表达。这种境界,其实就是李翱所讲的“复性”。这种观念,在宋明理学家那里有些表达,这些表达,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不同层级的解释。比如,程子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二程遗书》卷六)对这个说法,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在哲学本体论意义上,它是说,这是唯一绝对的存在者,这就是未有“天”“人”之分的状态。当然,你也可以很本源地去阐释,但我一般不这么看。我把它归属于形而上学的观念。那么,在境界论意义上,就是复归那么一种境界----天人同一的境界,也就是形而上的唯一存在者、绝对物的境界。 这样的境界,道家讲“成仙”,佛家讲“成佛”,不是谁都可以达到的。对于儒家来说,似乎就是成为“圣人”了?我并不这样看。我对“圣”有另外的看法。 3.自如境界:回归生 我会说,“圣”是另一种境界:自如的境界。那是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以后的境界。在儒家的观念当中,我会把这个自如的境界理解为:那就是重新回到“自由自在”的本源情境,回到生活本身,回到纯真的生活情感本身。那么,怎么回到生活本身呢?孔子就是这样表达的:“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里涉及到几个很关键的词语:“天命”、“耳”、“心”、“欲”、“矩”。我们一一来看: (1)知命:领悟生活 首先是“知命”----“知天命”。那么,“天命”是什么意思?我首先要说:“天命”不是“什么”。但是,一般后来的理解,包括“文化大革命”中对孔子的批判,都是把“天命”理解为“上帝的意志”之类的。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结果。 这首先涉及到:怎么来理解这个“天”。冯先生讲过很多“天”,讲了“天”的很多意义,分门别类的含义。[4] 那种谈法,其实是很糟糕的。那是把“天”把握为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存在者。还有李申写的《中国儒教史》,也把“天”理解为一种最高的意志。当然,也不是说这样的理解全然都是不对的,因为“天”确实曾经被这么理解了。老百姓甚至有一种很人格化的理解,比如我们日常口语里的说法:“老天爷”。所以,“天”被理解为至高无上的存在者,这确实也是观念史上的一个事实。但是,问题在于:同样是在中国观念史上,“天”只能被这么理解吗?我们应该怎样更加本源地去理解“天”?我一再强调,儒家文本里面出现了很多词语,它们的含义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在不同的语境中,它们可能说的是不同的事情。比如“仁”这个概念,我说过,有的时候说的是形而上的东西,有的时候说的是形而下的道德原则,而有的时候说的是非常本源的事情。对此要作区分----观念层级的区分。“天”也是一样的要作区分。 怎么理解“天”?孔子有一个说法,很值得玩味。我从“命”字说起,再说孔子讲的“天”。“命”是一种言说,就是“口令”。这是很明白的,汉字“命”本来就是这样构造的。但是,这个“口令”难道就是“天”在那里“发号施令”吗?不然。孔子却说:“天何言哉?”(《论语·阳货》)[5]“天”一边发“口令”,一边却又“无言”,这似乎是一种矛盾。我是说:孔子讲“天何言哉”,但是他又称之为“命”,这似乎是一个矛盾。但是,我这样说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是:我已经把“天”理解为了一个存在者。我们说“天是要说话的”,意思是在说“老天爷”、“上帝”这样一个会说话的存在者。然后,我才能说:“天何言哉”而又能“命”,这是一个矛盾。还有,很多人这样来理解孔子这句话,说:孔子这里说的“天”是“大自然”,nature,所以它不说话;然后又在“命”,那只是一种比喻。但是,所谓“大自然”还是一个存在者、或者是一个存在者领域。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过去这么理解,总是把“天”作为一个存在者。 但是,我更愿意这么来理解“天”,就是“自然”;但不是什么“大自然”,而是中国人讲的“自然”。我经常讲这个话题。谈“自然”,儒家谈,道家也谈。在汉语当中,“自然”不是一个词,而是一个词组,就是“自己如此”的意思。[6] 当然,这样讲仍然会导致一些模糊之处。比如,我们在现象学语境当中谈“自己如此”的时候,仍然会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在胡塞尔那里,“自己如此”可以理解为“自身所予性”(Selbstgegebenheit),那么,我会说:这个还有一个形而上的存在者。另外一种理解,是海德格尔式的理解,似乎是对应于“存在本身”、“生存领会”什么的。不过,海德格尔也有他的问题,也有他的不彻底性。这是我讲过很多次的了,就不再讲了。 我更愿意采取道家的说法:“自然”是“无”。这就意味着:自然就是真正的存在本身。这就回到了我在第一次讲座上上所讲的那个观念上去。自然不是什么“自身所予性”,而是“无”,就是“无物”;对于儒家来讲,自然就是先行于存在者的生活本身、情感本身。我说:有各种各样的爱的情感的显现样式,这些样式就是自然----自自然然、自然而然。这样的自然,就是自己存在,而与任何形而上的根据无关,也与任何形而下的东西无关。自然先行于这一切。这才是真正的“大自然”。 因此,“天”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存在者。所以,这个“天”之“命”,我会说,就是生活本身在说话,但是在无声地说话。虽然无声地说话,我们却倾听着。在中国的观念中,有很多词语,都和说话有关,这不是偶然的,这意味着,我们的远古先民,一定有那么一种领悟,---- 这种领悟和认识无关,完全不是认识,而先行于任何认识。就是说,他似乎听到了什么。可是他什么都没有听到;但他确确实实感觉自己听到了什么,他感觉自己只有在这种倾听之中才能“去生活”。我们不能设想他没有这么一种领悟,否则他根本就造不出这些观念来,就不可能这样来用这些字。特别是“道”这个字,从一开始就有两个意义,一个是道路,一个是言说。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我们会感到很奇怪,没法解释,任何知识都无法告诉我们,训诂学、语言学都不行。我们只能说:它跟知识无关,而是先行于知识的,先行于认知的。这样的“天命”,我称之为“生活领悟”。如果我们一定要说“良知”的话,我更愿意在这样的本源意义上使用“良知”这个词语:“良知”就是生活领悟,就是“听见”了生活情感、尤其是爱的情感的无声的召唤。生活情感的这种无声的召唤,就是“天命”。 (2)耳顺:倾听生活 所以,孔子才说“耳顺”。也正因为如此,我会说,人到了这个自如境界,才算是真正的“圣人”。因为“圣”字从“耳”,就是倾听。“圣”是个形声字嘛,“圣”的繁体字是“聖”,从“耳”,读“呈”。(《说文解字》)因为你能倾听,你才成“圣”。所以,孔子才会特别说到“耳顺”。孔子特意地说到“耳”,圣人之“耳”用来做什么?倾听。倾听什么?倾听天命,而不是听上帝发号施令。这里没有上帝,也没有任何存在者。我说过了,这里的“天”不是实体,也不发号施令;但我们似乎确实倾听到了,所以,我们把这件事领悟为“命”---- 口令。“天”既然不是存在者,不是物,那就是存在本身,就是生活本身;“命”也就是生活本身的情感流行的某种“趋向”、“趋势”、“势头”、“动向”。所以,倾听什么?就是倾听生活本身,倾听生活情感。这样,你就成圣了。 我刚才谈到过,“圣”就是“仁且知”(《孟子·公孙丑上》)。什么叫“仁且知”呢?这跟“圣”之“耳”的“倾听”有什么关联呢?“仁”就是“天命”,就是存在本身的无声的言说,也就是生活情感本身的流动;而“知”,就是“知天命”,就是“知道”了、倾听到了这样的“天命”。此时,不仅生活情感涌流着,而且我们倾听到了、“知道”了这种涌流,这就不再仅仅是自发境界、自然境界了,而有了“觉解”。这就叫“仁且知”,也就是我所说的“生活领悟”。 我们倾听“天命”,就是听到了生活本身的流水之声。生活之“活”,原来就是流水之声:“活,水流声。”(《说文解字》)生活犹如《诗》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卫风·硕人》)所以,生活犹如孟子所说:“源泉混混,不舍昼夜。”(《孟子·离娄下》)犹如孔子所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所以,我经常说:生活如水,情感如流。这就是“智者乐水”、“智者动”;然而生活本身,其实无所谓动不动,这就是“仁者乐山”、“仁者静”。(《论语·雍也》) 这个时候,就叫“耳顺”。“耳”是倾听,“顺”是听见了。许慎解释“圣”字:“通也。”(《说文解字》)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叫做“通顺”。圣人“耳顺”,所以能“通”,就是“通顺”。通往哪里呢?通往生活本身、存在本身。这就是我所说的:通达本源。 大家都能注意到,汉语观念中有一系列的关键性的词语,在儒家、道家都非常核心的词语,都和我们的口、耳有关。诸如“命”、“名”、“哲”、“和”、“吉”、“君”;还有“诚”、“信”、“谊”;还有“圣”字(繁体从“耳”),等等。据说老子这个圣人,名“耳”,字“聃”,也跟耳朵有关。很有意思!这一切绝不是偶然的。从“口”或“言”,就是说话;从“耳”,就是倾听。可是“天”不说话,你听什么?但是天又能“命”,你确实是能够听见的。你回到本源上,谁告诉你什么?没有谁告诉你什么。但是唯其如此,你才“耳顺”,才能“通顺”,才能通达本源。否则,孔子突然说了一句“耳顺”,你会感到突兀,不明所以。他听什么呢?实际上,他是在听“无”。 还有一点,我要分辨一下:事实上,在第一个境界之中,在自发的境界之中,我们就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耳顺”了。我们一向就在倾听生活,一向就在倾听情感。我们向来就“在生活”,所以我们向来就在感悟生活、倾听生活。假如你听不见“活”---- 水声,你就没法“活”---- 没法生活。但是,这里缺少一点----我刚才讲了,我愿意理解为----真正本源意义上的“良知”。这样的良知,从知识论的角度看,是“无知”的。在认识论、知识论的意义上,良知无知。良知无知,因为其无“所知”。但良知又确实是一种“知”,所以才叫做“良知”,才有个“知”,那是“无所知之知”。“圣”之为“仁且知”之“知”,就是这样的良知。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为生活领悟的“良知”。这跟传统形而上学所理解的“仁且智”的智是不同的。人们通常这样理解“仁且智”,就是:仁者爱人,有爱心,或者说遵守儒家的道德原则;然后他还很有智慧:于是就成了圣人了。更有甚者,把“良知”把握为什么“本体”。不是这样的,不能这么理解。“仁且知”固然是达到圣人的境界,但是圣人的境界就是倾听。倾听什么?听无。什么都不要听,不听知识,不听道德,不听上帝;只听“天命”,只听生活本身,只听生活情感。这才是“圣”,这才能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那么一种“自由自在”。圣,就是知道倾听爱的呼唤。 (3)从心所欲:生活 孔子说他自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对于这个表达,人们有很多的误解:又是“心”、又是“欲”、又是“矩”。太主体性了!所以,我想通过对这几个观念的解释,来说明孔子这种最高境界的本源性意义。 第一点,关于“心”。 从字面上看来,“从心所欲”的前提是“心”,于是,人们马上就想到形而上学的“心性论”,说:这个是良心,本心,本体。其实,这个“心”也就是“无心”。汉语的“心”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用法的。所谓不同,是观念层级上的不同:有时是说的形而下的心,比如说,牟宗三所说的什么“道德心”、“知识心”[7];有时是说的形而上的心,就是孟子所说的“本心”、“良心”,也就是绝对主体性;有时侯却恰恰是说的无心,是说的本源之心:无心之心。此心即无。《增广贤文》上说:“流水下滩非有意,白云出岫本无心。”生活情感的显现、本源性的爱的显现,就是“非有意”、“本无心”的事情,就是“自然”----“自然而然”---- 的事情。所谓“从心”,就是随顺这样的自然。孔子之所以能这样随顺自然,是因为他已经“知天命”而“耳顺”,已经领悟了生活本身、倾听了生活情感。所以,对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我们千万不能理解为心性论的那个“心”。 第二点,关于“欲”。 我在谈“七情”的时候就谈到过,“欲”一般来说是一个主体性范畴。我说过,“欲”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意向性”(intention)。[8] 甚至有时在谈到“仁”的时候,“欲”也是主体性、意向性的事情。比如,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显然,这里的“仁”是“欲”的对象,是一种道德情感方面的意愿,当然就是形而下存在者的一种主体性意向性了。但是,显而易见,孔子这里所谈的“从心所欲”,却是自如境界的事情,那就绝不会是主体性意向性的事情了。这个问题,同样涉及我经常讲的一个话题,就是:孔子那里的词语往往是多层级的用法。“欲”也是这样的,在谈到自如境界的时候,孔子所说的“欲”,一定不是说的主体性的意向性。这里的“欲”,一定是回归了本源层级的事情。 这就使我想到关于“欲”的这样两种说法:“性之欲”和“情之欲”。首先需要指出:这不是现代汉语里所说的“性欲”、“情欲”。“性之欲”这个说法,例如朱子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诗集传·序》)我讲过,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形而上学的“性-情”观念架构。[9] 而“情之欲”,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里没有“性”---- 主体性的预设,而是从“情”---- 生活情感出发的。有情,就会有欲。当然,欲不是情;欲是从情感向意欲的观念递转,正是在这种递转中,主体性才得以生成。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接近于本源性的“欲”毕竟还不是主体性。 我理解,孔子这里所说的“从心所欲”之“欲”,既然实质上是“无心”的,那么就是“无心之欲”,就是那种直接发源于生活情感的“欲”。这非常接近于我刚才谈“天命”的时候说到的:生活本身的情感流行的某种“趋向”、“趋势”、“势头”、“动向”。这种“欲”,恰恰是“无欲”。比如,孔子在领悟天命的时候,说:“予欲无言。”(《论语·阳货》)这样的“欲”,恰恰是“无欲”。所以,“从心所欲”恰恰是说的无心、无欲。 第三点,关于“矩”。 所谓“不逾矩”,从字面上看,是说的不会逾越规矩,诸如不会犯法、不会违纪之类。那就是说,怎么做都不会“犯事”。但是,这样的理解是很不好的,是很形而下学的理解,而不再是超越了形而下学、形而上学的自如境界的事情了。我们知道,“矩”是说的“礼”,就是我谈到过的各种各样的规范。这样的规范的存在,那是形而下存在者的事情;可是,在这种自如境界上,我们不仅超越了形下之物,而且超越了形上之物。这里“无物”,也就无“矩”、无“礼”可言。孔子之所以能“不逾矩”,是因为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根本就没有什么“矩”:不仅超越了形而下的东西,而且超越了形而上的东西,真正回到了生活本身、情感本身。 所以,我的理解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说的生活而已。不过,需要注意:这里的“生活”是个动词,就是“生活着”,就是本源地“在生活并且去生活”着。所谓的“达到最高境界”,其实就是生活着----纯真地、质朴地生活着。 如此说来,这不是又回到了那个最低的境界去了吗?不是又回到了自发境界、或者“自然境界”了吗?当然可以这么说。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复归于无物”(《老子》第14章)。所以我常说:最高的境界,就是回到最低的境界。但是,这里还是有个区分:这个最高的境界却又跟那个最低的境界有本质的不同,这个不同就是有无“觉解”,或者我刚才说的,有无“良知”。最低的自发境界是无觉解的,而最高的自如境界却是有觉解的。所以,更确切地说:最高的境界,就是自觉地回到最低的境界。具体说来,最高的境界就是:自觉地回归生活本身,自觉地回归生活情感、尤其是爱的情感,自觉地在生活并且去生活。 好了,我们的讲座就到此结束吧。 注释: [1] 冯友兰:《新原人·境界》,商务印书馆(上海)1946年版。下文同此,不再注明。 [2] 牟宗三 徐复观 张君劢 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原文:“儒家亦素有形上之道见于形下之器的思想,而重‘正德’‘利用’‘厚生’。” [3] 黄玉顺:《绝地天通:从生活感悟到形上建构》,载《哲学动态》2005年第5期。 [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35页,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 [5] 原文:“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6] 黄玉顺:《中西自然价值观差异之我见》,载《理论学刊》2004年第3期。 [7] 牟宗三把“知识心”、“知识主体”看做形而下的,而把“道德心”、“道德主体”看做形而上的,这才有他的所谓“良知坎陷”的设计,由绝对的道德主体性来开出相对的知识主体性。但我认为,这是站不住的。参见拙文:《“伦理学的本体论”如何可能?——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批判》,载《西南民院学报》2003年第7期。 [8] 参见第二讲第三节“1、本源之爱”。 [9] 参见第二讲第一节“1、性与情:儒家的形而上学架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