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9)
http://www.newdu.com 2024/09/20 04:09:39 中国儒学网 黄玉顺 参加讨论
二、中国思想的“思”:爱与思 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正面来谈“思”的问题。 如果说,我们要在一种“思”当中,给出存在者,那么,这样的“思”本身,当然就不是任何存在者的事情了。因此,我们现在就会想:假如真有这么一种“思”,那不是存在者的事情,那么,那也就一定不是笛卡儿意义上的“思”。因为我们知道,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就是从笛卡儿的“思”开始的,但正是在这种“思”中,他第一次高高挺立起了认知主体性,也就是说,他那个“思”----“我思”是主体性的“思”。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所要讲的“思”是先行于主体性的事情,那就一定是更先行于笛卡儿那样的“思”的事情了,而一定不会是笛卡儿意义上的“思”了。 那么,还可能有怎么样的“思”呢? 我们今天能够想到的、跟存在者没有关系的“思”,或者说先行于存在者的“思”,放眼当今世界,似乎只有海德格尔在讲这个问题,那就是他后期的“思”:Denken。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天翻译海德格尔的“思”的时候,有两种译法:在英文里面,就是think、thinking或者thoughts,其实就是“思想”;而国内在翻译的时候,有些译者为了把他的“思”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思考”之类的作出区分,就译为“思”,而不译为“思想”。其实,在西语里面,它们仍然是一个词。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译本还是把海德格尔的“Denken”译为“思想”。 这就是说,在西方的语境当中,不管是笛卡儿那样的“思”,还是海德格尔那样的“思”,其实仍然还是某种方式的“思维”、“思考”,仍然还是在西方背景下的、知识论进路上的那么一种“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样的“思”跟情感无关,跟儒家所说的爱无关。甚至,在海德格尔后期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1],所谓“诗与思”,你虽然可能认为他是在谈真正的诗歌当中的那么一种“思”,但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在他那里,诗人----比如荷尔德林----完全被解释成了一个思想家。这跟我们中国人理解的完全不同:在中国的观念中,诗人并不是什么思想家;诗是情感的言说,不是什么“思想”。譬如老子就是一个思想家,没有人会说他是诗人;尽管《老子》是押韵的,我们仍然至多只说那是“韵文”,绝不是诗。 当然,在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中----在我第一次提到的“虚位”的意义上,他讲的那个“思”,和儒家所讲的在本源意义上的“思”,还是有着对应性的。是怎么对应的呢?那就是:在观念的层级上,儒家的本源性的“思”和海德格尔的“思”都是先行于存在者的。但是,在“定名”的意义上,两者则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不难发现,海德格尔的“思”,不论是前期、还是后期,整个地不可能摆脱西方的那么一种背景:那是认知性的、而不是情感性的“思”。 1.汉语“思”或“思想”的本源性意 下面我就来讲一讲中国人所说的“思”以及“思想”。 我们平时老是说“思想”,那么,“思想”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查了一下《红楼梦》。《红楼梦》前八十回,曹雪芹亲自写的,出现了三次“思想”这个词语。我们就从这里切入,来看看中国人所说的“思想”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例子,是说甄士隐丢失了女儿,他们夫妇怎么“思想”她。原文是这样的: 那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便知有些不妥,再使几人去寻找,回来皆云连音响皆无。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岂不思想?因此昼夜啼哭,几乎不曾寻死。(《红楼梦》第一回) 这是《红楼梦》中“思想”的第一个例子。显而易见,用现代汉语的话语来说,那是“思念”的意思。 第二个例子,是贾琏说的一段话。贾琏这个人,当然是很讨厌的,不过,他说的这番话还是很中肯的。我们知道,贾府的元春选进宫了。贾琏由此联想到了一种情境。什么情境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情境。(元稹《行宫》)这些宫女选进宫里,有的甚至终生连皇上的面都没有见着;另一方面,千山万水,远离父母兄弟,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们怎么能不“思想”呢?贾琏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宫里嫔妃才人等皆是入宫多年,抛离父母音容,岂有不思想之理?在儿女思想父母,是分所应当。想父母在家,若只管思念女儿,竟不能见,倘因此成疾致病,甚至死亡,……(《红楼梦》第十六回) 这里仍然跟上一个例子一样,是指“思念”。而且,这里明确地出现了“思念”这个词语:女儿“思想”父母,父母“思念”女儿。作者同时使用了这两个词语,都是说的思念。 这就表明:原来中国人说“思想”的时候,那首先是情感的事情。当然,《红楼梦》里面的“思想”的第三个例子是跟认知有关的,[2] 这就不说了,因为那是后起的用法。我们现代汉语当中说到“思想”的时候,就总是跟认知有关,而且不是所谓“感性认识”,而是所谓“理性认识”。那就更是“西学东渐”以后的事情了。传统的“思”或者“想”固然是有这样的认知意义的,但更多的是本源的意义:“思想”意味着情感之思。 我以前写过一首歌,《就这样吧》,其中的“思想”也是这种用法,是指的情感之思: 就这样告别吧,不用忧伤, 从今后再不要苦苦思想; 就这样分手吧,天各一方, 从今后再不要回头张望。 我刚才引用的《红楼梦》,是比较晚近的文本;其实,更早的文本也是这样的用法。同时,早在中古以来,在宋词、元曲里面,例如《西厢记》里面,还大量地使用另外一个词:“思量”。但是,它的意思还是相当于“思念”这么一种情感之思。“思量”这个词,大家是比较熟悉的。比如,“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苏轼《江城子》)这个词在汉语中是原来跟“思想”一致对应的,甚至可以说是等同的。在本源意义上,“思想”、“思念”、“思量”都是一个意思。不过,它们后来逐渐地由情感之思转向了认知之思。这种词语用法的转变,实质上是观念的转变----观念层级的递转。在“思”这个话题里,我们要说明的是:观念层级的这么一种递转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这种在情感意义上的“思想”、“思念”、“思量”,在上古时代往往只说一个字:“思”。比如说,你去翻一下《诗经》,那时候一般不用双音节词,就一个字:“思”。《诗经》里“思”的用法一共有三种,但首先是情感之思。在《诗经》这么一个比儒学的成立还要早的文本当中,“思”表达情感,这种用法是最多的,非常之多,尤其是在《国风》当中。我们知道,《国风》主要言说的是情感的事情,它和《商颂》、《周颂》、《鲁颂》是不同的。当然,这些“颂诗”,你可以说表达了另外一种情感。但不是那么本源性的生活情感。比如说,在追溯自己祖先的丰功伟绩的时候,人们会表达一种崇敬的情感。但是,《诗经》里面的“颂诗”,在今天严格地看起来,其实不能算是诗。因为,这种“颂诗”跟另一种体裁完全是一回事,比如说,后来我们发现的钟鼎文上面的铭文,也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3] 的,跟“颂诗”一样。你可以拿来对照,它跟《诗经》里面的“颂诗”相比,从内容到体裁,几乎完全一样:在体裁上,都是以四字句为主、押韵;内容方面,就是毛亨在《诗序》里给出的那个界定 ----“美盛德之形容”,----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歌功颂德”。但是,这些钟鼎铭文,没人说它是诗。真正的诗,在《国风》以及《小雅》当中。在这些作品中,情感之思表达为“思”。 不仅如此,进一步说,这样的“思想”、“思念”、“思量”之“思”,作为情感之思,是跟“爱”有密切关系的。思念女儿,是因为爱女儿;思念父母,是因为爱父母。相思,是因为爱某人,如《红豆》诗所说的:“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思乡,是因为爱家乡,如李白《静夜思》:“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总之就是:爱,所以思。 那么,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讲座的题目:“爱与思”。在中国人这里,思首先是情感之思,是爱之思。所谓“爱之深,思之切”。我上一次讲“爱”的时候讲过:爱,或者“仁”,原来是先行于任何存在者的一种生活情感,是一种“本源之爱”;而当我们对这种爱进行一种存在者化的打量的时候,它就成为了一种道德情感、道德原则、道德要求,成为一种“形下之爱”;然后我们再追问它的终极根据,就会将爱把握为“性”,就会把“性”作为绝对主体性而确立起来,作为本体来把握,这就是“形上之爱”。这时候,我们要问的是: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那就是“思”。思首先是情感之思、本源之思,这是应合着本源之仁的;然后转为形下之思,这是应合着形下之仁的;最后转为一种形上之思,这是应合着形上之仁的。 再回到“思想”这个词语上来。这在汉语里面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可以来看许慎的解释。我们知道,许慎的很多解释都是很不到位的。现在分析一下他对“思”、“想”这两个字的解释。 许慎对“思”的解释是特别有意思的:“思,容也。从心,囟声。”(《说文解字》) 把“思”解释为“容”,这看起来很怪,其实很有意思,让我想起了“容貌”、“形容”、“形象”等等。比如说,你在“思”你的女朋友的时候,就会想到你女朋友的“花容月貌”那样的“容”,那样的形象。思与形象的关系,这是我后面还要重点讲的话题。 再说“从心,囟声”。说到“囟声”,我第一次讲座上讲过,汉字有个特点,就是这个所谓的“声”其实往往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思”字里的“囟”可能也是有意义的。这是个词源学的问题。我们看这个“囟”,就是脑袋顶上的囟门,一般的理解,它是不管情感、只管认识的。而“心”不同。在中国人的理解当中,心和囟是有区别的。“心”的用法很多,有更大的包容性,其中包括关乎情感的事情。而惟有关乎脑的事情,诸如认识、思维的事情,这才是关乎“囟”的事情。其实,西方人也是一样的,他们说到情感的事情的时候,不会说大脑brain,而会说heart。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思”字怎么是“囟声”呢?读起来不对呀?其实,古代“囟”字的反切是“息进切”,“思”字的反切是“息兹切”,两个的声母完全一样,也就是“息”的声母。这个声母----用汉语拼音来注音----今天读“x”,古代本来读“s”,就是今天“思”字声母的读法。“思”和“囟”,涉及到音韵学上的“音转”问题,就是说,两个字的声母是一样的,但是韵母改变了,这是古人所说的“一声之转”当中的“对转”。这就是说,“囟”和“思”应该是同源词,含义是相关的。否则,我们无法理解:这个许慎是怎么搞的,“思”怎么会读“囟”呢?其实,“囟”跟“思”同源,而且在“思”字里是有意义的,那就是说,“思”跟认识、思维有关。但是,“思”字首先“从心”,而这样一颗“心”,在儒家的思想当中,包容性是很大的,既管认知,也管情感,还管意志。 这是“思”的问题。我们再来看“想”。许慎解释:“想,冀思也。从心,相声。”(《说文解字》)这就是说,“想”首先是一种“思”。一种怎样的“思”呢?“冀思”。这个“冀”就是我们现代汉语所说的“希望”,怀着某种“向往”。许慎这个解释是说:“想”之为“冀”,是一种希望、向往,一种意愿、意欲。比如,你“想”母亲了,你在“想”的时候,就会产生某种“冀”,会有某种希望、向往、意愿、意欲。当你想一个女孩子的时候,情形也是一样的。因此,这是一个重要的枢纽,就是从情感之思向意欲之思转变的枢纽:思→想。 “思→想”而有意欲,从《诗经》开始,“思”字就有这样的用法:情感之思而转为一种意欲之思。正是在这种意欲之思当中,主体性被给出来了;然后,我们才可能有认知方面的事情。我在谈到“七情”的时候就说过,“喜、怒、哀、惧、爱、恶、欲”当中,这个“欲”是主体性的事情,我不会把它看作一种本源情感。[4] 为什么呢?一般来讲,我们讲到希望、欲望的时候,总是一种主体性的事情,其前提是“有分别相”:主体和客体的分别,主体和主体的分别。而“冀”字上部的“北”,就是分别相。所以,“北”和“别”也是同源词,一声之转。那么,“北”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所说的“东西南北”,是假借字;“北”字的本义,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背”---- 两者相背。“北”是一个象形字,所画的是“二人相背”(《说文解字》),也就是不见面的意思。相背而不见面,你才会“想”---- 想念、思念。这就是我在前面说过的:“思”不是当下的,其所思者不在面前。要不,你怎么会思他想他? 在“思→想”中,会出现所思者的形象,这就是“想”字里的那个“相”字。我刚才又讲过了,这个“相”不仅仅是读音,其实它是有意义的。“想”中有“相”,就是“思”中有“象”。这是很有意思的。主体性的行为总是对象性的,那么,这个对象、客体,最初源于何处?就在“想”之“相”中。许慎解释这个“相”字说:“相,省视也。从目、从木。《易》曰:‘地可观者,莫可观于木。’”(《说文解字》)我们看今天流传下来的《周易》,并没有这句话。但这无关紧要,关键就在于“观”。假如没有“相”或者“象”,你怎么“观”?所以,“相”字从“目”,就是“观相”,《周易》叫做“观象”。这就是说,我们在“思→想”中“观象”,就是观所思者的形象。这个“象”或“相”的问题,我会在后面进行比较详尽的讨论,这里我简单说一下:“象”在观念的层级中有这样一种递转,是跟“思”或“思想”的层级递转一致的: 本源之思 → 意欲之思 → 认知之思 想象 ----→ 形象 ----→ 表象 这个递转系列,正是由“存在”给出“存在者”的观念生成序列。至于“想象→形象→表象”的具体情形,下面再谈。我这里只是说:一切都渊源于本源之思----首先是情感之思,然后是领悟之思。 2.思与爱:情感之思 儒家所讲的“思”、或者中国人所讲的“思”,首先是生活情感的事情,是爱之思。在这个层级上,我们可以用这么三句话来说:思源于爱;思不是爱;思确证爱。 第一句是:思源于爱。 我刚才就说过了:爱,所以思。意思是说:情感之思是源于爱的情感的。我们思一个人、想一个人,那是因为我们爱这个人。比如孩子给母亲打电话:“妈,我想你了!”你为什么想她呢?因为爱她嘛。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不用多说。 第二句是:思不是爱。 情感之思虽然源出于爱,但不是爱本身。思和爱是有区别的。区别就在于:爱是当下的,而思不是当下的。比如说,你现在面对着所爱的人,你是不会思他、想他的。他就在你面前,就在当下,还有什么好“思”好“想”的?你爱他,但此时此刻不会想他。你至多只会说:“我想你来着。”但这个“来着”正表明:那是过去的事情,不是当下的。假如你面对着女朋友,却在那里“思”,她可不高兴了,以为你在想谁呢。 这就表明:思总是意味着一种时空上的距离。有一句很著名的汉乐府诗:“有所思,乃在大海南!”(《有所思》)所思者在天涯海角,这就是空间上的距离。我刚才举了苏东坡的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这就是时间上的距离。而且严格说来,我刚才所说的“意味着时空距离”也是不确切的表达;恰恰相反,“时空”的观念正源于这样的思。正是思,才给出了时空:在这种情感之思当中,我们才领悟到时空。 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我们精神生活的很多秘密、甚至全部的秘密,都蕴藏在这里。那么,这里面有什么秘密呢?那就是说:当我们谈儒学的重建、形而上学的重建等等问题的时候,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在“思”当中给出存在者。存在者是怎么可能的?物是怎么可能的?这仍然还是“思”的事情。不过,这个问题所涉及到的乃是我想谈的另外一种“思”:领悟之思。然而,我们现在所谈的却是情感之思。情感之思和领悟之思都是先行于存在者的思,都是本源性的思,但是,这两种思还是不同的:思首先是情感之思,然后才是领悟之思。而这两种思、或者说两个层级的思之间的转枢,就是我现在所讲的“思不是爱”这个问题。 领悟之思是我下面要专门讲的一个话题,这里先简要地谈一谈: 刚才提到了“时空”的问题。当我们谈到“存在者”的时候,一定涉及“时空”范畴。时间和空间都是关乎存在者的事情:我们要刻画一个存在者,一定要涉及时空,因为时间和空间是存在者之存在的条件。但是,在存在本身的层级上,并无所谓“时空”。“时间”、“空间”的观念、概念,同样是由存在本身给出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在西方的传统当中,当涉及到“时空”的时候,他们总是说,时间先行于空间。几乎所有的西方哲学家都是这么看的,所以,他们特别重视时间问题。但是在我看来,按我对中国思想的理解和领会,我会说,就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来讲,中国人的看法跟西方人的恰好相反:空间是先行于时间的,时间是被空间给出的。 首先,在儒家的观念当中,关于存在者的“时空”观念,仍然是被本源性的情感所给出的,具体来说,是在情感之思、领悟之思当中给出的。正是在这样的领悟之思当中,我们才领悟到空间和时间。这是因为,情感之思总是想象-形象的(关于“形象”问题是我下面在“领悟之思”中要谈的一个重要话题),而空间和时间就在这里面显现出来了。有一首很著名的诗,阿波里奈尔的《密腊波桥》,是说:在当下的爱当中,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那首诗里是这么说的:“时光消逝了,我没有移动。”[5]“时光消逝了”,没有时间;“我没有移动”,也没有空间。在当下的爱当中,时空根本不可能显现出来。惟有在“思”当中,时空显现出来了。我刚才说到的东坡那首《江城子》,就是在讲时空的显现:“十年生死两茫茫”;“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这是对时空的一种更本源的领会。所以,“时空”这样一种关于存在者的范畴,在儒家的观念当中,是在情感之思、领悟之思----本源之思当中被给出来的。 另外一点是:在“时-空”呈现的序列当中,是先有空间观念,后有时间观念。中国人理解这个“时”,很有意思。什么叫“时”啊?就是太阳的运行,太阳空间位置的变化。现在什么时候了?看太阳的空间位置嘛。要不,怎么能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呢?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生活领悟。今天的人也说:“看看表吧。”看表,其实你不是看的时间,而是在看空间:这个指针现在指到哪儿了,短针指到哪儿了,长针又指到哪儿了。就是指针的空间位置。正是这种空间位置的观念,规定了时间的观念。所以,中国人对时间的把握,一开始就是从空间切入的。这跟西方的一般理解完全相反。我们后来的范畴的构造,比如在《尚书·洪范篇》里面的“五行”范畴的构造,也是一种“时-空”的连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空-时”连续。“五行”的观念,我把它叫做中国式的“空时连续统”,它规定了空间、时间的观念。这个“时”的原始含义是“四时”,就是春夏秋冬四季,那么,这种时间观念是怎么确立起来的呢?是“五行”的格局,东、南、西、北的空间方位。“四时”的时间观念就是这么被“四方”的空间方位所给出来的。这里,“土”是居中的。“土居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庄子所讲的“中央之帝曰‘混沌’”(《庄子·应帝王》),就是“无分别”,没有空间的分别、时间的分别。然后才是东、西、南、北的“分别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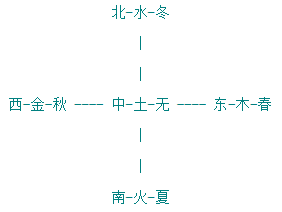 东、西、南、北“四方”的空间分别,规定了春、夏、秋、冬“四时”的时间分别。 不仅如此,我经常谈到的“科学的三大预设”那些观念,也都是在这样的情感之思、领悟之思当中被给出来的。其实,不仅科学,哲学也是这样的。第一,我们首先领悟到的是存在本身,这是科学关于“客观实在”的预设观念得以可能的本源所在。这就是我所说的“存在领悟”:爱,所以在。这是我上一次讲汉语的“存”“在”的时候所谈到的中国人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第二,我们不仅领悟着存在,而且同时领悟着一种“流行”,一种纯粹的“流行”、存在本身的“流行”。生活如水,情感如流。科学的那种预设信念,“运动”的观念,就是被这样的“流行领悟”给出来的。第三,在这种流行领悟中,我们倾听着生活本身,然后才领悟到“天命”。“天命”不是什么东西,不是后来很形而上学化地把握的那个“天命”,诸如“命中注定”啊、上帝意志啊、客观规律啊什么的。“天命”实质上就是对生活本身的一种倾听,是对情感本身的一种倾听。[6] 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源出于领悟之思;而领悟之思,源出于情感之思。 现在说了两句话:“思源于爱”、“思不是爱”。 还有一句:思确证爱。 思虽然不是爱,但思是爱的见证。当然,这里所说的还是情感之思。在情感之思的意义上,我说:如果说,不爱则不思,那么,思着表明了爱着。其实,“思确证爱”这句话的意思是“思源于爱”那句话里早已蕴涵了的。所以,当孟子说“弗思耳矣!”“弗思甚也!”(《孟子·告子上》)的时候,那就意味着:“弗爱耳矣!”“弗爱甚也!”这也是很明显的,不用多说了。 3.思与诗的本源性言说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我经常举诗歌的例子。诗歌这样的言说方式,是情感性的言说方式,实际上所表现的就是情感之思。情感之思一定是想象-形象的,这才有领悟之思的可能,才有领悟空间、时间的可能。 不过,当你读诗的时候,你去品味,就能发现:诗诚然是想象-形象的,但是,诗却又是“言之无物”的。这里所谓“言之无物”是说:这里没有物,没有存在者。诗中显现的想象的形象,不是存在者,不是物,不是我们的认识对象。本源性的言说是“言之无物”的,意思是说,在本源性的言说当中,在一首好诗的言说当中,诚然出现了很多想象的形象,但这不是你所“看到”的形象。你所看到的,只是情感本身的流淌,情感本身的显现。假如你“看到”了这些形象,那就是把它们作为一种对象来打量,那就完了!比如说,我们读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时候,假如我们对象化地想:“哦,有一张床。这是一张什么床呢?是钢丝床、还是席梦思啊?”然后就去考究一番。这样一来,这首诗就全完了!可是,现在很多研究《红楼梦》的人就是这样搞的,比如,他们在研究大观园宴会的时候,老太太坐什么位置啊,宝玉坐什么位置啊,去作详尽的考证。但是,考证清楚了又怎么样?你就读懂了《红楼梦》啦?还是完全没有懂!我经常说,《红楼梦》究竟是表现什么、反映什么的?什么也不反映,就是曹雪芹那首诗所说的,作者一开篇就告诉我们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就是情感而已。可是,人们偏要把它当做历史、当做论文来读,完全不明白那只是“假语村言”而已,这可正应了作者所说的:“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我忽然想起,苏东坡有一首词《水龙吟》: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来看,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这首词是写杨花的,说:春天来了,杨花到处飘着,惹人伤感。这里当然有形象了:有杨花、有尘土、还有流水。一般欣赏诗词的人,对这几句是赞不绝口的:“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确实很美!但我也见过有学者这样注释:“杨花的三分之二飘到了地面上,三分之一飘到了水面上。”诸如此类的吧。我的天!多么精确的计算!“三分之二”,“三分之一”!你把杨花飘落的比例搞得这么清楚,就理解了苏东坡啦?苏东坡根本不是写杨花,这里根本没有杨花,“无物”。所以,他接着写道:“细来看,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没有杨花!至多是“似花还似非花”。这就叫做“言之无物”。科学、哲学、形而上学都是“言之有物”的,然而,诗歌、艺术、本源性的言说是“言之无物”的。 这涉及到“言说方式”的问题,就是说,形象有两种,有一种形象是表象。表象是对象性的,是关乎存在者的。以表象的方式去把握本源的事情,那就正是老子所讲的:“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1章)这样一种“道”,这样一种言说方式,是通达不了本源之“道”的。因为,本源之道是“无物”,就是“无”。因此,如果说有一种言说方式是可以通达本源之道的,那一定是“言之无物”的。 但是,我们用今天的语言哲学、或者语言科学的观念来看,他们所理解的“语言”观念,就是“道可道,非常道”的。从索绪尔开始,今天的语言科学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架构:语言是一种符号,什么“能指”啊、“所指”啊。“所指”是什么?“所指”就是一个对象,是一个客体。但是,本源性的言说方式恰恰没有这样的“所指”的,是“无所指”的。语言哲学呢?在弗雷格那里,实际上是对“所指”有一个区分:有一个“指称”(reference),还有一个“涵义”(sense)。指称,在弗雷格看来,就是一个客观实在的东西;而涵义,有点类似于概念,它是不是就不是对象性的呢?弗雷格自己有明确的说法:涵义是客观的。这就是说,涵义同样是对象性的,就是一个object。[7] 这是因为:他的分析哲学的根基是经验主义。那么,这样的一种言说方式,这样的一种对语言的理解和把握,正好印证了老子所讲的“道可道,非常道”。这样的一种言说,是“有所指”的。有所指的言说方式,是通达不了本源之道的。 那么,是不是存在着一种无所指的言说方式呢?当然是有的。比如说,我刚才所提到的苏东坡的那首词,那就是无所指的言说方式。再比如我提到过的李白的《静夜思》,这样一种“思”的言说,也是无所指的。“无所指”就是说:这里诚然浮现了很多想象的形象,但这些形象不是物,不是东西,不是存在者,不是对象,不是让你去认识它的。真正的艺术,从来不必承担认识的义务。这是我们首先必须把握的艺术观念。所以,凡是对艺术作品说“反映了”什么什么、“表现了”什么什么、它有什么什么“主题思想”等等,都是屁话。包括小说、电影那样的艺术形式,你老去说它“表现了”什么、“反映了”什么,那就说明你完全没有看懂。艺术的言说方式,诚然是形象的,因为那是情感性的言说;但是,这样的言说是无所指的。比如,你听纯音乐,歌词什么的都没有,但是,此时此刻,你脑中会出现一些形象,这些形象,弗雷格把它归结为最不可靠的东西 ----“意象”(image),但这正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所在。弗雷格认为,那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是不客观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才是最本源的。总之,情感性的言说是想象-形象的,但这样的形象不是对象,不是存在者,不是供你认识的东西。艺术不是别的,是生活情感的----姑且用这个词来说吧 ----“升华”。 当然,这样的言说方式,也不限于艺术、诗歌。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爱涌现的时候,我们会说很多话,但那都是“无意义”、“无所指”。那不过是情感的显现。我常常举的一个例子,一对热恋中的人在一起,不外乎就是两种情境: 一种就是一句话都没有,默默无言,“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或者是相视而笑,傻乎乎的。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因为此时此刻不需要任何一种对象性的言说,任何对象性的言说都会打破这种本源情境。比如说,两个人正在含情脉脉的,你忽然说:“你交作业了没有?”或者:“你的那个股票抛了没有?”或者:“你这条项链多少钱?”诸如此类的,就有点煞风景了,一下子就从本源情境当中被抛出来了,马上就进入了一种对象性的思考。所以,孔子才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兴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不说话,却有“天命”,“命”恰恰是“口令”,[8] 恰恰是在说话。那是无声的言说,本源的言说,其实就是生活本身的显现,情感本身的显现。我刚才说了,这样的“天命”是一种本源性的生活感悟。热恋中人的那种默默无语的情境,正是如此。 另外一种情境:那个男的、或者那个女的,在那儿滔滔不绝,喋喋不休,说了很多话,完了别人就问:“你刚才说什么啊?”回答:“没说什么啊?”是啊,是没说什么啊。因为刚才所说的那些,都是“无意义”的,“无所指”的,“言之无物”的。“言之无物”在这个意义上是说: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情境当中,我并没有给你讲一个对象性的事情,没有讲什么存在者,没有讲什么物,没有叫你去认识、去分析。我此时此刻所说的话,根本就“不成话”---- 那不是语言科学、语言哲学所理解的那么一种“语言”。 这样一种情境,在诗歌当中、艺术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再比如说绘画这么一种艺术样式,也是这么个道理。我小的时候不懂这个道理,看了毕加索的画,就说:“他还没有我画得好!”我是说他话得“不像”。我说他没有我画的好,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绘画就像照相一样,是一种认识,是客观的反映。但绘画并不是反映,不是认识。象我们中国人的画,以前有人讲:“这个画得不对吧?不讲透视,比例也不对呀!画一个人骑马,这个人怎么比马还大啊?”我在上世纪80年代看到一篇评析,很荒谬的,他说:“你看徐悲鸿画的马,完全没有常识!马在狂奔的时候,蹄子不会这样向上翻;否则的话,蹄子会崴断的。我在内蒙放了很长时间的马,马蹄应该是这样向下扣的,这样才有力量。”他预先有了一个错误的观念,跟我小时候的错误观念是一样的。我们在评价艺术作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不是在“反映”什么,不是一种“认识”。 艺术的功能,就是表现情感。所以,王国维评论宋词,说:差一点的境界,是“有我之境”、即“有物之境”,所有客观的物都带上了我的主观色彩;真正好的词,是“无我之境”、即“无物之境”,“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9] 当然,诗词里面是有很多形象的;但是,这些形象不是供你认识的,更不是你想要去认识的。这就是本源之道,就是“复归于无物”,就是“无”。这么一种言说方式,言之无物的、无所指的言说方式,在诗歌当中是比较典型的。 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明白:像诗歌当中的这样的言之无物的、无所指的一种想象-形象,就是本源所在。这就是儒家的本源观念:这就是作为“客观实在”观念的源泉的存在领悟。所以,回到开头的问题:究竟是怎样在“无”的情境当中生成了存在者?究竟怎样“无中生有”?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现在我们的问法是:究竟怎样在本源的情感当中,生成了表象,生成了对象?简单来说,可以这样说:当你把情感之思当中的、或者情感涌流当中的想象-形象,把握为一种存在者,对它进行对象化打量的时候,存在者就诞生了,主体和客体就给出来了,表象就生成了,物就被给出来了。 我举例来讲,咱们中文系的一位老师,他朗读了一首诗,杜甫的《登高》,挺好。然后他开始分析,说其中的那一联,“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这里面有“八悲”。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不过这是很对象化的。他说:离家“万里”,这是一悲;“秋”容易愁,又是一悲;异乡“作客”,这固然是一悲;而且还是“常”作客,这又是一悲;“百年”衰老,这是一悲;而且“多病”,又是一悲;“登台”望远,也容易令人悲;而且是“独”登台,又是一悲。这么一种思路,这样分析下来,是很成问题的:你分析得越清楚,离诗本身就越远。我想,当这个学者在这样看这首诗的时候,跟他第一次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感触的情境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第一次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想到什么“七悲”“八悲”的,只是被打动了而已;现在他去分析它,分析它就把它对象化了,这就进入了一种传统意义上的诠释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主”“客”这么两种存在者同时被给出。 然而,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总是要成为存在者,成为主体,因为我们总是要进行对象化打量,进入“主-客”的观念架构。有一次,我给本科生讲“视而不见”的时候,举过这样的例子:为什么形而上学、形而下学是不可避免的呢?因为本源情境是不可避免地要被打破的。我记得我在一篇文章里面举了房子的例子。[10] 现在我给他们讲:在本源的情境当中,在本源的爱当中,你对你的所爱者,原来是“视而不见”的。她有什么优点、缺点啊,你都“视而不见”。因为:你从来就没有把她作为一个对象去打量。所以,我会说,俗话说的“情人眼里出西施”,那是不对的,因为情人眼里既不出西施、也不出东施,而是无物存在。比如两人谈恋爱,那个男孩子有一天想:“我到底爱她哪里呢?”他马上就从本源性的爱当中跌落出来了。然后他就开始考虑,开始打量。首先从容貌上看:“她这个眼睛,哦,丹凤眼,双眼皮,不错,可惜就是左眼小了一点点,好在还不容易看出来。”然后接着往下看:“这个鼻子差点,人家说鼻子要象一根葱一样,这个差了点。”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进行这样的对象化的打量的时候,我们有一句“名言”:“有比较才有鉴别。”当你这样把你所爱的人,这样打量的时候,一定要有比较。你打量这个鼻子的时候,你马上想到了另外一个女孩子、诸如小张、小王的鼻子长得如何如何的好看。这是非常危险的啊!这就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这就不是“视而不见”了,而是“视而见之”了。这样的一种“视而见之”,就确证了你的不爱。不爱,那么你爱的人就不复存在。但是,形上之思,形下之思,这样一种对象化的打量,却又是必然的。比如,你那个所爱者突然打了一个喷嚏,如果你此时此刻仍然“充耳不闻”,那同样确证了你的爱的不在。如果爱是在的,这个时候,你就会问:“感冒了吗?是不是穿少了?”然后首先看看脸色。这个时候,就再也不能“视而不见”了。你甚至去找出体温计来,对象化地测量她;甚至去看医生,请一个专家来科学地诊断她。但是,这个时候,对象之被给出,同样是在爱当中。正是爱,才给出了这个对象。而当对象被给出的时候,主体同时也就被给出了。在我们的生活中,生活之所以可以不断流动,就是因为本源情境总是不断地被打破,我们总是要成为一个存在者。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总是要“去生活”。这完全是无可避免的事情。 这时候,我们就进入了形下之思、甚至形上之思,而不再是本源之思了。这样的思,是去思存在者,去思对象,是科学和哲学的事情。科学和哲学是没有本源之思的。我们知道,海德格尔有个说法:“科学不思。”我要说的是:这是不够的。在本源之思----情感之思、领悟之思----的意义上,不仅科学不思,哲学同样不思。我经常讲这个话题,就是说:如果说,当我们所说的“思”是关于存在者的事情时,不仅哲学要思,科学同样要思。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哲学所思的是形而上的存在者,哪个唯一绝对的存在者;而科学所思的是形而下的存在者,是众多相对存在者当中的一个领域。但它们确实都在思。其前提是:那是认知之思。但是,如果“思”首先是生活本身的事情,那么我就会说:不仅科学不思,哲学一样地不思。那么,是谁在思?艺术在思,诗歌在思,情感之思自己在思,而不是“人”在思。 正是在这么一种本源之思当中,存在者生成了,“主体-主客”这样的架构给出了,人诞生了。这时候,“人”成为了一种可以规定的东西。人作为一个形而下的相对存在者,是被其它的形而下存在者规定的。我经常讲,马克思对“人的本质”有一个界定,这个界定在哲学的意义上是极其准确的。他说:“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11] 这意味着什么呢?我经常举这个例子,我们不妨作一个实验:你拿出纸和笔来,一句一句地写“我是谁”。你一句一句地、不停地写下去,那么,你会发现:“我”总是“非我”。---- 这些句子的左边的主语都是“我”,而右边的都是“他者”。“我”总是被“他者”规定的。这恰恰就印证了:每一个人,自从有了自我意识,你就作为一个形而下的存在者而被给出了;你作为一个形而下的存在者,不断遭遇到其它的形而下存在者,你被它们所规定。所以,凭马克思这句话,我们就可以断定:这是一个形而上的表达。但是,这也说明了在这个层级上,主体是怎么样被给出的。 不管是对于整个人类来讲,还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来讲,从轴心时期的形而上学建构开始,或者从古希腊哲学的所谓“拯救现象运动”开始,我们就有了一种自觉的自我意识。但是,我们一开始就是被他者规定的。我记得我在关于“他者意识”的那篇文章里面专门分析了汉语的“我”这个字,证明:自我意识的诞生,恰好是由他者规定的。[12] 古汉语的“我”,就是一个人拿着“戈”。拿着这个东西干什么?有两点意思。在中国汉语当中,自我意识的产生,有两层意思:第一,当我们说到“我”的时候,意味着有一个对象,有一个“他者”,一个陌生者,一个危险者,一个敌对者,他在威胁着我。自我意识意味着:在我和他者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这也是“存在者领域”的划界,一种“物界”。而这个他者对于我来说,总是一种威胁。自我意识首先是这么被给出的。第二,“自我”不是个体的事情。“自我”从一开始产生,就是一个族类、族群的事情,就是“我党”“我军”“我国”的事情,而不是我个人的事情。抗日战争开始,“敌强我弱”,所以要“持久战”,这个“我”不是毛泽东个人,不是任何一个个体,而是一个族群----中华民族。汉语的“我”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那是一个部落,是一个族群和另外一个族群的敌对关系。在这么一个关系之中,“我”才被规定了。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使我们可能回到本源上去。我为什么要抗日?因为我爱我这个族群,我爱我这个国家、我这个民族。这是我讲的。舍勒也讲这个问题,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爱的优先性”。我的观念跟舍勒的不同。我理解这个问题是:爱怎样给出了存在者?就是这么回事。在我们族群内部的平平常常的生活当中,在其乐融融当中,我们原来根本没有什么“自我意识”。只有突然有其他族群来侵犯了,这个自我意识一下就出现了,本源情境就被打破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首先成为了这么一个形而下的存在者,然后才会继续追问,不管是个体、还是整个人类都追问:我是从哪里来的?这才有了轴心时期的所谓“理性的觉醒”,这才有了哲学的诞生。 一个个体也是这样。一个小孩,有一天忽然有了自我意识,清楚地意识到自我和他人的区别,然后会追问,去问母亲:“我是从哪里来的?”母亲就说:“你是我生的嘛。”然后小孩又会问:“那你又是从哪里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小孩天生就是一个形而上的存在者。他不断地追问形而上的根据,直到一个地方就打住了,就不能再问了。我们不能问:“上帝耶和华是从哪里来的?”谁知道呢?不知道。那个小孩假如再问,可能就会挨骂。在形而上学的范围内,这个绝对主体是不能问的。也有人说,那只是一个设定,仅仅是设定。比如,康德就说:上帝只是实践理性的一个公设。[13] 但是,我们今天仍然要问。并且,我们还意识到:我们这样的形而下的存在者,以及那个形而上的存在者,那个被设定的存在者,其实都是生活本身给出的,都是本源性的爱给出的。 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兴于诗”(《论语·泰伯》)的意义所在:主体性、对象性、存在者、物,都是被本源之爱所给出的,那么,诗作为一种本源性的言说,正是这样的本源之爱的一种显现样式。 那么,在轴心时期以后的儒家这里,众多相对的存在者、或者“天下万物”是怎样被爱给出的?这样的观念,后来被形而上学化,比如在孟子那里,被表达为:“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这就是说,“天下万物”、即众多相对的存在者,是被一个绝对主体给出的。这个观念的前提就是:已经把那种本源之爱,把握为了一种形而上的存在者----绝对主体。《中庸》里面则是另外一种表达:“不诚无物。”这也完全是一样的形而上学化的表达。“诚”本身是说的一种本源性的言说,是讲的由“言”而“成”。“成己”“成物”,存在者成为存在者,它们是怎么被给出的?由言而成。但是,既然不仅“物”、而且“己”即“人”都是由“言”而成的,那么,这里的“言”显然就不是“人言”,而是先行于“人”的存在的某一种“言”。现在我们知道,只可能这么来理解:这样的“诚”,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那种本源性的言说,就是“天命”那样的无声的言说,就是本源性的爱的显现。但是,在《中庸》这个文本当中,“诚”已经不是这个意思了。它已经是一个本体,或者叫做“中”,或者叫做“性”。这里设定了一个“未发”之“性”,就是把本源之爱把握为了绝对主体性。这已经是存在者的表象----表象式的把握方式。 4.想象·形象·表象:领悟之思 说到“表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对于“生活儒学”的建构来说,甚至是一个关键性的话题。 在西方近代哲学中,“表象”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语。但是,我们去翻一翻哲学辞典,就会发现,所谓“表象”其实是很难被界定清楚的,各家的用法有所不同。但是,尽管如此,我想说的是:“表象”这么一个观念,一方面,跟中国的哲学教科书里面所讲的那种完全和“形象”无关的“抽象”“概念”,是没有关系的;另一方面,我可以这么说,表象是一种“象”。大家可以反省一下、体验一下:在你自己进行所谓“抽象思维”、“逻辑推理”、“理性认识”的时候,那里面究竟有没有“象”?我想,应该是有的。理论的、逻辑的思考,其实一定不是“抽象”的,而是“具象”的,或者叫做“具体”的、“形象”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脑子里面充满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区分之类的观念,我们以为只有感性认识才是形象具体的,理性认识则是抽象的。但我自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我自己的研究、思考当中,当我清理某种“抽象”思路、“理论”架构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出现的,却往往是一些非常“具体”的、“形象”的东西,有时侯简直就小孩子搭积木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在我看来,直白地说,根本就没有所谓“抽象思维”,任何思维都是“具象”的----具体的、形象的。而仅就认知性的具象来看,有两种。有一种是当下性的具象,另有一种是非当下的。当下性的具象,很简单,就是所谓“感知”,经验论意义上的“直观”,是最直接的。比如说,我现在看见你们,如此这般,这就是一种当下性的具象。而那种非当下的具象,就是所谓“表象”。但是,不管感知、还是表象,都是形象的、具象的。所谓“感性认识”,就是直观性的形象;所谓“抽象思维”,其实是一种表象性的形象。 我这个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刚才所表达的观点,其实就是休谟的观点。你去读休谟的《人性论》,他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当然,他没有用这样的概念:“表象”什么的。他是另外一种谈法。他说:我们人的所有的“心灵中的知觉”---- 其实就是我们的全部的观念、整个的精神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的、鲜明的、鲜活的知觉,叫做“印象”(impressions),其实就是我所说的经验直观;另一种就是间接的、比较模糊一些的知觉,叫做“观念”(idea),其实就是我所说的表象。印象和观念的区别,就是“感觉”、“感性认识”和“思维”、“理性认识”的区别,其实就是我所说的当下性的形象和非当下性的形象的区别。[14] 但要注意,休谟所说的这个“观念”跟后来胡塞尔所说的“观念”不是一回事,更不是柏拉图所说的那种“观念”。休谟的“观念”是对应于我们所说的“思维”的;但尤其要注意,在他看来,所谓“思维”,其实也是“知觉”(perceptions)而已。休谟就从这里谈起: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一切都是“知觉”。这就等于是说:一切都是具象的、具体的、形象的。换句话说,在休谟看来,根本就没有什么“抽象思维”。这是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经验主义者,所以,在他的心目中,所谓“抽象思维”不过就是心理联想,而心理联想也就是一些模糊微弱的知觉之间的联结。其实就是表象的联结。就是这么简单。 所谓“抽象的”思维其实就是表象式的把握,这个观点,海德格尔继承了下来:在他看来,形而上学就是以表象的方式去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15] 只不过,他只提到了哲学形而上学,而在我看来,按照休谟的观点,不仅哲学、而且科学的“理性认识”同样是表象式的。 我是非常欣赏这个观点的,虽然我并不是站在经验主义的立场。只不过,我会这样来表达:不管所谓“感性认识”还是所谓“理性认识”,一切都是观念(我自己的用法意义上的“观念”,对应于、但不等同于休谟所说的“知觉”);一切观念都是形象的;但是,所谓“感性认识”是直接的、直观的形象,就是所谓“感知”;而所谓“理性认识”则是间接的、变形的形象,就是所谓“表象”。换句话说,在我看起来,表象也是一种形象。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表象”。总之,表象就是那种非当下性的、间接的形象观念。 这就是说,表象作为一种间接的形象,来自另外一种直接的形象,就是直观的感知。但是问题在于:直观的感知形象是认知性的,是关于存在者的一种认识,那也不是本源的事情,不是存在本身的事情。于是,我们要问:如果说,表象来自直观形象,那么,直观形象又来自何方?这等于是在问:被直观所感知到的那个存在者来自何方?我的回答是:来自想象。表象来自形象,形象来自想象。但是,这不是一般心理学所谓的想象。心理学把想象归之于“认知心理学”范畴,就是把想象归结为一种“认识”,这样一来,那样的想象就不是本源性的想象了。想象之为想象,就是“想-象”,就是“想”中之“象”,就是“想→象”。换句话说,想象源于生活情感性的、本源性的“思→想”。所以,假如我们问:如果说,形象来自想象,那么,想象又来自何方?回答就是:想象源于一种“思”---- 本源性的情感之思。 这种情形,在诗歌里是最典型的。诗,一般来说,就是形象的,但不是表象的;其实不仅不是表象的,而且严格来说,也不能说诗是形象的。诗是想象的,因为诗是情感之思。我刚才举了一些诗歌的例子,并说诗是情感性的言说方式。确实,诗就是情感性的“思→想”。如果说,生活情感作为生活本身的显现,是真正的本源,那么,情感性的言说方式就是本源性的言说方式;而诗,正是这样的一种本源性的言说方式。当然,本源性的言说不仅仅是诗;但是,真正的诗一定是本源性的言说。唯其如此,孔子强调诗,主张“兴于诗”(《论语·泰伯》),意思是说:就“教”而言,主体性的确立,源于诗,也就是说,源于情感性的、本源性的言说。这才是儒家所说的“诗教”的本源性意义所在。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诗首先是情感之思,同时也是领悟之思。当然不仅是诗,日常生活、情感生活也都充盈着情感之思、领悟之思;但诗是最典型的。情感之思乃是“想象”:想→象。这就是说,这样的“思想”之中,“其中有象”。老子这一段话,应该就是在说这样的事情:“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第21章)。首先,“道之为物”,它已经是一个物、一个存在者,就是那个形而上的存在者,我称之为形上之道。[16] 那么,此道来自何方?来自恍惚。此“恍惚”犹如庄子之所谓“浑沌”。此恍惚既然先行于“道之为物”、先行于物,那么,恍惚本身就是无物,也就是无。在这样的无物的恍惚中,首先生成了“象”,最终生成了“物”。这也正是老子的“无中生有”的思想。 这样的无中生有,其实就是:想象→形象→表象。想象生成了形象,于是就有了领悟之思,就有了各种样式的生活领悟。领悟之思乃是“形象”,这种形象在想象中生成。这是显现、显示、呈现的真正意义,是对应于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的事情。这里,情感之思的想象、领悟之思的形象,都属于本源层级上的事情,即是存在本身、生活本身的事情。然后,观念的层级才能转为存在者的表象,转为物的表象。各种各样的存在者,人与物,都发源于想象的形象。所谓存在者、物,并不是所谓“客观实在”的东西,而只是表象:存在者的表象、物的表象。存在者、物的生成,意味着表象的生成;反过来说,也是一样。这是怎样生成的呢?那就是我一再讲的本源情境的打破,想象的形象之被对象化、客观化、存在者化、物化。 于是,我们得到观念层级的这样一个递转序列:想象 → 形象 → 表象 。我们谈“诗与思”,作为一种追溯,其实是把这个序列颠倒过来:表象→形象→想象。这就是说,我们是从“表象”的问题切入这个话题的。 从“表象”来切入这个问题,可以从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规定谈起。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有一个著名的界定: 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着眼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之共属一体,来思考存在者整体----世界、人类和上帝。形而上学以论证性表象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17] 海德格尔在这里对“形而上学”的把握是很准确的。不过,人们通常只注意到这个界定的一个方面:形而上学就是对存在者整体、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思考;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个界定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这种思考是“论证性表象的思维方式”。这里,“表象”是一个关键词。 海德格尔指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乃是表象的方式。这是深刻的;但我要说:海德格尔这个说法仍然是不完整的。其实不光形而上学、哲学是以表象的方式来把握存在者,科学同样如此。可以说,任何一种思维,认知性的思维,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思”,包括神学,统统都是以表象的方式去把握存在者。这是为什么呢?我刚才说过了:存在者、物的观念,只能以表象的样式存在,或者说,它们本质上就是表象。这使我想起叔本华的一句名言:“世界是我的表象。”[18] 这是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全书的第一句话。今天看来,这句话可谓是形而上学观念的一种直率的概括。如果不仅形而上学是思考存在者、而非存在本身的,而且科学也仅仅是思考存在者、而非存在本身的,那么,科学也只能以表象的方式去思考,否则,它就不是科学。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问题的转换,发问方向的转换。我原来提出的问题是:存在者是怎样被给出的?存在者是怎样在“思”中生成的?我们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现在,这个切入点就是:表象。那么,现在问题就可以转换为:“表象怎么可能?”当你在问“存在者怎么可能”、“认识怎么可能”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你在问:“表象怎么可能?”不仅所谓“理性认识”,甚至包括所谓“感性认识”这样的认识,你也可以问:感性的形象是怎么可能的?这样的问法,就引导我们进入了儒家的“思”、中国的“诗与思”。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个表象、或者认知中的“具象”,它总是形象的。但是,却有不同的形象。表象是一种形象,但不是全部的形象。比如,我会说,在情感之思、领悟之思当中,就已经有形象了,但这样的形象并不是表象。而在认知之思当中,也有形象,而且这样的形象就是表象。那么,在本源之思之中的形象,和在认知之思之中的形象,区别在哪里呢?两者之间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本源之思中的形象是怎样转化为认知之思中的表象的?这是问题的关键。 我们知道,情感之思一定是形象的,是想象中的形象。表现情感之思的艺术,也一定是想象-形象的;否则,就不可能表达情感。那么,我在前面说过:中国人所说的“思”,首先是情感之思;而在这种“思念”这样的“思想”当中,出现的就是想象的形象。这种想象的形象,在诗歌、诗词当中是非常典型的。毛泽东以前说:“诗是要讲形象的。”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界就展开了大讨论,叫做什么“形象思维”。说诗歌是“形象思维”,这很荒诞。当然,前面两个字是对的,诗歌一定是“形象”的;但是,诗歌哪有什么“思维”?他们所说的“思维”是一种思考,是理性认识;但是,诗歌不是理性认识,甚至根本不是什么“认识”。我经常强调:艺术无关乎认识、知识;艺术只是情感的事情。诗歌一定是形象的,但诗歌里面的形象绝对不是表象。反过来说,不论是意欲之思,还是认知之思----就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思想”、认知意义上的“思想”---- 当中的形象,都一定是表象。 一个思想者、思考者,包括科学家那样的一种思考者,其思考方式都是表象式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爱因斯坦。我以前把《爱因斯坦文集》找来看,特别是第一卷,那是跟哲学有关的。那本书里面的几个地方,表达过一种很重要的观点,比方说,类似于“理性为自然立法”那样的观点。在他看来,科学相信客观实在,其实只是一种“信念”而已。[19] 据说,他还有这样一种很有意思的“信念”:他自己在构造“狭义相对论”的公式 ----“质能关系式”的时候,是有“科学”以外的一些指标的。比方说,他觉得:我要“发明”的这么一个公式,它必须是均衡的、匀称的。一言以蔽之:它必须是美的。爱因斯坦心里是很明确的:如果搞出来的这个公式不美、不匀称,那我就一定是搞错了。我不知道爱因斯坦的这种信念是从哪里来的,但我是很认同的,因为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形象的把握。他的那种工作方式,所谓“思想实验”之类的,比如著名的“追光实验”和“升降机实验”,那明显地是“具象”的、形象的,其实就是表象的把握方式。我们的很多所谓“抽象思维”,实际上,我想,就象小孩子搭积木一样,有些“具象”的、形象的东西。这些具象的东西不是直观的形象,而是另外一种形象,具体说来,就是表象。 当我们问“表象从哪里来”的时候,我们不难想到:表象作为认知当中的一种形象,一定是对象化的。或者我们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讲:表象是关乎“存在者”的事情。一定如此。科学的表象是关于存在者的一种形象。形而上学、哲学当中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要构造一个什么“天地万物一体”的观念,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天地万物一体”的观念,我们其实是在搭积木:是一种表象的搭建。 下面我就来谈一下这样的“表象的搭建”:思的建构性。 注释: [1]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红楼梦》第六十四回:“自古道‘欲令智昏’,贾琏只顾贪图二姐美色,听了贾蓉一篇话,遂为计出万全,将现今身上有服,并停妻再娶,严父妒妻种种不妥之处,皆置之度外了。却不知贾蓉亦非好意,素日因同他姨娘有情,只因贾珍在内,不能畅意。如今若是贾琏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趁贾琏不在时,好去鬼混之意。 贾琏那里思想及此,遂向贾蓉致谢。” [3] 朱熹《诗集传·颂四》:“颂者,宗庙之乐歌,《大序》所谓‘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4] 参见第二讲第三节“1、本源之爱(2)情绪”。 [5] 吉尧姆·阿波里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 1880 - 1918),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二十世纪先锋派的开创者。《密腊波挢》的相关诗句:“…… 让黑夜降临让钟声吟诵 / 时光消逝了我没有移动 / 我们就这样手拉着手脸对着脸 / 在我们胳膊的桥梁 / 底下永恒的视线 / 追随着困倦的波澜 ……”---- 莫渝 译。 [6] 以上参见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 ----“生活儒学”问答》,中国儒学网(www.confuchina.com)。 [7] 弗雷格(Gottlob Frege):《论涵义和指称》(Üeber Sinn und Bedeutung),原载《哲学和哲学评论》,100,1892年。肖阳的汉译文《论涵义和所指》(On Sense and Reference),载于马蒂尼奇(A. P. Martinich)主编《语言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8] 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命”字:“从口、从令。” [9] 王国维:《人间词话》,见《人间词话新注》(修订本),滕咸惠校注,齐鲁书社1986年版。原文:“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10] 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 ----“生活儒学”问答》,中国儒学网(www.confuchina.com)。 [11]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原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12] 黄玉顺:《中国传统的“他者”意识----古代汉语人称代词的分析》,载《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2期。 [13]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第136-143页,商务印书馆1999版。 [14] 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第13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原文:“人类心灵中的一切知觉(perceptions)可以分为显然不同的两种,这两种我将称之为印象和观念。…… 进入心灵时最强最猛的那些知觉,我们可以称之为印象(impressions);在印象这个名词中间,我包括了所有初次出现于灵魂中的我们的一切感觉、情感和情绪。至于观念(idea)这个名词,我用来指我们的感觉、情感和情绪在思维和推理中的微弱的意象。…… 每个人自己都可以立刻察知感觉与思维的差别。” [15] 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见《面向思的事情》,第68页。 [16] 我的看法是:老子那里,“道”有三个观念层级:形下之道、形上之道,本源之道。形上之道就是“道之为物”,是一个“物”;本源之道则是“无物”,也就是“无”。 [17] 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见《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第68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18]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第25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9]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284、292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