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土文献《论语》在古代东亚社会中的传播和接受 作者:金庆浩、戴卫红 来源:《史学集刊》2017年3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二月十三日庚申 耶稣2018年3月2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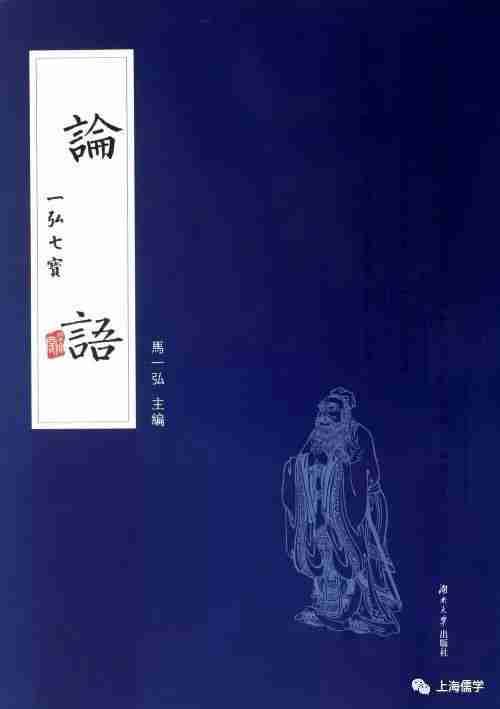 【作者简介】 金庆浩,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秦汉史、简帛学; 戴卫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成员,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简帛学。 【摘要】 《论语》作为儒家学派最为重要的典籍之一,在中国的先秦时期即已成书,至汉武帝独尊儒术时,成为儒学教育的重要教材。其影响不仅在中国,还远及韩、日等东亚国家。20世纪以来,在中、韩、日等国均出土了《论语》简牍。本文以《论语》简牍为中心,考察古代东亚社会儒学普及和汉字的使用。特别是通过对从汉代以后到8世纪前后,中、韩、日东亚三国出土《论语》简牍的比较分析,提供理解东亚世界汉字以及儒教思想传播和接受的新视角。 一、序论 学者们在定义东亚世界或者东亚社会时,一般采用“汉字文化圈”或者“儒教文化圈”这样的概念。这样的解释,缘于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空间概念和此区域内共有的文化性质。空间方面,以中国为首,韩国(韩半岛)、日本、越南同属一个空间位置;而在这个地域内汉字、儒教、作为政治制度的律令和佛教则是共有的普遍概念。可是,若详细地探察这样的东亚社会特定概念,可以发现它并不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地域从一开始就共有,而是从中国兴起而传播到周边国家或民族。特别是汉字,若考虑到中国和周边地区的语言体系不同的话,对周边地区民族而言,将汉字的普及推广理解为单纯的文化推广多少有些牵强。 战国时代有“言语异声,文字异性”的情况,而西汉末,不仅有扬雄提取各地多样的语言编纂成《方言》;而且,从出土简牍中分析边境部署的士兵出生地的结果显示出这样倾向,即同一地域出身地的兵士部署在同一地点。在《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内史杂律”的记事内容中,还有向上级报告时一定要使用文书形式这样的规定,这一规定便是在中国地域内使用口头语言进行沟通也存在障碍的最好例证。并且从秦、汉简牍可以看出,对在边境的官吏们进行识字教育,考课之后得出“史”、“不史”的结论来确定下级官吏的晋升与否,这都与文字的习得有密切的关系。随着帝国范围的扩张,对边境地区进行有效统治的文书行政便成为强化中央集权体制的主要手段。由此可见,为了帝国内的统治能灵活地沟通,使用统一化“文字”,以此代替反映地域差异的“言语”变得尤为重要。 以农耕社会为基础而形成、组建中国郡县体制,从而形成了与游牧社会性质不同的文化圈。随着帝国领域的扩张,以农耕为基础的周边地区作为编入对象,便意味着一旦编入中国秩序便全盘接受中国的文化。然而,事实上中国文化的普及和传播,对周边国家来说意味着在语言体系上强制使用汉字;同时周边国家由于现实实力不能与中国相较量,因此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便形成了。由于这样的原因,历来对古代东亚世界性质进行讨论时,学者们便强调以上所述的以东亚世界四个特征为中心的册封和朝贡秩序体系的形成。如果说在东亚世界里,汉字的普及不是单纯的先进文化的传播,而是和中国的郡县统治体系的编入与否以及古代国家的形成有密切关联的话,汉字必然地以郡县体制及其密切相关的文书简策的形式普及,在东亚各国均有简牍的出土正是论证此观点的实证材料之一。东亚各国出土简牍的形态,可以分为文书类和书籍类这两个大的类别;在时间上,韩国(韩半岛)和日本基本上都以6-8世纪的简牍居多。由于这个时期与东亚各地区古代国家的发展有密切关联,《论语》简牍便成为描绘中韩日三国共有的历史影像的唯一线索。因此,本文以《论语》简牍为中心考察古代东亚社会儒学普及和汉字的使用,特别是2009年公开的平壤出土的《论语》竹简内容,对从汉代至8世纪前后东亚三国出土的《论语》简进行比较分析,由此提供理解东亚世界汉字以及儒教思想接受和传播的新视角。以下便以河北省定州市发现的大约为西汉宣帝时期的《论语》简以及和它时间比较接近的平壤出土《论语》简的格式、记叙内容为中心进行探讨,通过比较韩国和日本出土的木简,从而推究《论语》在东亚社会中普及的实际状况。  二、简册的标准化和《论语》的普及 众所周知,20世纪以前,在出土资料的正式发掘和介绍之前,对简牍的形态和使用的研究,主要依靠传世文献的记载。20世纪以后随着对实物简牍的正规发掘介绍,逐渐将传世文献内容和实物简牍结合。最初的研究是1912年王国维发表的《简牍检署考》,50余年后陈梦家对王国维的学说进行了补充。王国维用“分数和倍数”的概念来说明简册制度,即规定“古策长短皆为二尺四寸之分数。周末以降,经书之策皆用二尺四寸,礼制法令之书亦然。《孝经》策长一尺二寸,汉以后官府册籍、郡国户口黄籍皆一尺二寸。《论语》策长八寸。汉符长六寸。”陈梦家对王国维理论肯定的同时,只是对其进行修改增补而已,对简牍形态的研究并没有太大推进。王国维和陈梦家代表的研究是1970年以前的状况,1970年以后大量的简牍,特别是战国、秦汉简牍的出土、整理,反映出多种多样的简牍形制和叙事内容,而他们的见解已经不能对其进行更清楚的说明了。 随着形态多样的战国秦汉时代的简牍出现,长度与传世文献记载内容不一致的简册也呈现出来。由此,有学者对王国维的见解提出异议,认为简牍的长度、宽度还有厚度等形制不是绝对的,形态也并非固定。但有学者指出西汉后期或者东汉初期,简牍的规格和形态制度化,战国及秦汉简牍可以分为遣策、文书简、书籍简、律令等,考察它们的形态和规格,可以看到秦汉以后无论书籍还是公私文书,最常用的长度是一尺,由此证明一尺是简册和木牍通用的长度。秦代以后的书籍简,比战国时代的减少了18-30厘米,长度没有超过30厘米,这样的趋势持续到西汉前中期。有学者指出,汉成帝时期的尹湾6号汉墓(以下简称尹湾汉墓)内出土的《神乌赋》、《行道吉凶》、《刑德行时》等书籍简的长度仍为一尺,这可以证明简牍同一形制逐渐“标准化”。特别是尹湾汉简24枚木牍中除1枚外,所有木牍的长度几乎全部接近1尺(23cm),而天长汉墓34枚木牍(以下“天长汉简”)的长度大体也是在1尺(22.3-23.2cm)。 汉代边境地区乐浪郡出土的户口簿,更加确认了这一点,即西汉中、后期以后简牍形制成为统一规格的标准化。近年,平壤市贞柏洞364号墓出土的标题为“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多少□□”户口簿的照片得以公布,在这个户口簿中记载了乐浪郡下辖的25个县的户口数。将其与连云港出土的尹湾汉简“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以及安徽天长出土的纪庄汉墓“户口簿”相比,它们不仅在形制规格上一致,而且在记载方式上,也使用了统一的简牍文书样式。有学者指出,到汉武帝时期,书体从篆书字形特征残存较多的古隶体发展为八分体,也有学者认为乐浪郡户口簿书体也是典型的八分体特点,某些字形中依旧使用了带有篆书形态的字形,在乐浪郡也可以看到和内地类似的书体变化的情况。因此,考察简牍的形制、字数、字体等研究结果,可以看到武帝以后文书书写统一原则已经建立,而乐浪地区出土的户口簿是验证这一观点的最好资料。 笔者如此烦琐地叙述乐浪郡户口簿的相关内容,是因为关注在统一原则下进行的文书书写、文书行政和《论语》竹简的关联性。到现在为止,可知的代表性的出土《论语》材料,还有1973年在河北省定州市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的《论语》竹简和以上推断为与乐浪户口簿同一墓贞柏洞364号墓中出土的乐浪《论语》竹简。在定州汉墓620余枚《论语》竹简中,残简占大部分。中山王刘修在西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去世,因此定州汉墓中《论语》的制作年代在五凤三年以前;其形制方面,长度为16.2cm(约7寸),宽0.7cm,每简上的字数约19-21字,简的两端和竹简中间留有编缀的痕迹。尤其是以竹简中部编缀部分为中心,上下均写有10字左右。 关于《论语》的形态,我们可以参考《论衡》中的相关记载: 但[知]周以八寸为尺,不知论语所独一尺之意……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 根据《论衡》的记叙内容,《论语》竹简的长度为8寸(18.4cm),定州竹简除相差1寸外,没有别的差异。 另一方面,2009年12月笔者和李成市、尹龙九一起,对贞柏洞364号墓出土的《论语》竹简已公开的照片进行了释读,其主要内容与柳秉兴先生提到的第11卷《先进》和第12卷《颜渊》的部分内容基本一致。而且在形制上,竹简两端和中间部分残存的编缀痕迹清晰可见,尤其是以中间部分的编缀痕迹为中心上下两部分各均匀地写有10个字,这与上述定州汉墓《论语》竹简形制基本一致。而且在编缀方式上,可以明确看到先编后写的形态。由于这两种竹简具有非常相似的系统性,因此乐浪《论语》竹简极有可能是从汉代内地流入的。同时,平壤贞柏洞出土的乐浪《论语》竹简与清楚标明时间为“初元四年(前45年)”的户口簿一起在同一个坟墓出土,而定州《论语》竹简是在宣帝五凤三年之前制作,那么可以忖测至少在宣帝、元帝时期统一化的《论语》版本在全国普及。由此可见,秦汉统一帝国对在国家制度运作中没有直接帮助的《论语》这样的典籍类木简的样式都要求规格化。那么,根据出土的两种《论语》来看,宣帝、元帝时期具有统一样式的《论语》存在的理由是什么?下面我们可以参看《论衡》的记载: 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 从以上《论衡》的两段记载可知,昭帝以后,《论语》开始被人们广泛诵读,使用的不是2尺4寸的“经”,而是8寸长的“传”这样的文本。这个长度短于教化、初学使用的《孝经》文本长度的1尺2寸。究其原因,是出于“怀持之便”的目的,从而比较容易地在民间社会普及儒教理念。这两类《论语》竹简使用的时间在公元前55年前和公元前45年前,即西汉宣帝五凤三年前到元帝初元四年前,由此而知,这个时期在汉代社会,儒家理念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宣帝时期“《诗》、《书》、《春秋》、《礼》、《易》等经无一例外都配置了博士官,五经博士全部存在”,而且从小就学习《论语》的宣帝和非常“好儒”的元帝十分强调儒家理念。因此在当时的民间社会,《论语》虽不属于五经,实质上被视之为经,是从皇太子到汉代民间私学的必读之书,同时也是传习《六经》的入门之作。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为了学习儒家理念,使用的文本中的一种便是定州汉墓《论语》竹简和平壤《论语》竹简。 事实上,在不是京师地区的中山国(现在的河北省定州市)和乐浪郡发现《论语》竹简,与武帝时期郡国学的建立以及公孙弘嗟叹“道”(儒家的统治理念)之沉滞的上书内容有紧密关联。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这也是主张教化的现实范围从京师逐渐扩散到边境这一观点的重要依据。在这种趋势下,参考元帝时期“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这样的记载,那么可推测,《论语》竹简出土的贞柏洞364号墓的墓主可能是担任乐浪郡户口簿制作等行政事务的属吏,当然也不能排除其担任五经研究官吏的可能性。贞柏洞364号墓同一墓中既可以看到郡县统治实际状况的户口簿,又存在反映强调“移风易俗”的统治观念的《论语》竹简,这也是汉代边境统治典型形态的重要史料。贞柏洞364号墓中出土的乐浪郡户口簿,与尹湾汉简以及户口总计方式以县为单位的松柏汉墓木牍的形态一样,使用“户+户口数+[少前.多前.如前]+增减数值/口+口数+[少前.多前.如前]+增减数值”的记载方式,由此可以确认汉代已经通过文书行政和典籍形式的统一化来实现郡县统治。而且典籍类的乐浪《论语》竹简不论是形制还是简册的编绳方式、类似的符号使用以及书写用的环形书刀与它同时出土,这些情况,和内地有简牍出土的墓葬很类似。因此,乐浪《论语》竹简及与它有10年时间差异、但具有同一形制的定州《论语》竹简极有可能同属一个系统。如果那样的话,考虑到当时通行的鲁论系《论语》也存在偏差不是一致的情况,有可能定州和乐浪《论语》都是在民间社会通用的不同版本的形态,这中间有一部流入到汉代边境地区的乐浪郡。 相反,宣帝和元帝时期儒家理念在边境地区的普及,不仅仅局限于乐浪地区。另外让人瞩目的还有《敦煌悬泉置汉简》中出现的《论语》卷一九《子张》篇的残片以及与儒家典籍相关内容的残片,主要内容如下: 1)乎张也,难与并而为仁矣。·曾子曰:吾闻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必也亲丧乎。·曾子曰:吾闻诸子,孟庄子之孝,其它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 2)子张曰:执德不弘,通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 上述两简都是敦煌悬泉置地区出土的,其中第一个木牍长23cm,宽0.8cm,章与章之间使用黑点作为间隔。其主要内容是《子张》篇的一部分,和目前通用的《十三经注疏》比较,简文中添加了“而”字,“吾闻诸子”一句在现行版本中写为“吾闻诸夫子”,“其它可能”中的“它”写为“他”,“孟庄子之孝”的最后部分现行版本中插入了“也”字。第2枚木牍长13cm,宽0.8cm,章开始的部分也用黑点来标记,简文内容与《十三经注疏》比较的话,“执德不弘”在现行本中为“信德不弘”。虽然简文与现行通用本文字上有若干出入,特别是第2枚木牍的内容,在定州《论语》简中没有发现,它作为复原西汉中、后期《论语》文本的重要材料这一点还是无误的。 而且,悬泉置汉简中除了以上与《子张》篇有关联的内容外,还可以确认类似性质的内容,即“之祚责,恶衣谓之不肖,善衣谓之不适,士居固有不忧贫者乎。孔子曰:‘本子来…’”及“欲不可为足轻财。彖曰:家不必属,奢大过度,后必穷辱,责其身而食身,又不足”,但其出处并不明确。1930-1934年罗布卓尔遗址中发现了宣帝、元帝时期使用的《论语·公冶长》内容的1枚残简。与此相同,在河西地区发现了西汉中后期以后的《论语》简,说明这个时期《论语》在河西边境地区得到了传播。我们要注意的是,定州和乐浪《论语》是竹简,而西北地区发掘的《论语》简都是木简。这是因为从内地流入的《论语》文本使用了当地的胡杨、松木等书写材料抄写。 关于河西地区儒教理念的普及,还有宣帝、元帝以后的相关记载: a)河平□年四月四日,诸文学弟子出谷五千余斛。 b)又造立校官。(1)自掾吏(史)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并免除徭役。(2)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3)郡遂有儒雅之士。 作为武威汉简中的一部分,可以推断a的记载时间是在西汉成帝河平年间(前28-前25)。从“诸文学弟子”可见,这些人已经熟悉经书,由此也可以推测西汉后期武威郡儒学的普及。b记载的是建武年间(25-55)担任武威郡太守的任延在这个地区建立学校的情况。b-(1)中受教育对象是武威地区具有实质性影响力的掾吏(史)的子弟,接受国家的恩泽到学校接受课堂教育,并免除徭役;b-(2)可见教授的内容以及授业全部结束熟练文章者将被录用为小吏。总之,官府为了强化对河西地区,尤其是对外族的统治,很重视河西出身的掾吏的作用。任用河西地区本地出身者作为郡县属吏是当时地方官吏任用的惯例,这样的现象毫无例外地适用于汉四郡地区。这可以从汉武帝在玄菟和乐浪地区设置郡时,“初取吏与辽东”的记载得到确认,“初”的意思也许是汉四郡设置当时,在b-(1)、(2)记载的时间之前。换句话说,汉四郡设置以后,经过一段时间后,会任用当地人为属吏。汉建武六年乐浪郡废除东部都尉,选拔隶属于县的渠帅,代替县设置侯国,主簿和诸曹全部从秽民中选任,这样的记载虽然和河西地区设置学校和教育的记载不同,但与b-(1)、(2)一样可以反映出这一地区的本地人参与了郡县统治。 经历了b-(1)、(2)所载的阶段后,河西地区因为有了b-(3)的“儒雅之士”,儒学变得普及,东汉时期这个地区虽然是边境,但同样出现了侯瑾和盖勋这类儒者。这样的情况从武威地区发掘的49号墓的性质中得以确认。这个墓的墓室长4.19米,宽1.88米,墓主可能是东汉中期(顺帝、冲帝、质帝)的官吏,或是地主阶层,引人注目的是其随葬品中有漆骊冠即进贤冠和木印。《后汉书》中已经说明进贤冠是儒者的服装,木印正面刻有“森(?)私印”、背面刻有“臣森”,由此可见墓主人的身份是具有极强儒家性质的官吏,这也揭示出河西地区儒学普及、学校建立的结果便是儒者们的出现。 虽然在边郡设置“学”或者任用当地出身的官吏,最初是为了稳定边境地区的统治,但从根本上是为了顺应西汉统治,自然而然地实现“移风易俗”。景、武帝年间,蜀太守文翁教民读书法令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教化百姓。虽然与一些地域依据“习俗”或者“乡俗”的统治相反,从秦简的内容看,教民法令是为了消除不同的传统和惯例,从而实现统治的一元化,并且要求有效实施这些法令。而且,在《居延新简》中有很多强调对小吏“功”、“劳”的文书,如E.P.T50:10简有“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也可窥见边境地区法律的熟知和强制程度。 那么,文翁教民读书意味着什么?河西地区发掘的汉简内容中,有为了识字而使用的《仓颉篇》或者《急就篇》,还有反映官吏的文书写作能力有无的考课———“史”或者“不史”的内容,以及《二年律令·史律》中“史”“卜”“祝”等的子弟为学童被任用为县属吏的规定。与此相关,《汉书》卷三○《艺文志》记载了学童能力考试的内容,“能讽书九千字以上”者任用为史。在同一记载中,史的子弟作为学童,在3年学习期间能诵读5000字以上者任用为史,郡又以八体课之,太史诵课,选拔成绩最好的一人作为县令史,这样的规定要求培养能优先担当文书行政的小吏并熟知相关法令。 因此,文翁在蜀地设置学校,其教民读书的内容不是“诗书礼乐”之类的内容,而是通过“移风易俗”来普及的统治理念及其相关的内容。平帝元始三年(3)郡国设置学,同时各个庠序设置孝经师,凉州刺史宋枭为了风俗教化而让各家各户抄写《孝经》来习读《孝经》,若将其联系起来思考,文翁教民读书可能是希望在边境地区,通过使民众熟知像《孝经》、《论语》这样内容不多的文本来提高统治效率,从而贯彻文书行政、普及统治理念。 因为汉简中有识字简的出土,或者官吏们“不史”的情况,很容易推测出边境地区吏员识字水准相当低。由此可以看出让民熟知经书内容也不是很容易。因此,在《四民月令》中可以看到,正月、十月,为了学习五经,成童入太学,正月、八月、十一月学习《论语》和《孝经》,幼童入小学的命令,并且,主张“王霸混用”国家统治理念的宣帝在18岁以前也学习《诗》《论语》《孝经》,这些至少可以反映出汉代社会《孝经》和《论语》文本的普及,渐次普遍化,而定州《论语》竹简和乐浪《论语》竹简便是当时全国普及《论语》的一部分。  三、纸木并用期的《论语》普及 西汉时期,以木简及竹简为主要书写材料的《论语》是流通的书写物,这一情况到东汉时期也没有大的变化,竹简及木简《论语》依然流通。然而,不能否定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蔡伦纸的发明引起书写材料变化这一事实。蔡伦之前也有纸的使用,在肩水金关遗址、放马滩汉墓和悬泉置遗址内都发现了纸。不过那时的纸不是作为文书和书籍而使用的,主要为包装或绘制地图而用。作为书写材料,纸的应用虽是从所谓的“蔡侯纸”开始,只是说蔡侯纸慢慢地在中国社会内普及使用,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简牍书写材料一时间就变成了纸。关于蔡侯纸使用后的书写材料,在文献中也有反映。《后汉书·吴祐传》载安帝时期南海太守吴恢的儿子吴祐随父赴任,对他父亲制作竹简书写经书进行劝谏;还有大约公元190年公孙赞伪造诏书的行为;另外还有景初二年(238)曹魏明帝临终前决定由曹爽代替燕王曹宇,将后事托付给曹爽,刘放、孙资同意后建议起用当时的权臣司马懿来保护皇室,明帝准备黄纸书写诏书。这三则史料反映出并非以元兴元年(105)为起点书写材料就从木简转化为纸了。长沙走马楼吴简由9万余枚竹简构成,楼兰地区出土的3-4世纪700余件木简,书写的文字材料时间相当于三国魏到西晋时期。也就是说蔡侯纸发明后,原来的书写材料木简或者竹简并没有马上直接被纸代替。 尽管如此,不能否认的是从3-4世纪以后,书写材料正在从简牍向纸过渡。上述楼兰罗布泊发掘的700余枚出土文书材料的时间,可以区分为汉代和魏晋时代,其中有70余枚汉代木简,而魏晋时代的木简和纸都有出土。魏晋时代出土文字材料可以分为书籍、私信、簿籍、符、检、公文书等类别。汉代的书籍类和簿籍类大部分在竹简上书写,魏晋时代主要是木简和纸并用。因此,斯坦因搜集的楼兰文书M.192中《论语》“学而”的一个句节“子曰学……(残存)”也可以反映书写材料的转化过程。一种看法认为它是完全成型的书籍的一部分,另一种说法认为它是学习《论语》并且将一部分的句节在纸上练习书写,而后者更为妥当。因为就像同一地点发掘出土的识字教育用的《急就篇》文书一样,这可以作为学习《论语》并在纸上练习一部分句节的习书来理解。并且,这是与后代敦煌和吐鲁番地区出土的3-4世纪《论语》写本相同的种类。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经书是作为学习用的教材在楼兰地区得以使用。同时,这个地区只出土了汉代写成的《论语》竹简,并没有发掘出之后的《论语》木简。因此,唐代的阿斯塔纳古墓群中出土了在纸上记录的《论语》完帙本的形态,与咸通十五年(874年,乾符元年)、署名为学生身份的王文川的《论语序》以及写着大中、乾符等年号的《论语》的发现,至少可以推测在8-9世纪以后,普遍使用纸书写的《论语》。伯希和、斯坦因在敦煌地区发现的文书中,有经书、千字文和道经共30种。在这些文书中《论语》占有19种之多,它的内容里有郡学(P3783)、县学(P2618)、寺学(P2618+S1586)等名称,由此可知当时官学、寺学以及地方学校里,《论语》都是必修的书籍。 在中国,纸张发明后,未发掘出竹简和木简书写的、即所谓的“书籍简”《论语》,只出土了书写在纸上的《论语》。与这一情况不同,在6-7世纪韩半岛(新罗和百济)和8-9世纪日本的《论语》木简被发掘出来。刘乐贤先生认为在木简和纸两种书写材料并用时期,木简仅在特殊的情况使用。笔者推测韩半岛和日本的《论语》木简,在纸作为书写材料的情况下因为不同用途使用。到现在为止,韩国出土的《论语》木简只有2枚,即金海市凤凰洞(1999年发掘)和仁川市桂阳区所在的桂阳山城(2005年发掘)两地分别发现的1枚木简,其出土的地区不是王京的中心地,而都在地方,这是它们的共同点;另外,其书写的主要内容都是《论语·公冶长》的一部分。 根据釜山大学博物馆的发掘报告书内容,金海凤凰洞木简应当是《公冶长》中半部分的内容,残存的木简长20.6cm,宽为1.5~2.1cm,四个面的内容书写如下: 这个木简的形态为“觚”,汉代形态为“觚”的木简主要为识字用及识字教材、文件内容草稿,或是为了读书而抄录的经书等。有的学者指出如果考虑书写的内容记载原则为“一章一觚”的话,《论语》木简也可能是记载《论语·公冶长》篇的特定章句的整体,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比较妥当。 按照木简同一层位一起出土的陶器类型推测,木简的年代大约在6世纪后半期或7世纪初期。虽然发掘初期有的学者推测这枚木简为“习书木简”,但是它与中国和日本发掘出的习书木简同一字句反复书写不同,由此推断这个木简是为了特定目的而制作的学习用具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具有五面体形状的桂阳山城《论语》木简,也保留了《论语·公冶长》篇的一部分内容。根据发掘报告书,这枚木简长49.3cm,宽2.5cm,文字部分长为13.8cm,这枚木简也是按照“一章一觚”的书写原则,在有比较完整文字的第3面上一个字大概1.3cm,由字的大小及“章”的字数来推测,木简大略长为96cm。直到现在可确定的主要内容大体如下: 与桂阳山城出土的《论语》木简的使用时期相关,在遗址的集水井护岸石筑上部出土了刻有“主夫十”铭文的瓦,可知从高句丽时代到新罗时代“主夫吐郡”的存在。在木简出土的集水井底层(Ⅶ层)还有底面为圆形的短颈壶出土,这个短颈壶具有4-5世纪百济陶器的共同特征,它和木简的使用时代为同一时期。即便如此,笔者认为对此应该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从出土的2枚《论语》木简的特征来看,将其理解为单纯的习书木简多少有些牵强。在中国汉代木简中找不到与《仓颉篇》相同的字句练习的痕迹,而《论语·公冶长》的部分内容具有很强的抄写目的。 日本也出土了《论语》木简,它的样态和韩国木简稍有不同。在日本,习书木简出土的遗址达115个之多,以时代为序的话,古代有101个遗址,中世和近世有14个遗址。习书木简的出土地点不仅有都城及其周边的遗址,也有地方官衙遗址。以上习书木简当中,与《论语》有关的木简到现在为止介绍的有29个。出土地域也不仅仅局限于中央地区,而是分布在全国范围内。虽然发掘出土的日本木简中,还写着《尔雅》、《王勃集》、《千字文》、《春秋》、《尚书》、《本草集注》、《乐毅论》等内容,但《论语》和《千字文》木简占压倒性的多数。而且,考察桥本繁先生整理的《日本的〈论语〉木简出土一览》,《论语》木简可以大略区分为经书内容抄写形态和为了熟悉字句而抄写练习这两类。细分之,出土的《论语》木简可以分为一种可见《序》、《学而》、《为政》、《八佾》、《公冶长》、《尭曰》等篇名,同一的字句没有重复的简;另一种为不见篇名而同一字句重复的简这两种情况。以下我们只引用并抽选后者情况如下: 由上表可知,《论语》木简不仅在平城宫宫都出土,在对当时社会政治观念上发挥着中枢作用的神社和东大寺等地区内也发掘出土。在以上地区出土的《论语》木简中,很难认为同一字句反复书写便是单纯乱写的书写形态。同一汉字的反复书写形态中,表现出想要熟悉有关古字的意志,也内含了熟悉文字的必要性。在古代日本,关于《论语》的流传,可见《古事记》“应神天皇条”中所载百济照古王通过和迩吉师王仁传送了《论语》10卷和《千字文》1卷给日本。可是,这个记载和史实并不相符。因为若应神天皇实际存在的话,其时期大概在5世纪前半期,而直到6世纪初,中国南朝时代的梁朝大臣周兴嗣为了初学者才编纂了汉字文本《千字文》,这和上述《千字文》在古代日本普及的时期不一致。不过,若考虑到最近在韩国和日本出土了形态差不多一样的《论语》木简这一点,《古事记》记载本身虽有不可信的一部分,但它也反映了编纂时的7-8世纪时的社会状况。 那么,《论语》习书木简在什么时候、被谁、以何种目的使用呢?首先,有必要推定上述《古事记》记载内容中“《论语》10卷”的具体内容。依据《养老学令6》“教授正业条”可知,《论语》文本中使用了郑玄和何晏的注释书。尤其是平城宫出土的《论语》木简中有“何晏集解子曰”,兵库县裤狭遗址中出土有《论语序何晏集解》,而《养老学令6》的《论语》相关记载与以上二者相同,由此我们不能认为7世纪后半期以后《论语》的接受和《古事记》的相关记载绝无关系。 与之相关,不是在宫都地区,而是地方出土的,我们推测为7世纪后半期的《论语》木简,如长野县屋代遗址35号的“子曰学是不思”以及45号“·亦乐乎人不知而”木简的出土,或者是德鸟县观音寺遗址中发掘的四面体《论语》木简,似乎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线索。观音寺遗址《论语》木简的残存部分左侧面的内容为“子曰学而习时不孤□乎□自朋远方来亦时乐不知亦不愠”,也和35号、45号同样是对《学而》篇的习书。然而,也很难将地方上发掘的《论语》木简判定为单纯的习书简,因为没有看到木简前后面书写的内容中同一字句的重复。因此,以上这种7世纪后半期单纯的习书行为,可能是想要熟悉《论语》句节,也是正式地接受汉字文化的一环。 自7世纪以来,不仅是单纯的习书,还通过渡来僧、留学生及留学僧的归国,还有从百济亡命而来的贵族,来学习《论语》等典籍内容,这是吸收汉字文化的开始。一方面,通过接受文书行政和律令,古代国家体制渐次完善;另一方面,为了统辖中央和地方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运作,文书行政及其吸收变得越来越必要。不仅在中央政府采用文书行政,地方上的国府和郡家等也广泛普及汉字文化。以上情况可以在兵库县裤狭遗址出土木简的书写内容中得到确认: ·子谓公冶长可妻【正面】 ·右为蠲符搜求【背面】 这支简的正面和背面的意思完全不相通。背面的“蠲符”是与“课役免除”有关的文书。反映古代国家的思想理念和行政层面的文书共存在一个木简上。而在平城宫遗址也出土了正面和背面意思完全不同的《论语》木简。这种情况不是抄写论语章节的部分内容,而是为了单纯地熟悉字句的习书内容。然而,不管是何种情况,《论语》木简的书写者都是官吏。 和日本木简比较,到现在为止出土的新罗以及百济木简的最具特征的一点,便是多使用多面体的木简。尤其是《论语》木简都是多面体木简,其内容不是单纯的习书记录,而是《论语·公冶长》的部分内容。这一点和日本出土的《论语》木简,在形态和书写内容上有明显的差异。当然也存在例外,在德鸟县观音寺遗址中出土的多面体《论语》木简在形态上与金海凤凰洞出土的《论语》木简非常类似。而且,有的学者认为在新罗国学作为学习和评价方法的“读书三品制”中,《论语》为必修科目;新罗的“金官小京”地区的“骨品”身份的人是通过《论语》木简而熟悉文字,从而提高成绩晋升为官吏;有的学者指出日本学令所见《论语》木简文本和学习《文选》的背景与新罗国学有紧密联系。以上这两种观点也可以反证观音寺出土木简和金海凤凰洞出土木简的关联性很高。因而,新罗设置国学的同一时期,日本也设置了国学,这反映出和新罗一样的情况,即地方豪族们通过观音寺遗址发掘的《论语》木简学习以及按照成绩而晋身为官。 新罗和日本通过《论语》学习而进出为官的情况,可以反证古代律令国家体制的形成,以及同时正在向以儒家理念体系为中心的国家统治秩序转变。并且,官吏们学习论语或者书写《论语》习书的这一特征,早在汉代下级官吏根据文字的习得与被区分为“史”和“不史”、“故不史今史”这样的考课中反映出来,通过《论语》和《孝经》的学习从而确认为官者的进出一样,7世纪以后新罗的读书三品制中国学毕业时考试《论语》是成绩评价方法,同时日本也以此作为为官者进出的途径,地方豪族们对《论语》积极的学习态度,成为跟随向律令国家转换的时代理念而确立的不可避免的标准。 结论 在理解东亚古代木简时,研究各个地域出土的木简形态的类似性,在说明木简的系统发展过程中虽然有效,但通过木简记载内容来阐明古代东亚汉字文化的性质是有限的。韩国及日本的古代木简使用的时期大体在6世纪末到8世纪末,因此,通过这个时期从中国流传而来的汉字文化和木简的相关性,对古代东亚社会进行实证研究成为可能。 古代东亚国家的中央集权制统治,是吸收从中国流传的律令体制而成为可能的,这样说并不为过。通过文书行政,中央和地方的有效统治体制的确立、以儒家为代表的统治理念的普及等,构成了以上古代国家成立的重要要素。因为以上要素都是以汉字为媒介而传播、被接受,所以通过熟知汉字来进行文书行政、普及统治理念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对官吏们来说,具有一定水平的习书以及熟知《论语》《孝经》这类与国家统治理念密切关联的经传,是必须的要求。能确认与此相同的古代东亚社会状况的实证材料,便是出土文字材料《论语》。 与中国出土的定州《论语》竹简、敦煌悬泉置汉简中所见《论语·子张篇》的部分内容以及日本出土的29个《论语》木简相比较,韩半岛出土的《论语》,只有平壤贞柏洞364号坟出土的论语竹简、金海凤凰洞出土的《论语》木简以及仁川桂阳山城的《论语》木简这3个。现在已经证明贞柏洞364号墓《论语》具有竹简册书的形态,和定州《论语》竹简的形态及书写方式有很多的类似。而推定为7世纪时期的其余两处《论语》木简书写的都是《公冶长》篇的部分内容,它们和单纯的习书简不同。682年在新罗设置国学,《论语》在国学入学和任用官吏时是必读的书目,在结束学业的时候,通过授予大奈麻、奈麻等官位可以就任下级官吏。 日本出土的《论语》可以分为学习用和习书用两个类型,韩国的木简与这样的性质稍有不同。观音寺遗址出土的《论语》木简不仅在形态上与韩国木简有很大的类似,而且习得的过程也是通过国家制定的法令或制度进行,这一点可以解释为国家主导《论语》的普及,即统治理念的扩散。然而,日本《论语》木简也有不同特征,其正面和背面书写的内容找不到连续性,这样的木简反映出在实行“文书行政”的律令统治和执行思想理念统治的官吏的状态。 与之相同,我们可以看到在东亚出土的木简,不仅在形态上具有类似性,而且伴随着古代律令国家的成立,东亚木简广泛使用,它们和依据文书行政及其相似的律令统治,以及并行的统治理念的普及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木简来纠明古代东亚社会的性质,理解“小天下”和“大天下”的观念区分。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