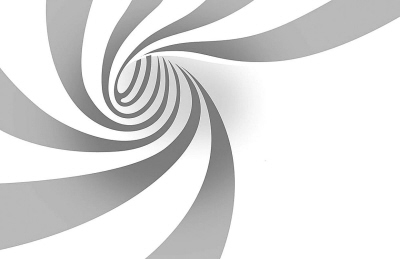 读吴小如先生的学生编写的《学者吴小如》一书,最过目难忘的是小如先生的冰雪精神,赤子之心。书中特别提及其少作对名家以及他的老师的评点,直言不讳,率真而激扬,真是令人格外感喟。因为面对今日文坛红包派发、商业操作的见多不怪的吹捧文章,这样的文字,几成绝响。 看他批评钱钟书:“一向就好炫才。”说钱虽才气为多数人望尘莫及,但给读者“最深的印象却是‘虚矫’和‘狂傲’”。他批评萧乾的《人生采访》文字修饰功夫“总嫌他不够扎实”。他批评师陀的《果园城》“精神变了质”:“失败的症结不在于讽刺或谴责,而在于过分夸张——讽刺成了谩骂,谴责成了攻讦。”他批评巴金的《还魂草》拖泥带水,牵强生硬,“一百多页的文字终难免有铺陈敷衍之嫌”。 就是自己的老师,他的批评一样不留情面,敢于指手画脚。比如对沈从文的《湘西》等篇,他说道:“格局狭隘一点,气象不够巍峨。”“作者的笔总还及不上柳子厚的山水记那样遒劲,更无论格古情新的《水经注》了。”对于废名,他直陈不喜欢《桃园》,因为“没有把道载好”,“即以‘道’的本身论,也单纯得那么脆弱,非‘浅’即‘俗’”。 这让我禁不住想起法国音乐家德彪西。2012年,是小如先生90岁寿,是德彪西诞辰150周年。两位年龄相差整60岁一个甲子的人,直率的性格以及对待艺术的态度,竟然如出一辙,遥相呼应,相似得互为镜像。 年轻时的德彪西,一样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说贝多芬的音乐只是“黑加白的配方”;莫扎特只是“可以偶尔一听的古董”;他说勃拉姆斯“太陈旧,毫无新意”;说柴科夫斯基的“伤感太幼稚浅薄”;而在他前面曾经辉煌一世的瓦格纳,他认为不过是“多色油灰的均匀涂抹”,嘲讽他的音乐“犹如披着沉重的铁甲迈着一摇一摆的鹅步”;而在他之后的理查·施特劳斯,他则认为是“逼真自然主义的庸俗模仿”;比他年长几岁的格里格,他更是不屑一顾地讥讽格里格的音乐纤弱不过是“塞进雪花粉红色的甜品”……他口出狂言,雨打芭蕉,几乎横扫一大片,肆意地颠覆着以往的一切,他甚至这样口出狂言道:“贝多芬之后的交响曲,未免都是多此一举。”“过去的尘土不那么受人尊重的!” 有意思的是,无论小如先生,还是德彪西,这样直率甚至尖刻的批评,当时并没有惹得那些已经逝去的大师们的拥趸者,和依然健在被批评者火冒三丈,或是急不可耐地反批评,或者带着嘲笑的口吻说其“愤青”一言以蔽之。这种对于年轻人的宽容,既体现了那些学人作家与艺术家的宅心宽厚,也说明那时的文化氛围,如当时的大气与河流少受污染。这是一种文化的生态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作家、艺术家与批评家,万类霜天竞自由,能够一起相得益彰地成长。 于是,小如先生以年轻时对前辈与老师直率的批评,和对艺术与学问的真诚态度,步入他以后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学问之门。德彪西也是这样,打着“印象派”大旗,以其革新的精神,创造了欧洲以往从来没有的属于他自己的音乐语言。在他32岁创作出《牧神的午后》时,法国当代著名作曲家皮埃尔·布列兹,就曾经高度评价并预示:“正像现代诗歌无疑扎根于波特莱尔的一些诗歌,现代音乐是被德彪西的《牧神的午后》唤醒的。” 说起那些少作,小如先生说自己是“天真淳朴的锐气”。燕祥说他是“世故不多,历来如此”。天真和世故,是人生与学问坐标系中对应的两极。我想,这应该就是小如先生的老师朱自清所说过的那种“没有层叠的历史所造成的单纯”吧。学者也好,文人也罢,如今这种单纯已经越发稀薄,而世故却随历史的层叠,尘埋网封,如老茧日渐磨厚磨钝。自然,如小如先生和德彪西年轻时的那种“天真淳朴的锐气”,也就早已经刀枪入库,只成为了可以迎风怀想的老照片。 但是,我一直以为,小如先生也好,德彪西也罢,他们年轻时的那种“天真淳朴的锐气”,其实更是一种如今文坛和学界所匮乏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存在,文人之文,学者之学,才有筋骨,也才有世俗遮蔽下独出机杼的发现和富于活力的发展。 小如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再有些人,虽说一知半解,却抱了收藏名人字画的态度,对学问和艺术,总是欠郑重或忠实。”对于今天的学术、艺术,或作家与作品,这段话依然有警醒的意义。对待上述的一切,我们很多时候确实是“抱着收藏名人字画的态度”,有些谦卑,有些妄想,有些世故,有些揣在自己心里的小九九,便有些欲言又止,有些王顾左右而言他,有些违心的过年话,有些成心的奉承话,甚至有些膝盖发软,有些仰人鼻息,只是没有一点脸红。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