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作者与小南一郎先生(左)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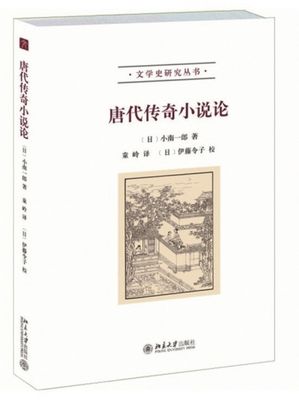 《唐代传奇小说论》,[日]小南一郎著,童岭译、[日]伊藤令子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第一版,30.00元 编者按:今年10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品牌书系“文学史研究丛书”推出日本学者小南一郎的《唐代传奇小说论》,受到学界和读者关注。小南一郎是日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大家,早年师从汉学史上大名鼎鼎的小川环树和吉川幸次郎,是京都学派的第三代嫡传弟子。小南先生善于从历史、考古、民俗学等角度切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跨学科的研究风格在日本汉学界独树一帜,对国内古典文学研究界更是具有借鉴意义。他前些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神话传说与古小说》也受到国内学界重视和好评。这样一位重量级学者,值得让国内更多读者认识和了解,为此,本报约请《唐代传奇小说论》译者、在京都大学短期客座的童岭副教授,于10月14日在京都对小南先生做了一次采访。 童岭:尊敬的小南一郎先生,又是两年不见了。这次很荣幸受北京《中华读书报》之邀采访您。您是海内外著名的汉学家,可否给中国的读者介绍一下您年轻时的求学经历? 小南一郎(下简称“小南”):我进京都大学是1960年,是反对日美军事同盟的政治运动的高潮时期。进学后不久,学生会决议罢课。我也参加过游行。我读完研究生课程时,学生们正在反对大学制度,赶出教授们,占领学园。办公室也搬到别的地方去,我在那儿作退学的手续。在这样动荡时代里,我在大学读书。但是学习生活十分充实。我的恩师是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两位教授。从他们那里亲切地接受过读书和论证的方法。在读研究生课程时,高桥和巳先生以副教授的身份调到京都大学来。高桥先生和我,在文学观念和学问方法上差异不少,因此跟他时常讨论。以那时的讨论为基础,我巩固了自己的研究方法。 童岭:您的博士论文《楚辞とその注释者たち》在朋友书店出版,很可惜这本书目前没有中译本。中国大陆和港台的学者对您关注最多的是中古小说研究,请问您的研究兴趣,是怎样从《楚辞》转移到六朝隋唐的“说部”上的? 小南:我的博士论文《楚辞とその注释者たち》的主要部分,是比较各类《楚辞》系作品,判别其中哪些作品的哪些部分是古代的,哪些部分是后世新加的。进而去分析“楚辞文学”是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属于楚文化的人们,本来是在共同体之中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然而,随着时代、社会的变化,他们从古代共同体之中切离出来。在那样的社会环境变化下,他们怀念遥远古代的同时,也对现实社会抱有很大的疑问与不满,这些,我认为都定格在《楚辞》的各类作品中了。 我想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小说与《楚辞》的研究是共通的。不论是志怪小说热衷于记录怪异的出现,还是唐代传奇小说选取恋爱不幸的物语来形成作品,其背景都是人们对当时现实的不满吧。 童岭:原来这样的研究理路是一以贯之的。我留学时有幸接受平田昌司老师之邀请,翻译您的《唐代传奇小说论》,现在译本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翻译过程中,感觉您对唐代小说的研究非常独到,比如您的关注点——“中唐”。此外,您的思路与“鉴赏流”“文献流”甚至是陈寅恪先生以来的“文史互证流”并不尽相同。您的研究时有妙入毫颠之处,时又给人惊鸿一瞥之感,请问您的小说研究,秉持怎样一种方法?受到哪些先贤影响最大? 小南:文学史研究是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分,广义而言,也可以认为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因此,进行文学史研究时,一方面严密的史料批判是不可欠缺的,另一方面也要遵守其客观性。然而,在多大程度上贯彻“客观性”,这是一个疑问。就我自己的研究而言,带有浓厚的所谓“现代”社会环境之色彩。研究者自身的立场,会对其研究有很大的影响。我自己在分析文化现象时,比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更加重视的是民俗学的视野。柳田国男的民俗学,或者是宫本常一的《忘れられた日本人》等著作,给我的影响很大。 童岭:您觉得唐代传奇与六朝小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换言之,是怎样的“内核”,使唐代传奇小说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小南:唐代传奇小说最大的特征,据鲁迅先生所言,是使用了有意识的虚构手法。如果不使用虚构手法,那么就无法描写社会与人生的真实——这样的意识一旦诞生,就给中国小说史带来了全新的空间。这种意识,也见于西欧近代小说。不过可惜的是,这一意识后来在中国似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就日本而言,平安时代创作了《源氏物语》,然而在此之后,我想就没有后继的类似作品出现了。 童岭:原来如此。那么冒昧问一下:您最喜欢的唐代小说的男性与女性形象,各是哪一位? 小南:唐代小说中,有特别好的男主人公吗?唉,女主人公喜欢的又太多了(笑)。开个玩笑了。其实我的小说研究,是不使用“人物形象论”的,所以关于主人公,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然而,将唐代士大夫阶层的精神性伤痕记忆定格下来的,毋宁说《霍小玉传》给我印象最深刻吧。 童岭:中国学界这几年,对于“五四”以来纯文学的概念重新反思。我拜读您的大作,感觉您可以运用考古学、史学,包括刚刚提到的民俗学等多种理论,同时核心又不离文学。请问您如何理解中国文学?特别是“唐宋变革”之前的中古文学? 小南:包括文学在内,不论是文化还是时代,我们都与过去的人存在着差异,甚至根本价值观都不相同。那么,为什么过去人遗留下来的作品,还可以被我们所理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说我们仅仅能就自己所理解的部分来评价,也许会误解此外的部分。虽然理解那些超越了时代和文化而具有共通性的文学作品,是有可能的,但是对此的议论,到底可以受容到哪一步,我对此颇为踌躇。 唐及唐以前重要的文学作品,大多是在价值观转折剧变的大时代中产生的。例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以古典的价值观为基础,在理解新时代的苦恼中产生的,从而《史记》获得了窥见历史之流的优秀视点。唐代传奇小说也是这样,它是在“唐宋变革”的大时代中产生的。所谓“唐宋变革”,历史学者谈论比较多,文学史学者不太涉及。我以前写过一篇《杜甫的秦州诗》(文载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杜甫特辑》),就是从唐宋变革的视角来看杜甫的政治立场。就唐宋变革本身而言,固然给社会、政治带来了巨大变化,如果在文学之流中考察,它同时也带来了价值观的变化——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这一时期,六朝以来门阀贵族的价值观开始崩溃,官僚阶层(特指皇帝周边的有干才的官僚阶层)新的价值观逐渐诞生。例如,《文选》中所收的文学作品,就不能完全满足新官僚阶层的内心需求,所以他们就追求唐宋八大家那样的文章。优秀的文学作品,并不只是单单宣传新时代的价值观,而是一方面充分理解了古典价值观的存在意义,另一方面又在痛苦地吸纳新价值观——在这对矛盾之上,产生了伟大的作品。 童岭:提到六朝门阀贵族,京都大学的学者对六朝文学多有专攻。“谢家轻絮沈郎钱”——您提到的高桥和巳先生,也是钟情于“六朝美文”,比如他对潘岳、陆机、江淹的作家论。高桥先生提出六朝美文的特色,一个是“个人情感的强调”;另一个是“显著的装饰性”。您如何看待小说以外的六朝诗文? 小南:我以前写过一篇叫做《六朝文人たちの梦》的文章,指出了当时人对于“才”的观念,与我们今天有很大的不同。在梦中获得了彩笔,六朝人的“才”是华丽的,他们的“才”与美文文学结合在一起。当时的文学,与其说表现个人的内心,不如说是将个人具有的“才”定格在作品上,后者的倾向在六朝时期尤为重要。 童岭:下面再请教一个关于六朝的具体问题。留学时,有幸收到您《〈世说新语〉的美学——以魏晋的才与情为中心》大作的抽印本。有一点至今记忆犹新:您说《世说新语》为了肯定魏晋高士自由表露情感,不惜用“低级趣味的轶事”来描写,但我们读了之后,并没有发现“否定的感觉”,反而读到了“真”与“善”。此外,您将西晋与东晋时代划分而谈的理念,亦令人耳目一新。台湾中研院的学者将您的美学观称为“京の味”(京都式美学)。 小南:《世说新语》这部作品成立于刘宋时期,是书写关于魏晋时期门阀贵族们生活态度的一部作品。提到西晋、东晋的区别,此书当然也受到了东晋初年被广泛提及的“清谈亡国论”的影响,因此该书舍弃了魏晋高士们生活方式所具有的政治性含义,专注于从美学的视角描写他们的生活。然而,我自己除了《世说新语》之外,也对魏晋知识人的政治性生存方式深感兴趣。 关于“京都式美学”,我想说的是:东京的学问,不论右派还是左派,都有政治性的倾向。但是,京都的学问只关注于人类的文化活动与精神活动。在这一点上,与东京的学风有不少差异吧。最典型的例子,可以举出关于中国历史上“中世”的设定,这一问题长久以来是东京学者与京都学者争论的焦点。 童岭:提到东京、京都之争。您如何看“京都学派”的特色,以及与清儒的关系?一般都认为,崇尚文史校雠传统的“京都学派”,与崇尚西学的“东京学派”,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体制与学风。但似乎有的学者认为并不存在“京都学派”。 小南:“京都学派”这种称呼,有各式各样的使用方式,其内涵也是不一定的。如果只是就从狩野直喜开始,到我们为止的“中国学”领域来看,那当然是受到清代朴学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论是京大的中国文学还是中国哲学研究都如此。我的恩师吉川幸次郎先生,生平一大壮举就是《尚书正义》的日语翻译。我自己也从吉川先生那里,受读过《公羊传》。清朝学者中,特别是高邮二王的著作给我的教益极大。然而另一方面,如何在清朝考证学的基础上,超越其学问方式,我想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童岭:您今后的研究计划,可以向我们透露一下吗? 小南:最近在集中阅读明清时期的宝卷,并去浙江省调查宣卷,大约一年一次吧。如何理解民间的宗教性文艺,目前我还在摸索之中。 童岭:最后一个问题,还是回到您的老师吉川幸次郎先生吧。他在《我的留学记》中说过:“中国天生就是我的恋人。”——这其实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高桥和巳先生将吉川先生的研究法称为“儒家的文学研究法。”但是,有些专攻古典文史的学者坚持研究中不要投入“感情”,要“纯粹客观”去研究中国,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小南:这其实也是属于研究的“客观性”问题,它虽然是不可欠缺的,但其客观性到最后能贯穿到什么程度,却很难说。我们只能尽可能努力保持研究的客观性吧。另一方面来看,一部文学作品,扩展开来看就是一个文化现象,因此必须与研究对象产生共鸣吧。如果不能从根本上产生共鸣,只是停留在客观地描写文化现象,这恐怕不能说是文学研究吧。 最后再提一下我的老师吉川先生,他是一位严于守礼的伟大学者。然而有时,自己本身却又有无视“礼”的简傲言行。平常学生们偶有失礼的行为,他虽然被激怒了,但也还能够保持容忍的雅量,这好似魏晋的诸贤吧。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