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振皆遗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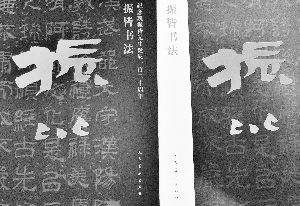 出版的《振皆书法》。本报记者 房毅 翻拍 前不久,《纪念魏振皆诞辰120周年——振皆书法》一书在兰州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魏振皆这个名字,在本人故去30多年后第一次被以如此郑重的方式推到了大众的视野之内。 这部书是由皋兰一个叫杨重清的商人捐资出版的。对于出书的目的,杨重清直言,就是要通过这本书,“恢复”魏振皆在书坛应有的价值和地位。 一本书的出版 36年前,魏振皆临终时,给学生留了句遗言:“有朝一日给我出个帖。” 不过,最后实现他这个心愿的,并不是他的学生,而是和他生前素未谋面的人。 尽管都是皋兰人,而且自己的家和魏振皆距离不足10公里,但是杨重清第一次知道这个“老乡”实属偶然。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商人的杨重清第一次认识到魏振皆的价值,源于他的那种“商业眼光”。杨重清是搞收藏的,收藏品包含了书画、玉器等。 “1993年在一个朋友家第一次见到魏老(魏振皆)的东西。”搞收藏的杨重清自然是个识货的人,当时的感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震撼,很想拥有”。这一次,杨重清深深地记住了魏振皆这个名字。“记住了这个名字,也就注意了解有关这个人的一切,包括他的作品价值。”杨重清很坦然地说,后来他还在古玩市场上了解到,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日本人收购魏振皆的书法作品,叫价一个字50元人民币,数字论价,而这个价格在当时就是一个干部一个月的工资收入了。“我醒悟了,也开始重视起来了。” 随后的一次碰壁,加剧了杨重清收集魏振皆墨宝的“冲动”。 “我听说魏老的一个姓杨的学生手里有七八幅魏老的作品,就专程去拜访,想再一次一睹为快,还想看看有没有机会买上一两幅自己收藏。”让杨重清没有想到的是,对方不但不卖,甚至连看都不让他看。一向要强的他就在走出对方家门的那一刻,发誓要收集魏振皆的作品。“当时确实也是赌上气了。”现在每每说起往事,杨重清还有一种“因祸得福”的感觉,他觉得正是因为那一次碰壁,加之当时也年轻,个性中充满了争强好胜,无意间推动了他,促使他在随后的十七八年间一直为收集魏振皆的墨宝而奔波不息。 秋子在接到参加《振皆书法》首发式的邀请的那一天才知道魏振皆的作品居然出书了。秋子多少有些吃惊,因为作为省内为数不多的研究魏振皆书法艺术的学者,多年来他一直有出书的想法,只是苦于收集不到东西。 “这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书,收录了魏振皆1925年至1965年40余年间创作的约200幅书法作品,绝大多数堪称其毕生心血创作的佳品力作。这本近300页、四色彩印、八开函套精装的大部头集子,无疑是一本对我们真正有益的好书,它足以让我们眼界一开,读之获启,研之得悟。”现为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的秋子说,“前两天,我的一个爱好书法的朋友还特意跑到我这里来找书,我说这哪里是我们甘肃出的书,它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的。” 其实,早在1982年甘肃就出版过一个魏振皆作品册,只是因为其中收集的作品数量极为有限,所以那个薄薄的册子在出版后即被淹没了,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 独行的书坛主角 书的主角——魏振皆,在研究者眼中,就是一个从黄土地上走出去又走回来并最终埋冢于黄土的知识分子。 1889年,魏振皆出生于皋兰县石洞乡,1909年入甘肃文科高等学堂学习,后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系。1918年毕业后东渡日本考察一年,应该是陇上最早的留学生之一。建国前曾任酒泉中学、武威师范、兰州一中、兰州女师、兰州师范、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等校教师、教育主任等职。建国后,以“具有相当学识”、“夙有声望的文人耆宿”被省政府聘为甘肃文史研究馆首批馆员。 “他毕生从事书法艺术的研究与实践,篆、隶、楷、行,无一不佳,功底扎实,结构严谨,笔法精到,并能神思独运,将楷、隶、行书体熔于一炉,创新出别具一格的‘魏体’,是世所公认的华夏书坛巨擘。”第一个把魏振皆写进中国书法史的是秋子。“事实上我是把他放在全国大盘子里进行反复研究的,就是放在这个平台上,他也是占了主角的。一句话,他是20世纪中国书法史上举足轻重的一个人物。”秋子认为,魏振皆能获得如此高的历史定位,完全是实至名归。 魏振皆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书法研究魏碑的时代,明末清初中国书坛掀起了崇尚魏晋书法之风,从魏碑中汲取营养,书坛呈现出自唐以来又一次创新的高潮。随着考古学的发掘,一大批年久失传的魏晋碑文重见天日,给书法界带来了新的冲击。书坛从唐楷图式中挣脱出来向魏晋时期——书法的孩童期去寻找一抹纯净的阳光,一批有识之士成了古典书法演变时期的探索者、首倡者和实践者,魏振皆先生就是其中一员。 “站在整个书法史的高度来看,魏振皆的最大贡献在于笔法的创新,以魏碑方笔参以帖学和汉简的逸气,着力表现‘屋漏痕’,即由缓转疾、中提后注、顿圆收尾的‘古钗角笔法’;同时,在结体上的创造,将魏碑与汉隶结合而形成真正外方内圆、结字有大有小、有敛有逸的‘魏隶’书体,又将行书笔意化于其中,形成颇为凝重有变且灵动活泼的‘魏行’书体,成为近现代书法史上独树一帜的戛戛独响;而在章法上的创变,即打破魏碑整齐划一的范式,采用行书布局,加大字距并力避着字并行的章法,大小、轻重、枯润、虚实千变万化,随心所欲地自由挥洒。”秋子说,魏振皆书法一生,走过与历史上多数书家并无大异的学书之路,与众不同的是,他成功提交的是这样一份令书坛难忘的答卷。 “所以,可以大胆地说,他就是甘肃现当代史上走在书法仪仗队前面的‘旗手’。” 秋子曾在多个场合说,魏振皆已然成为中国现当代书坛一个鲜明的符号,他不仅是甘肃书坛的骄傲,更是中国书坛的骄傲,他的艺术造诣及其书法品质,堪与林散之、于右任、沈伊默等现当代大家相提并论! “洞叟”的悲哀 然而,在兰州大学教授何裕的眼里,甘肃现当代书法史上的“旗手”,是一个活得极其小心谨慎的知识分子。 “上世纪60年代我们结识后他时常来我家或吃饭或聊天,更多的时候我们一起写写字,切磋切磋,苦难时期,家里没有宣纸,我们就在报纸上写,后来,我曾经几次专门给他备好了宣纸,希望他给我写点什么,他总是以‘等等’‘不急’推却了。”已经90岁的何裕今天说起故人往事,还是忍不住笑了。“他当时被‘地主’的成分压着,各方面都受到影响,而我当时是在兰州大学马列主义系讲政治课的。” 魏振皆的地主成分是怎样来的,作为好友的何裕是很清楚的。“解放前,当一个小学教员,一个月有10块大洋,而一个中学教员,就有40块大洋,大学教员则达到了上百块。”何裕说,魏振皆当教员手里有了钱,就在老家买了地,让弟弟种地,解放后,他的名下有土地,就这样成了地主。“这个地主成分让他不能不活得小心谨慎。”一生中遭遇的那段如同魏振皆一样的不公平的境遇,让何裕完全能理解魏振皆当时对人抱有的戒备之心。 “文革”开始之后,何裕和魏振皆的交往因为各自都自顾不暇而中断了,“文革”没结束,魏振皆就去世了。“听说他曾在山洞里生活,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不过,由此可见其生活境遇的不堪。”言及此,何裕不禁慨叹。 魏振皆曾住过的那个山洞,杨重清进去过。 “1969年,魏老被打成牛鬼蛇神遣返回皋兰老家,住进了古时乡民因避匪在山上开凿的窑洞,随遇而安是魏老当时唯一的想法。”杨重清说,在他爬上梯子进入那个距离地面足足5米高的窑洞时,阴冷黑暗让他顿时觉得凄凉,窑洞的一面墙壁上凿有一小窑孔,墙面颜色发黑,窑孔上方是魏老用红油漆书写的“思时谨慎,和平庄重”八个魏碑体。“那个窑孔是当年魏老摆放灯的,当时就是在那样的境遇下他也没有放弃他的书法。” 让杨重清感慨万分的是,在京师读过书,又漂洋过海在日本留过学的魏老,算得上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物,可是,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他的生活又回到孩提时代缘木上下的状态,“目睹窑洞的一切,对比前后,让人不由得心头发沉……” “如果当初从日本回来继续留在北京,魏振皆的前程就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了。”杨重清不止一次地这样替魏振皆假设过。 秋子一直也很疑惑,想不通魏振皆从这里走出去到了京师,从京师去了日本,缘何又要从日本来到这里。“也只能认为这就是甘肃人的守土意识吧。” “可惜一生” 杨重清的假设和秋子的疑惑,最终落在一个共同点上——在甘肃,魏振皆是被历史“耽搁”了,这也就是杨重清缘何不惜花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