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德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术特征 1、德国20世纪汉学研究史表明,汉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的分支,它始终受到政治和经济的左右 德国大学东方学系或汉学系的建立就带着强烈的政治功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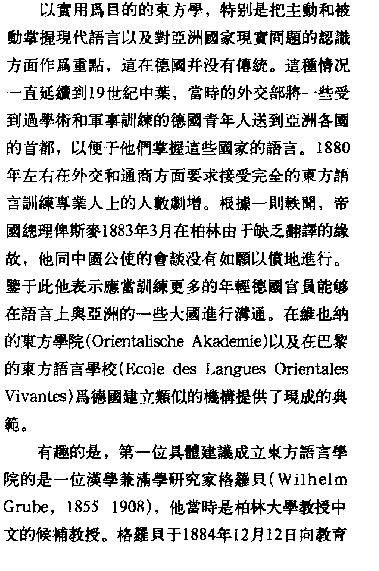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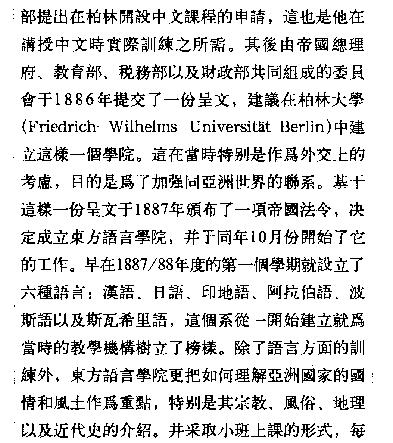 文化是一个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的概念,它是一个民族经过千百年积淀而形成的共同的民族心理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必然选择。不同的民族心理造就了不同的文化类型,从而形成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文化交流也由此而产生。然而,超地域的文化交流又不得不面临两大障碍:一个是地域隔绝一个是心理的排斥。这二者使文化交流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呈现不同的形式与内容,引发各类矛盾与冲突,并折射出该时期各民族的文化心态。地域隔绝为各种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独自发展的空间和时间,是形成一元化文化体系的前提与保障,而同时也使各种文化间缺乏相互影响与渗透。因此,在形成这种一元化文化体系的同时,也形成了以文化本位主义为中心的文化心理结构,它制约着一个民族的内在心态、精神素质、思维框架、情感方式和心理定势。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经过千百年的沉淀而转化为对外来文化的下意识排斥,它对文化交流的影响远远甚于地域的隔绝。地域隔绝可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逐渐消除,而心理上的排斥就像一道无形的墙难以逾越,对文化交流产生微妙而复杂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直接反映就是文化交流中的实用主义。正如罗伯特•莫非所说:“一个外来文化因素是否被接受的关键要看这个因素与接收社会的文化体系的吻合程度。……如果一个文化项目被接受的话,都是经过解释、改造的,使其与接收文化结构相适应。”[1]从老庄哲学在德国表现主义文学中的兴衰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罗伯特·莫非 文化和社会人类学[M] 吴玫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157)。 2、与欧美汉学界相比,德国大学的汉学研究总体上还是恪守传统路数,走的是严格的兰克式的考据学的道路,不似美国热热闹闹,新理论迭出,新思路纷呈; 欧美之间传统汉学与当代汉学的分歧逐渐加大,呈现不同的研究趋向。 美国在二战以后兴起所谓现代汉学。现代汉学与传统汉学之间不仅有上述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法上的差别,在研究对象、学科类别以及研究者出身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别:传统汉学是以包括古典文学在内的中国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现代汉学则是以现代和当代的中国文化、社会政治、风俗民情为研究对象;前者指向人文现象,比较单一;后者属于社会学,比较宽泛;前者的研究方法朝向人文现象的“特殊性”,后者倾向于人文现象的 “普遍性”;前者研究的主体是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后者则包括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乃至经济学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两派的分歧并未调和且有扩大的趋势,正如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许理和(Erik Zurcher)教授所说的:“比起1960年以后的美国,欧洲的中国现代、当代研究发展略显迟缓。欧洲传统汉学直到六十年代底、七十年代初,才领教了这个急速发展成长的双胞小兄弟。在许多欧洲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当代中国研究的欣欣向荣曾导致双方的误解和紧张。这股 ‘新兴势力’(通常非由《四书》陶养成器,而是受政治学、经济学训练)指控传统汉学家是已经僵滞的老古董;汉学家则为当代中国专家打上浮浅和政治化的标记”。 波鸿大学马汉茂(HelmutMartin,1940-1999)教授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讳莫如深地冷淡了数十年以后,首先在汉语世界里出现了对德国的中国学研究的介绍,然而这些介绍在相当程度上只涉及了一点皮毛。北京的社会科学院新出的辞典里已经有了一些传记词条,但它们基本上没有体现出传主的真正研究状况。还有些零星的介绍发表在《国际汉学》杂志上。已出版的内容单薄的专著更是一种误导,例如张国刚的概况式的描述。这些努力尽管粗糙,但却是个新的开端,对这样的开创性的尝试应该赞赏。这一状况恰恰说明,到目前为止,德国方面研究这一学科的可靠而全面的发展史还没有写出来,因此,中国的这些学者和作者们没有东西可资参考,他们也可能不愿意在原始资料上下功夫。(Chinaunddie Hoffnungauf Glueck: Paradiese-Utopien-Idealvorstellungen, Carl Hanser Muenchen, 1971。DasAntlitzChinas, CarlHanser, Muenchen,1971。) 马汉茂教授将其主要原因归结为德国方面缺乏力作,这是实情,也是客气话。其实,德语文献中汉学研究史的单篇资料大量存在,基本能够满足中国学者做整合性的研究。德国汉学家大量的优秀学术著作至今没有系统地翻译成中文。当然,制约这一工作的,有语言隔阂的因素在内;更紧要的,恐怕还是美国人话语霸权在起作用,就如同经济学界一样,我们唯美国马首是瞻,忘了也应该了解欧洲。 3、在学术思想方面,中国学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是诸子思想,尤其是老庄思想和儒家思想。 以欧洲文化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也同世界上其他的优秀文化一样,有其保守性和排它性,因为没有这一点,本民族文化就无法赓续,就会被其他民族文化所侵夺吞并。作为民族文化中最原始也是最稳定的因素——“语言”,就充分体现这一特征。这一特征也出自民族习性,即民族的自尊和自豪感,这当中的恶性发展(或被别有用心的当权者所误导),就便成民粹主义或文化霸权,如纳粹的“雅利安人至上”,日本军国主义的“大和民族至尊”,乃至“欧洲中心论”和“大汉族主义”等等。例如,我们一提到西方对中华文化的仰慕和学习,就会举西方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伏尔泰等人改编中国的元人杂剧《赵氏孤儿》,但如果对这个过程详加寻绎而不是断章取义,就会发现它的政治动机和文化利用成分远大于对中国戏剧乃至中国文化的认识和认可,而且在接受的过程中,更多的表现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感和对中国戏剧理论和表演形式的蔑视: 老庄哲学思想在德国表现主义文学运动中曾流行一时,但最终却归于沉寂。本位文化心理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这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文化心理,对文化交流起着消极的作用。 在诗文研究方面,前面提到的盛行于二十世纪初的英美意象派代表人物庞德的《神州集》,无论是创作理论、创作素材还是写作技巧都明显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但有些西方学者还是不承认这一点,美国学者休·肯纳说:“与其说《神州集》是中国产品,倒不如说是美国产品更令人注目”。美国著名诗人艾略特甚至认为《神州集》的风格“与中国灵感并无多大关系,它是庞德先生自身风格的发展”。 问题也还有着另一面,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着世界共通的、相互补偿的学术共性。欧美早年汉学家学者走的是乾嘉学者治学之路,而且代有传人。这批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作家作品时,对本土文学理论和文学观念大多有种自我审视、自我批评的自觉,并注意融入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这当中,植根于思想深处的中国学术传统在或隐或显起着某种作用。 我们必须看到,一些外国学者是从热爱中华文化出发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这当中更有一些华裔学者,他们在港台或大陆曾受过系统而严格的中国学术训练,然后才负笈远游沐浴欧风美雨,按他们自己的说法,青少年时代的师训让他们终生受益。所以,尽管他们中有的人在治学过程中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有争论、有修订、有批评,乃至有淘汰、有否定,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并未拔起,“中国情结”也并未动摇。因此,在研究实践中,一些优秀的研究者往往有种对本民族思想观念或方法论上反省的自觉,往往注意把中西文化中不同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加以取舍和融合。 儒家与老庄思想对西方学者的影响也相当显著:众所周知,德国的哲学革命完成于康德和黑格尔,但其思想渊源却可追溯到中国先秦的孔子学说,其间的沟通者和传播者即是莱布尼茨(Leibnitz)。由于传教士闵明向其介绍在中国的亲历,这位德国学者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697年,莱布尼茨出版一部关于中国的通信集《中国最近事情》。在这部著作的序言中,作者肯定儒家学说的道德力量,认为欧洲文明的特长是科学技术,中国文明的特长是道德实践。他力主这两种文明融合、互补:“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文明,即大陆两极端的二国,欧洲和远东海岸的中国,应集合在一起”。莱布尼茨作出如此号召的思想深层原因是出于他对基督教作用的怀疑。作者认为:基督教作为西方意识形态的精神支柱,他所提倡的禁欲、神启和末日审判等是与人性绝对背离的,因而无力维系西方社会的伦理秩序。而儒家所提倡的“仁爱”学说及其核心“敬”、“孝”是培植人性的种子,这比欧洲人小范围的亲教组织所起的移风易俗作用要大的多。莱布尼茨这一思想对当时的欧洲学者尤其是其弟子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中就有一位叫沃尔弗(Woif)的,他不但研究认可孔子学说,而且付诸实践,用德语在正统神学派占上风的哈尔大学讲授《中国的实践哲学》,因而受到普鲁士的驱逐。沃尔弗是德国启蒙思想的开创者,比起莱布尼茨,他的倾向性更为鲜明,即以儒家的理性反对基督的神性,以哲学反宗教。他认为“在孔子的著述中,虽有方法论上的缺点,缺乏欧洲人的雄辩之风,但是我们放远眼光,把握他们的一般法则,辨别出他们将地上政府建于天上政府的确实原则之上,那么便很容易发现他们是怎样具有最深的见解和最崇高的思想力了”。 盛行于二十世纪初的英美意象派,无论是创作理论还是写作技巧都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意象派代表人物庞德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就在庞德编辑出版第一部意象派诗歌集《意象派诗选》的1914年,庞德读到了法国汉学家波蒂埃翻译的《四书》英译本,便深深地为孔子思想所吸引,并专门写了一篇论文:《迫切需要孔子》。在为青年诗人所开的书目《读诗ABC》中,他认为荷马和孔子最重要。及至1945年,庞德在意大利被美军逮捕入狱时,随身只带了两本书:《孔子文集》和《汉语字典》。从二十世纪起,庞德翻译了许多儒家著作,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其中对庞德诗学理论影响最大的是《论语·子路》篇。他受该篇“正名说”的启发,充实了他的“维护说”诗学理论,正像美国诗人卡尔·夏皮洛所指出的那样:“《论语》第十三篇(即“子路”章,引者注)的几句话(即“必也正名乎”几句,引者注)为埃兹拉·庞德的史诗《诗章》提供了一个中心学说。这个学说强调精确的语言对于文明艺术的重要,所以诗人对于捍卫语言的精确性进而捍卫社会本身负有极大的责任”。 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对西方一些文学巨匠的影响也是相当显著的。德国伟大作家歌德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19世纪20年代,几乎与法国象征派诗人同时,德国伟大作家歌德的晚年诗歌和小说创作也同样受到诸子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晚年的歌德是个世界主义者。他认为:“国家文学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世界文学时期,凡人类俱要努力,完成这个大同” 。从此文学思想出发,歌德读过许多许多中国诗歌和小说,诸如《赵氏孤儿》、《老生儿》、《好逑传》、《玉娇梨》等,并将许多中国诗歌编译成《北美新咏》。他创作的诗歌《中德晨昏四季即景》中出现的物象和意境,很有儒家的中和之美;他创作的小说《威廉姆斯的漫游时代》提倡“孝”,提倡“三敬”(dreifache Erfuchte):敬天、父母师长;敬地;敬同类,更是来自儒家《孝经》和敬“天地君亲师”的触发。晚年的歌德对儒家思想的接受与他此时的政治态度和教育观念有关。从早年的狂飚突进主义者到婚后的怀疑论者,晚年的歌德成为一个保守主义者,他承认社会差别,渴望社会安定、人民守礼而反对使用暴力。要形成这种社会环境,就必须倡导儒家的教育方法,去启发人性、培养人的道德情操。所以在魏玛宫廷,歌德被称为”魏玛的孔子“(Konfuzius Weimar). 4、重视对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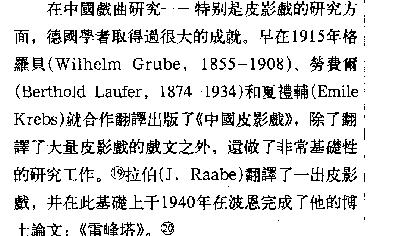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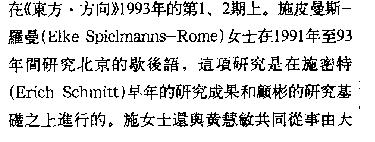 (一)创作素材 盛行于二十世纪初的英美意象派诗歌就借用了中国古典诗歌素材。其代表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为了摆脱当时弥漫在英美诗坛的“矫揉造作的维多利亚感伤诗风”,这位对汉语一窍不通的美国诗人,借助于汉学家费诺罗萨夫妇赠送给他的歌译稿,开始接触中国古典诗歌。面对精炼含蓄、意象鲜明的中国古典诗歌,异常兴奋的庞德找到了他“久已追寻的诗魂”,意象派的诗歌理论奇迹般地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找到了最佳例证。就像意象派研究者路易斯·L·玛兹所论述的那样:在那些诗歌里,庞德发现了合乎他诗的最深层需要的东西。这些诗歌充满活力,细节简明,包融着对自然赫人类的爱。最好不过的是,这些材料可以使庞德自由的用他成熟的技巧在他的手中再创造。庞德自己也指出读中国诗即可明白什么是意象派。1914年,庞德编辑出版了第一部意象派诗歌集《意象派诗选》,集中选了六首庞德自己的诗歌,其中有四首取材于中国古典诗歌:《仿屈原》,源自《九歌》中的《山鬼》;《刘彻》是对汉武帝《李夫人》的改写;《秋扇怨》出自班婕妤的《怨歌行》。1915年,庞德又从费诺罗萨夫妇赠送给他的150首中国古典诗歌译稿中选出18首,加以整理、润色和再创作,取名《神州集》(Cathay)。《神州集》的出版在美国诗坛引起了轰动,清新典雅、含蓄简明的中国诗歌受到普遍而热烈的赞扬,在美国诗坛掀起了“中国热”,随之出版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本达十多种,从而确立了意象派在西方诗坛的地位,《神州集》也被列为美国诗歌经典作品,“是庞德对文学最持久的贡献”。 (三)创作手法 英美意象派诗歌在写作技巧上也深受中国古典作家作品的影响。其代表人物庞德就试图模仿中国诗的结构形式,打破英文句法传统的固定形式,将具体的意象并置在一起,从而使意象更加突出。这在他于1913年发表的《巴黎地铁站上》表现的最为典型。这首被视为意象派压卷之作的短诗仅有两行: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 翻译成中文就是: 人群中 这些脸的 幢影 湿黑的 枝上的 花瓣 据作者自己说,他在巴黎某地铁站的车厢里看到一些美丽的面孔,一个个在他眼前闪现,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初,他为此写下三十行诗,后来经过反复思索,浓缩成这两行。在这两行诗中,庞德将他在瞬间所产生的审美视觉,“在空间上压缩,在时间上凝聚”,转变为他主观的审美形象。在句法上,庞德打破了传统的英文句法,将两个意象切割开来,“一个属于人的世界,一个属于自然界”,呈现出独立而具体的形态,则非常像中国古典诗歌“时空浓缩”和“时空交叠”等表现手法 ,使意象更加鲜明。 布莱希特对中国戏剧从理论到实践都有所借鉴。1935年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赴前苏联作巡回演出时举行了场座谈会,主题是“讨论并分析中国戏曲的技巧和象征手法”。中国古典戏剧中演员的既是表演者又是被表演者的双重身份(即“清唱”形式以及演员可以跳出角色,以第三者身份进行指点或独白——引者注),完全不同于欧洲传统的“亚里士多德移情法”,引起布氏的极大兴趣,并给他的戏剧改革——创立新型的“史诗剧”带来灵感。第二年,他即发表有关中国戏剧表演形式的专论:《中国演技的离间效果》,打印稿下还特别注明:“1935年春,梅兰芳一行人在莫斯科进行表演,文章即缘此而作”。在这篇论文中,布氏不无羡慕地写道:“重要的是,这位中国艺术家表演起来,似乎从未有第四面墙,而且其他三面在围绕着他。他表示他知道正在被人观看。这立即消除了欧洲舞台上一种典型的幻觉。观众再也不能幻想自己是被动的观察者,对实际发生的事情熟视无睹” 。布氏把此称为“离间效果”或“陌生化效果”。在他创立的“史诗剧”种借用了许多中国古代戏剧的表现手法,如单设一个故事讲述者,剧中人物自报家门;剧中地点变换由角色唱出来;剧中地点变换常常与时间推移相结合。这些是中国传统戏剧中固定招式,但对西方观众却是耳目一新。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