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些唐代诗人,虽然凭借“惊天地、泣鬼神”的不朽名句成为永远被后人景仰的贤达,但他们很多人生前却丝毫没有这样的满足感。“文章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在他们的生命中,最大的使命就是“学而优则仕”——当官。 现下很多的诗词解析者,用浮艳唯美的词藻,将唐代诗人们写得好似生活在澄清的水晶世界中,似乎他们整日里就是寻梅踏雪,拂云逐月,说不尽的诗酒年华,享不完的浮世清欢。其实,当年那些在文坛上熠熠生辉的唐代诗人们,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无一不为俗事所困扰。  要知道在唐代,没有一官半职的白衣平民,必须服兵役和徭役,就连张志和那样清高的隐士,也曾被县官捉去,塞上一把铁锹,逼他干活。而《石壕吏》中,捕吏再凶恶,也不能捉了杜甫抵数,正是因为杜甫大小是个朝廷命官。 “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这是愁病相煎的卢照邻孤独的写照。“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这是酒酣耳热时杜子美愤懑的倾吐。“青袍今已误儒生!”读了这么多书,还不如斗鸡儿、百夫长这等人活得惬意自在,这是无数唐代才子的共同感叹。 命运总是拥有我们看不见的手在翻云覆雨,造化弄人的事情古今皆然。而且,正如俗话所说的“情场得意,赌场失意”一般,文坛上的名气和官场上的际遇也像是一架跷跷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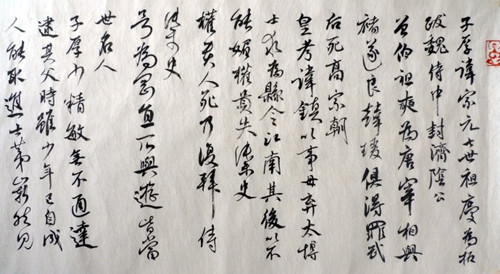 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中有这样一段话: “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至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意思是说,柳宗元如果官场得意,文章肯定就没有现在好了,到底是愿意官运亨通,文思衰退,还是希望像现在这样仕途潦倒,却才情四溢,这其中的成败利钝,老韩也很狡狯,自己不判定,要后人评说。 刻薄地想一下,历代文人虽然都把“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句话挂在嘴上,但心中对功名的热切才是最执着的。他们最后的墓碑上,首先镌刻的是自己的官职名,如白居易的墓志铭是:“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就连官职并不怎么风光的老杜,也是标名为“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什么官职也没有的唐伯虎,也题为“明唐解元之墓”。由此看来,名禄对于文人们,是何等的重要。 像孟浩然,包装得似乎是百分之百清高无比的隐逸之人,什么“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说得和神仙似的。然而一见洞庭湖边的张丞相,一大把年纪的孟老头禁不住一揖到底恳求道:“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给我个官做吧。李白说过:“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然而,一旦有了博取功名的机会,他还是嚷着“我辈岂是蓬蒿人”,宗氏夫人拉也拉不住,就“仰天大笑出门去”了。 其实,想想也并不奇怪,当时也没有“作家财富榜”,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诗赋只是文人们抒发胸臆的副产品而已。出将入相,捧着紫绶金印衣锦还乡,封妻荫子光耀门楣,这才是最高理想。所以,文人优雅风致的背后,其实也是一样的呛人烟火。 对此,一向直言的鲁迅先生说得最为辛辣透彻:“雅要有地位,也要钱,古今并不两样的,但古代的买雅,自然比今天要便宜;办法也并不两样,书要摆在书架上,或者抛几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摆在桌子上,但算盘却要收在抽屉里,或者最好是在肚子里。” 所以,既无地位也无钱的笔者,这本书里,也就不再谈什么“风花雪月”、“花鸟虫鱼”的“雅事”了,直接整一本最俗的东西,从抽屉里拿出算盘,开始八卦唐代才子的人脉和仕途。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