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语词典上的繁体字与简体字对照。CF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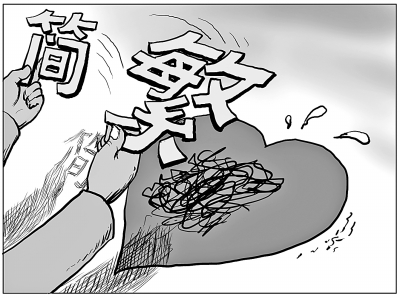 CFP “这是一次注定夭折的阅读历程。竖排的繁体文字、文言语句、布满正文的注释,中国人熟悉了上千年的行文到了我这一代已成了陌生的丛林。”学者许知远在他的文章中写道。 这种体验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因为我们都在使用通用规范汉字,也就是平常说的简体字。 但,繁体字真的离我们远去了吗? 又不是。在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中,在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中,在出版的书籍中我们还是会看到陌生而又熟识的字体。 前不久,《汉字简繁文本智能转换系统》在京发布。技术,可以让繁体字、简体字的转换不再是难事,精确度也一再提高,但关于繁体字与简体字的争论,却不曾停息。 “争论一直有,汉字也一直在简化” “汉字繁简问题的争论一直有,汉字也一直在简化。”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顾之川向记者讲述起汉字的简化史—— 从历史上看,汉字从甲骨文到楷书,总的发展趋势是趋向简单。清末就有人主张简化汉字。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教育部曾成立“国语统一促进会”,1932年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收录了部分被称为“破体”“小字”的宋元以来“通俗的简体字”。1935年1月,“国语统一促进会”第二十九次常务委员会召开,通过了与钱玄同的提案有关的“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如案名所示,它不是为新文字定策,而是提出将已在流通的简体字加以整理,以作为标准字。这些被称为“固有的比较实用的简体字”,一是现行的俗体字,二是宋元以后小说中的俗字,三是章草(草书的一种,笔画保存一些隶书的笔势),四是行书和草书,五是《说文解字》中笔画少的异体字,六是碑碣上的别字。 1936年1月,“简体字表”因受到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反对而“暂缓推行”。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50年代,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成为我国主要的语言文字政策,汉字简化终于成为现实,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有前代学者的研究与呼吁;二是当时我国有九成文盲,简化汉字有利于“扫盲”。 顾之川表示,我国推行简化汉字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在趋势就简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变回繁体。至于简体字的缺点,并非不能改正。如果考虑到更有利于在中小学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两岸文化交流等问题,有利于在海外推广中华文化,完全可以提倡“识繁写简”,即认识繁体字,使用简体字,让中小学生认识一些繁体字。 争论归争论。 不可忽略的现实是:在推行简化字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传统文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人们开始关注汉字,并思考:文字从何处起源?汉字的简化是如何发展的? “我们既不能一味追求简化而任意破坏理据,也不能因固守理据而无视汉字的繁难” “在简繁之争中,最好不要先有了感情色彩,而是要冷静思考,客观分析。”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军表示,简化是由古文字向今文字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方式。 他长期从事汉语言文字学教学与研究。“汉字是表意性质的文字,表意文字的根本特点就是其构形具有可解释性,也就是说,汉字的构形是有理据的。” 关于汉字的演化,他娓娓道来—— 从古文字到今文字,汉字一直坚持理据性的特点没有改变,但汉字理据的表现方式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早期古文字阶段,汉字的理据主要是靠物象或物象的组合来表现的。由于象形造字法满足不了实际需要,人们开始摸索着用两个或几个象形字进行组合造字。形声的出现,使得汉字不仅可以从意义的角度加以类聚,而且可以从声音的角度加以类聚。随着这种类聚关系的逐步调整和优化,到了小篆时期,汉字便形成了具有一定基础部件和有限构形模式的构形系统,这个时期汉字的理据已不再是个体字符的直观理据,而是通过部件的类化、义化和整个汉字系统的形声化,上升为更高层次的系统理据。 隶书是汉字形体简化幅度最大的阶段之一,它对篆书进行改造的目的也是为了“以趋约易”。从书写的角度来说,汉字的形体越简单,书写速度就越快;从理据的角度来说,汉字的形体越复杂,理据保留程度就越高。所以,书写和理据对形体的要求是相互矛盾的。汉字的发展就是要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去寻求简繁适度的造型。 在现在所说的繁体字中,有不少字的理据早就非常隐晦了。王立军举例:如“執”“願”按《说文》“六书”是形声字,它们的义符分别是“幸”“頁”,但现在还有几个人能了解“執”为什么从“幸”“願”为什么从“頁”呢?把“執”的义符改成“扌”、把“願”的义符改成“心”,意义不是更明确了吗?为什么非要那么绝对地说繁体字更能体现理据呢? “我们既不能一味追求简化而任意破坏理据,也不能因为固守那些已经十分隐晦的理据而无视汉字的繁难。”王立军强调,简化汉字推行了半个世纪,方便了几亿人的认字和写字,已经成为传播现代信息和国际交流的载体,在传统文化现代化方面,也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书写和认读简化汉字已经成为国内外绝大多数汉字使用者的习惯。 “繁简之争的背后是新时代的文化身份焦虑” 北京大学教授龚鹏程正是用繁体字来回答我们的提问。来北大之前,他曾是台湾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 “对正体字有亲切感,这是当然,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主要是认知上的,属于知识性感情,而非因自幼熟习的那种自然感情。”他所说的正体字就是繁体字。 “众所周知,简化字不只是个别字省了笔画而已,它还有大量同音替代、偏旁推类,一个字代替了好几个字,因此在认知上十分混乱。古代诗词歌赋文章典故、人名地名书名专有名词,到底原来是什么样,看简化字,更难判断,这让我头痛不已。”在龚鹏程的记忆中,无数文化名人、书法家,甚至中文系的教授也在繁体字与简体字的转换之间频频出错。比如:岳王庙写成嶽王庙、发展写成髮展、影后写成影後、新淦写成新干。“那不只是错了个把字,更是对一段话的文脉语境之误读,认知上大成问题。” “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厰空空,麵无麦,運无车,導无道,兒无首,飛单翼,湧无力,有雲无雨,開関无门,鄉里无郎……”这是一段在网上流传的文字,言外之意就是简体字隔断历史文化。 “传统六书造字法和笔顺,都很难讲。须知文字是跟思维合一的,混乱且简陋的文字体系,自然会使得思想简陋混乱,这亦是无疑的。”龚鹏程说,“歧见之趋同,有时也不是在道理上争辩就能解决的,还须有情感上的基础。例如朋友和家人,歧见虽大,毕竟容易商量,就是吵吵,也不伤和气,这就易于达成共识。否则越要据理而争,双方的裂痕就越大,越凑不到一块儿去。” 当年的他,带队来北京,赴语委会讨论文字问题,迄今亦二十余年了。“从剑拔弩张,火花四射,到现在和衷共济,其实也不容易。” “其实两岸文字学界交流合作多年,共识大于分歧。”他更为关注的是:眼光向前看,联合海内外,共同关心汉字与科技发展和运用的问题、汉字在世界拓展的教学问题等等。 “繁简之论,之所以日益引起大家的关注,背后的因素是新时代的文化身份焦虑。”龚鹏程回到争论问题本身,“现在,中国正在逐渐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阴影,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文字,是最重要的文化符号,当然格外引发关注。民情须知、民气可用,我们应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来探索一下:汉字与科技发展、汉字与英文西班牙文的国际竞争、汉字的推广等相关问题,不要继续斗嘴。” (本报记者 靳晓燕 本报通讯员 李达)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