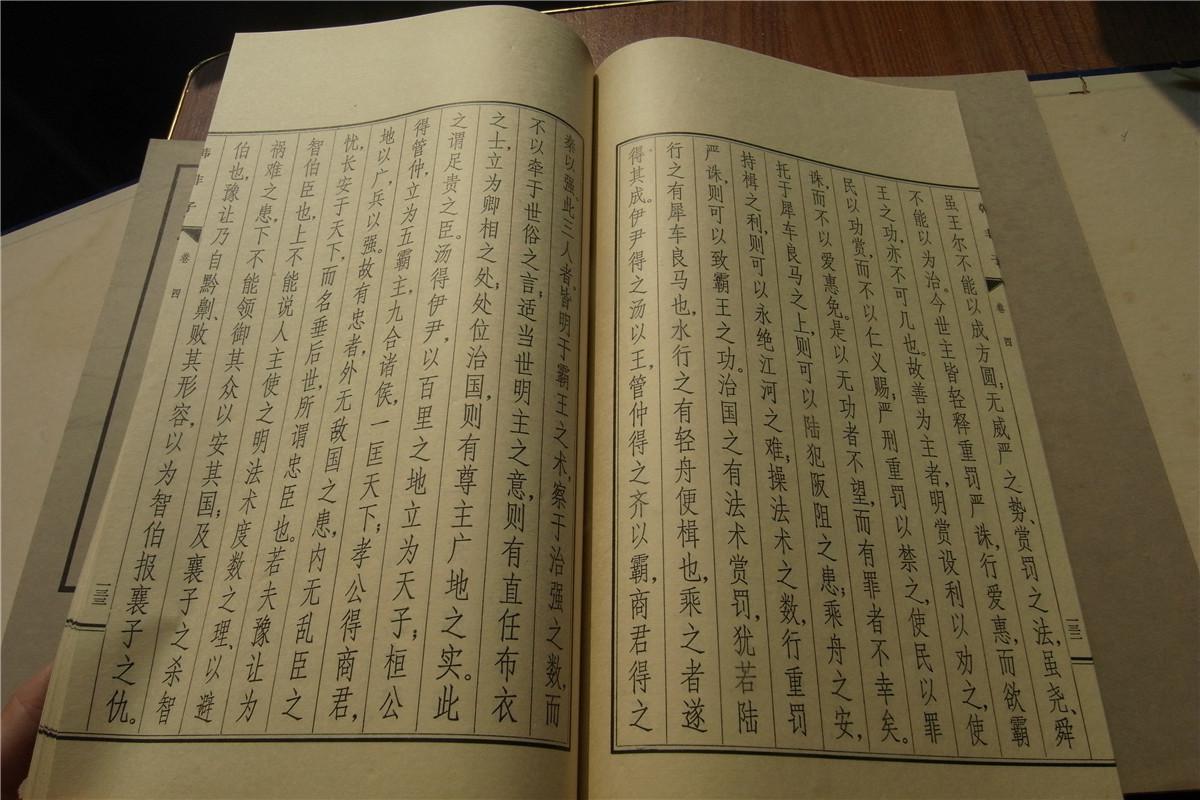 先秦诸子百家,法家是其中之一。文革时期“评法批儒”时流行一种说法,儒法之间长期对立,相互斗争,这是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如果说这个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的话,那么儒法相互补充恐怕也是事实。证据就是儒家的法家化,并且正是由于儒家有意识的法家化吸纳法家的思想,儒家才获得了两千多年帝制意识形态的地位。 跟其他各家比较起来,法家有点像现在搞企业管理的,他们擅长实际政治的操作。他们运用“实用理性”,为治理国家编制出一套合理的、高效的流程和方法,就算是智力平平、道德普通的人,也可以按部就班来管理国家。这些流程和方法就是所谓的“法术”,而精通这套“法术”的人士就被称之为法家。 法家的出现和崛起跟当时国家管理的复杂化有关系。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随着兼并战争的进行,国家的领土越来越大,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必不可少。如果说在从前小国寡民时代,谈谈哲学等等大道理就可以治国安邦,那么现在不行了:管理国家是一门具体的专业。 本杰明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一书中,说“法”之一字,大概有下面这些意思:首先是规矩,譬如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矩”相当于行为中的“法”;其次,“法”有规矩、技巧、方法的意思,或者专门指控制社会行为的政治技术,并引申出更复杂的含义:指塑造行为的“制度”或“体系”;其三,“法”的本义可能指刑法。本杰明指出:“法”这个词内蕴的强制性的涵义很可能随着法家的兴起,随着刑法以及所有的制度性模型都朝向强制的方向转变而得到了强化。 这里,“强制”是一个关键词。法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韩非子认为,民众喜欢混乱而不珍爱法律,但统治者最终总是能够向他们证明,他们的长期利益要靠以残酷的刑法律令为基础的体系给予最好的保障。本杰明说,韩非子从来都没有幻想过,他能很快说服多数人去热爱法律或者自愿地接受法律。所以,强制是必不可少的。 周代早期的统治者主要靠“礼”的精神——道德的凝聚力来维持社会的运转,靠以非强制性的纽带为基础的命令系统,即使是施行严酷的刑罚也要将其纳入到道德的系统当中。但是到周朝晚期非强制性的系统失去了作用。跟孔子同时代的人子产意识到,长远而言,世界最终得救要依靠恢复君子德性的政府,但就短期来看,残酷的刑法体系可能是最有效的。 本杰明指出法家是功利主义的,跟同样是功利主义的墨家不一样,法家的功利主义是行为主义的,也就是说,法家并不大关心人的内在逻辑。另外,墨家的功利主义强调“兼爱”中的个人利益,但法家的功利主义则把提高国家实力作为目标。法家的国家主义特色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无疑是最为鲜明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关注法家对后世源远流长的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国家主义者总是跟法家有相当程度的关联。 事实上,法家的第一个或者说最成功的实践家商鞅来到秦国,就是要把秦国打造成为中华世界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商鞅把每个人都跟国家的利益目标捆绑在一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不仅把人理解为仅仅只知道追逐自己利益的动物,而且还要把人塑造成为这样的动物。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不关心、不在乎自己的实际利益,这样的人就无法用他的赏罚制度来驱使。而当一个人完全是一个经济动物时,那么他的行为模式和行动后果就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因此,无论是商鞅还是韩非子,都对文明的副产品感到困惑,这些副产品包括:荣誉或者说虚荣、私人的理论、个人英雄主义……等等。 本杰明在阐述韩非子的思想体系时,发现了一个在法家的两大代表人物商鞅和申不害的理论中没有的东西,那就是源自慎到的神秘权威原则。本杰明说:“权威并不是靠强力建立起来的,毋宁说强制性的力量建立于对权威的接受上。”如果不能把权威内化,则整个体系就很容易崩溃。而权威内化主要靠神秘的外罩以及符号化的光环。 道家对韩非子的影响让他从道家那里找到神秘性的来源。韩非子写过《解老》和《喻老》。他正是从道的本体高度提炼出“君人南面术”,将这个南面术“藏之于胸”,就可以驾驭众人了。这里“藏之于胸”是要点,它的目的就是要使权威神秘化。 包括韩非子在内的法家思想帮助秦始皇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帝国。但是,秦帝国的短命也证明了法家的某些致命的缺陷,这就是他们对个人情感、价值和信念的无视是不能行之久远的。一个刘邦纠正了这一点,他顾及到人情世故的复杂性。而在这个地方,正是儒家的擅长。儒家的相对复杂的人性观反倒比法家冷冰冰的人性观来得更为“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刘邦留下来的遗产是一种复杂化的、柔化的秦始皇,他比秦始皇来得高明多了。 历来,一种流行的说法都是“儒道互补”。事实上,对于中国的士人来说是儒道互补,儒是进路,道是后门。所谓“达者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至于对于中国的官人,尤其是中国的统治者,则是儒法互补,儒是修饰、是谋略、是人情世故,是人性之常,而法是统治术,是核心价值观。我们知道儒家在中国的影响极为深远,我们不知道法家的影响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王绍培)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