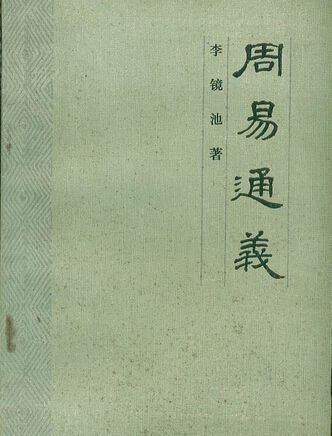 易学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周易》今译今注,百花齐放。 近十余年来,《周易》今译、今注,不断翻新。李镜池《周易通义》(1981)、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1984)、高亨《周易古经今注》(1984年重版)是第一批注译著作,为易学研究提供了急需读物。1987年,同时有两部新注本出版:宋祚胤《周易注释与考辨》、沙少海《易卦浅释》。此后,随着“周易热”的发展,陆续有新注译本问世,黄寿棋、张善文的《周易译注》(1989)、金景芳的《周易全解》(1989)、周振甫的《周易译注》(1991)、唐明邦主编《周易评注》(1996)。这批注译本,其注释的深度和精度都大有进步,反映了《周易》研究的新水平。刘大钧、林忠军的《周易古经白话解》(1989)、《周易传文白话解》(1993),徐于宏《周易全译》(1991)、邓球柏《白话易经》(1993),陈德达、杨树帆的《周易入门》(1999),为广大易学爱好者提供了入门读本。对易学普及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新涌现了各种《周易》经传注译本,有的长于文字考订,有的长于训诂诠释,有的长于理论评析,创立了《周易》注释的新体例,对《周易》的思想文化内涵,作出多学科、多角度的诠释。 二、人文易空前繁荣。 《周易》的哲学思想,自“五四”以来,就深受重视。冯友兰在致第一次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的《代祝辞》中,称周易哲学为富有辩证思维的“字宙代数学”。“周易热”中首先突出的是《周易》哲学思想。张立文《周易思想研究》(1980)、吕绍纲《周易阅微》(1991),张祥平《易与人类思维》(1992),罗炽主编的《易文化传统与民族思维方式》(1994)、张吉良《周易哲学和古代社会思想》(1996)、唐明邦《当代易学与时代精神》(1999),都着力于剖析《周易》哲学,特别看重其以象数思维为特征的民族思维方式。李廉《周易的思维与逻辑》(1994)着力探讨《周易》理论体系的逻辑问题。人们不再满足于对《周易》哲学作唯心或唯物的性质判定,而深入探讨《周易》所启示的民族思维方法及其特色,探讨其自然哲学、历史哲学和逻辑思维的固有特征。《周易》美学思想受到重视,刘纲纪《周易美学》(1992)、王振复《周易的美学智慧》(1997),刘纲纪、范明华《易学与美学》(1997),对《周易》美学思想的掘发,填补了易学中的空白。 关于《周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学者们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多侧面的审视和分析。刘大钧《周易概论》(1986),宋柞胤《周易新论》(1982),王振复《巫术:周易的文化智慧》(1990),郭树森、张吉良主编《大道之源——周易与中国文化》(1993),罗炽主编《中华易文化传统导论》(1995),翟廷*《周易与华夏文明》(1995),周山《周易文化论》(1994),胡道静、戚文主编《周易十日谈》(1992),从不同角度阐述《周易》的文化内涵及其对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贡献。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1995),发掘了周易卦爻辞中蕴涵的古代诗歌。程振清、何成正《太极思维与现代管理》(1993),周豹荣《周易与现代经济科学》(1989),段长山主编(周易与现代管理科学)(1991),余敦康主编《易学与管理》(1997),对《周易》的经世思想、管理思想作了全面阐述,突显了《周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借鉴意义。 《周易》和易学研究对现代化建设的现实价值,成为新时期易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安阳、庐山、西安等地多次学术研讨会上,对此进行了深入深讨。刘大钧主编《大易集成》(1991)、《大易集要》(1994),《大易集述》(1998),段长山主编《周易与现代化》第一辑(1992)、第二辑(1993),《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1994),朱伯主编《易学基础教程》(1993)唐明邦主编《周易纵横录》(1986),郑万耕、赵建功《周易与现代文化》(1999),张吉良《周易通演》(1999),王炎升《周易经世学新论》(1999),都论述了《周易》和历代易学思想,对新时期人们营建进步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有着古为今用的启迪作用,对提高民族文化思想素质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姜国柱《周易与兵法》(1997),为易学与现代化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出土后,经过专家学者多年精心考证诠释,1984年在《文物》上公开发表六十四卦经文,同时发表张政*《帛书六十四卦跋》和于豪亮《帛书周易》(1984),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帛书周易》研究,成为热潮。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1987)、张立文《帛书周易注释》(1992),韩仲民《帛易略说》(1997),是第一批学术研究成果。事隔10年之后,帛书周易传文开始发表,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1993)、第六辑(1995),朱伯昆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1995),公开发表《帛书易传释文》,共有《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六篇。从此张岱年、饶宗颐、严灵峰、朱伯*、张政*、李学勤、余敦康、张立文、陈鼓应、廖名春等纷纷发表论文,掀起《帛书周易》研究新高潮。邢文《帛书周易研究》(1997)是第一部学术专著,对《帛书周易》的内容、结构、成书年代,卦序特点、学术渊源等问题都作了论述。《帛书周易》的出土,是20世纪易学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在海内外的学术影响将与日俱增。 20世纪80年代。1980年《考古学报》上发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1984年为武汉召开的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提供论文《易辨—一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首次提出“数字卦”问题,主张八卦符号沿于上古占篮记录的数字符号。徐锡台、韩仲民等办发表论文阐述此观点。为八卦起源问题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 三、科学易巽军突起 《周易》同现代自然科学的联系,不少当代科学家作了深入探讨,力图从易学思维中找到现代科学方法的微妙启示。董光壁《易图的数学结构》(1987)、李树菁主编《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1990)、丘亮辉主编《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1993)、徐道一《周易科学观》(1992)、顾明《周易象数图说)(1994),焦蔚芳《周易宇宙代数学》(1995)、董光壁《易学与科技》(1997)、韩增禄《易学与建筑》(1997)、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1989)、商桂《易索》(1998)、何世强《易学与数学》(1999),罗翊重《易经象数学概论》(1999)等著作。剖析了《周易》及其象数模式同现代数学、物理、化学、分子生物学、天文、地震等方面的关系,着重论述了《周易》的太极思维,阴阳观念。对称法则,互补原理等对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的启迪作用,显示了《周易》这一“宇宙代数学”的科学价值。与此同时,江国梁《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1990),邬恩溥《周易——中国古代的世界图式》(1988),黄寿棋、张善文选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四集(1990),刘振修《周易与中国古代数学》(1993)等著作,着重论述了《周易》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的积极影响。 《周易》同中国传统医学、养生学关系尤为密切。召开过多次关于周易与中医学学术研讨会。邹学嘉、邹成永《中国医易学》(1987)、杨力《周易与中医学》(1989)、李浚川、萧汉明主编《医易会通精义》(1991)、刘杰、袁峻《中国八卦医学》(1995)、黄自元《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1989)、刘长林《易学与养生》(1997)等著作,对医易会通思想、易学与养生法则作了全面而透彻的论述。 科学易的巽军突起,支持者、参与者大有人在,持批评态度者亦不乏其人。董光壁《易学科学史纲》(1993)对科学易与易科学作了正确介定,论述了易学与中国科学的三次高峰,分析了易科学的困境,提出了易学的科学再造等新思路。 四、象数易复苏、易学史开卷。 80年代以前,象数易一直处于冷落局面。除尚秉和对易象有专门研究外,不少易学家表明他们的研究不及象数。义理易得到弘扬,象数易无人问津。80年代以后,情况逐步改观,研究周易象数者,除一些科学家外,已有学者专门从事。钱世明《易象通说》(1989)、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集(1994)、第二集(1996)、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第一集(1996)等,对象数易的历史与现状作了探讨,象数易同科学易的关系作了分析与展望。易图亦随之受到特别重视。欧阳红《易图新辨》(1996)、李申《易学与易图》(1997)对易国作了深入研究,正确评述易图在易学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 在人文易、科学易、象数易大为兴盛的学术氛围里,易学史开始受到重视,并取得可喜成就。朱伯*《易学哲学史》一至四卷(1986-1989),对易学哲学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剖析,为易学史研究开辟道路,作出典范。廖名春等编著的《周易研究史》(1991),郑万耕《易学源流》(1997),亦对易学发展历程作了简明论述。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1991)、王兴业《三坟易探微》(1998),对易学前史的评析,予人以深刻启迪。 易学史上著名人物的研究,亦已初步开展。萧汉明《船山易学研究》(1987)、梁绍辉《周敦颐评传》(1994)、卢央《京房评传》(1998)、唐明邦《邵雍评传》(1999),是对古代著名易学家进行个案研究的第一批成果,为今后易学名家个案研究,开辟了广阔领域,积累了初步经验。 五、《周易》辞书蔚为大观。 中国易学史上,80年代以前,没有一部《周易》辞典。随着“周易热”的高涨,《周易》爱好者日益增多,人们普遍要求编撰可靠的《周易》辞典,以应初学及研究之急需。多种《周易》辞书应运而生。几部辞典几乎同时问世。萧元主编《周易大辞典》、吕绍纲主编《周易辞典》、张其成主编《易学大辞典》、张善文编《周易辞典》,均于1992年出版。任华主编、卢叔度审定《周易大辞典》(1993)、朱伯主编《易学知识通览》(1993)、张其成主编《易经应用大百科》(1994),为易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易学知识,填补了辞书和易学史上的一大空白。 种种迹象表明,近代之前“《易》学”及与《易经》的思想阐释和实际应用而形成的各类学术和实用知识,就已经传入西方世界,但这种传播基本属于文化影响史的范畴。外来的文化影响,对于学术思想的发展当然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不过还不能看作是严格的学术交流。西方人直到16世纪以后才对《易经》展开直接而系统的研究,最初的一批研究者就是来华传教的欧洲耶稣会士。这一研究始于对《易经》原典和中国当时某些具有权威性的注释本的深入的研读,结果就形成一批由耶稣会士直接用汉文字写作的《易》著。这确实是中西文化史上一种令人惊异的现象。与此同时,为了使西方人更好地理解中国思想及其古老的传统,一些耶稣会士开始翻译《易经》,法国耶稣会金尼阁的拉丁文译本《易经》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易经》西语译本,已佚失。随后耶稣会士中宋君荣、雷孝思、顾赛芬都曾从事《易经》的翻译,而以雷孝思的拉丁文译本影响最大。将这一经典完整地介绍给西方世界,从此开始了《易经》传入西方和西方《易经》研究的近代时期。 16至19世纪期间,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士留下的易学著述,其数量相当可观。除了拉丁文翻译和研究著作,17世纪耶稣会士还留下了一批直接用汉语写的《易》著,这批著作基本完好地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和巴黎图书馆。他们在许多宗教、哲学和科学著作中,也不时对《易》及与易学相关的问题作出阐述。 传教士白晋于1698年自法国返回中国,此后半生皆致力于对中国典籍中的象征作深入的探讨。白晋在其一系列著作诸如《古今敬天鉴》(DeCultuCelestiSinarumVeterumetModernorum)、《易经大意》(IdeaGeneralisDoctrinaelibriYeKin)和一系列通信中表述了他的形象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可以大致归纳为两个方面: 白晋认为《易经》及中国古史以“先知预言”方式表达了基督教教义。他在1700年11月8日致莱布尼茨的信中不无得意地宣称:“今年我曾经应用同样的方法继续对中国古籍进行研究,幸而有些新的发现。……几乎完整的一套圣教体系,即在其中……。极大的神秘,如圣子的降生,救世主的身世与受死,以及他宣教的圣工(对世人)所起的重大作用,这类似预言性的表现,在珍贵的古代中国哲学巨著中,亦隐约有迹可寻。当你看到这无非是联篇累牍的虚无与象征的词语,或者真理新定律的谶语时,你的惊奇程度当不在我下。” 白晋试图通过揭示“数学中的神秘”的方式来证明《易经》为以色列祖先所遗留下来的圣典。他说:“《易经》数字的神秘,似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埃及犹太哲学中的神秘数学相呼应,此秘密是由第一个祖先给其后代的,虽然后来消失了,但必然是来自造物主之神秘启示。”由此他得出结论“在八卦中可以看出创世及三位一体之奥秘”。 傅圣泽作为白晋的合作者,对形象理论亦加以发挥。他于1711年来到北京,协助白晋编写《易经稿》等易著。傅圣泽未到北京之前,就已加入形象学派。傅圣泽通过《易经》等典籍来了解中国古史。他认为,在中国文字中亦含有很多的象征意义,其来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及其基本的基督教义。他将《周易》之“周”解释为宇宙,可衍申为洪水后保存于诺厄方舟中最早世界记录及普世教训的宝库;而将“儒”解释为“人”、“需”两字合成,需原意为期待;又解释《易》之需卦,谓需乃从天而降之云彩,此乃符合《圣经》所载神乘着云彩从天降下;孔丘之“丘”字则被解释为“亚当厄娃的象征”。厄娃,今译夏娃。 刘应,字声闻。他于1687年同白晋一起抵华。先后在北京、南京、广州、陕西等地传教。刘应精通汉语,涉猎了许多中国古籍,对《易经》作了深入的研究。他与康熙太子相善,据说有一次皇太子翻开《书经》的一章,刘应即取读之,并解释其义,毫不费力。太子奇甚,连声说“大懂”,并赠给题上赞语的绢本《书经》。刘应是最早对《易经》进行注释的耶稣会士之一,他对《易经》所作的注释被附在宋君荣《书经译本》之后,并被辑入《东方圣经》(livresSacresdeI’orient)。在对《易经》的理解上,刘应在许多地方与白晋的观点相异。由于在“礼仪”问题上,他与同会其他教士意见相反,支持了教皇的主张,他的著作也由此而得到罗马教廷的赏识。刘应对卦作了不同于白晋的解释,认为卦象符号是伏羲创造的,过去许多书之所以对卦的符号作不同解释,是因为时代和作者不同。 16世纪后期到18世纪末二百余年间,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士留下的《易》著及与易学相关的著作,其数量相当可观,并就与易学相关的宗教、哲学和科学问题展开阐述。从易学史的观点看,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的易说,无疑是中国本土易学演进的一个相当独特的组成部分,构成该时期多元化易学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流派。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