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注解:《道德经》的第十六章,呈现为思想进程的三段论结构,即第一,进入清虚专注的思想状态;第二,洞观万物生成的常理;第三,将这个常理应用于社会。这个三段论的思想进程,也可以表述为思而后明体,明体而后达用。达用是最终目的,但必须从“思”开始。 如何“思”?“虚极”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如何达到?“静笃”属于那种情形,如何守住?因为这些问题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瞑目打坐,所以对于这一章的解读,历来都带些东方宗教神秘体验的色彩,似乎只有修行过,具有类似宗教体验——尤其是道教的存思、内丹等修行方术及其体验的人,才能够找到理解这一章的恰当角度。 然而,宗教体验终究是个体性的,很难确认某种体验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所以即使在教团内部,这样的体验也只能是三两个人私下印证,以至有“法不传六耳”的习惯说法。而在当代,希望读懂《道德经》的人,远远多于具有相同宗教体验的人,所以如何由“密”而“显”,通过描述其体验和思想逻辑,讲清楚这一章的三段论内涵,是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 当然,描述宗教体验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佛陀拈花,迦叶微笑,可以意会,不可言传,所以讲起来很神秘。道家的体验也不例外,也很神秘,如《庄子·大宗师》里的寓言,子杞、子舆等四人相与语,“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像佛陀、迦叶一样,笑得心领神会,而外人不明就里。不过,道家的体验曾有前代高人描述过,我们只需借鉴,不必另起炉灶,否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能真的会遇到麻烦。 《庄子·齐物论》描述了一位道家修行者南郭子綦,在几案旁静坐,神情委顿,仰天而嘘,像是灵魂已出窍的样子。弟子颜成子游站在座前侍候,很诧异,不禁要询问,“今天怎么啦?修行者可以让自己形同槁木、心若死灰吗?今天这个静坐的人,不是过去那个静坐的人”。这一问,煞是恰到好处,让颜成子游道出了修行的秘密——“今者吾丧我”。正是在“吾丧我”的状态中,颜成子游闻听到众窍怒号、咸其自取的“天籁”。 那么“吾丧我”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学界有一种解释,“吾”是真我,超越了假我。这种解释或许也有个醉翁之意在里面,试图借助自然本我的理念,提升道德意识的自觉,针砭社会角色的虚伪。但道德自觉的“我”,还是有意识成见的,这样的道德意识抒发为外在的神态,即使不必像卫道士那样对谁都正义凛然,起码也不至于蔫然委顿。所以从《齐物论》的上下文意来看,所谓“吾丧我”,或许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精神专注,忘却了日常都会有的经验、观念、意识、意志等等,只剩下一团清虚的灵明知觉,浑然不同昔日之“我”,不知身在何处。《道德经》所说的“虚极”、“静笃”,大概也属于同类的状态。 进而言之,“吾丧我”的状态之所以出现,必定是由于精神高度专注,并非由于昏昧,因为昏昧中是没有这样一个“吾”的。既然精神专注,就必有其对象。颜成子游所专注的对象,是大风刮过,众窍怒号。《道德经》在虚极静笃的状态下,也同样有一个专注的对象,即“万物并作”。由此看来,在这个精神专注的过程中,虽然看不见任何一物的“殊相”,却能够洞观事物的“共相”,如众窍、万物之类。 按照常情来分析,人在闭明塞聪的状态下之所以能够洞观事物的共相,必然经过了长期的观察、思索,否则以空观空,必定空无所得。据此理解道家的洞观,似乎可以类比于逻辑学的归纳法,若就其撇开形式逻辑的程序模式而言,也可以说是归纳法的升级版。这样从认识发生的角度来还原道家的体验,或许能让理解变得容易些。即道家在洞观中可以归纳事物的共相,再由共相推阐出常理。这个常理,在道家看来是一切自然秩序的根本。《庄子·齐物论》称之为“天籁”,即一种风吹出千万种调,每种调都是由特定窍穴自身决定的。从窍穴到风吹声调各别,是“咸其自取”的,这个内在的自我规定性,被西晋时的郭象概括为“独化”。《道德经》称之为“归根复命”,即万物在自然大化中虽呈现为万象,但每种象的结果都是对其种根的复归,其呈现是由各自的“根”决定的。显然,“归根复命”与“独化”作为万物常理,在哲学思想的基本立场上是一致的,这也就是道家之所谓“自然”不同于上帝创世纪的关节点。 毋庸讳言,严格按照逻辑规则来衡量,道家的洞观不能算合格的归纳,因为从“众窍”到“万物”,“类”的概念都是抽象的,内涵和外延都是模糊的。尤其是《道德经》所说的“万物”,究竟是总宇宙为一大类?还是指不同的物种各自为类?从经文本身很难看出端倪。也许,在《道德经》的思想逻辑中,强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的重心,不在于对物品进行分类,而在于阐明一个常理的两个方面,即第一,从运动大秩序的角度看,万物是周而复始的;第二,从实体存在形态的角度看,物品是各自为种根的。大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又遵循“反者道之动”的必然轨迹,像是爆炸与塌缩相循环的宇宙,小到某植物的一粒种子,都在这个常理的概括之中。只是由于植物种子的比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更直观些,所以《道德经》就采用这个比喻,而从“归根复命”说起。 所谓“归根复命”,简单说来就是果实还原为种子。从植物的一个生长周期来看,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开花结果,确实很纷繁,很“芸芸”,但结果总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就果实与种子无所变化而言,是静止的;就果实必然复归种子、遵循其内在规定性而言,是注定要“复命”的;就物种不变、果实各自还原的普遍性而言,“复命”呈现为常态,是合乎常理的。 那么,弄明白这个常理,洞悉纷繁复杂的万物万象,其实遵循着周而复始和种根不变两条秩序原则,对于建构社会共同体,究竟有什么样的启示意义呢?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大,很敏感,因为它浮现出将自然法则应用于社会的表象,难免让人紧张。在现代的语境中,所谓将自然法则应用于社会,首先让人联想到的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用进废退等等,野性暴戾的画面,挥之不去。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里,“自然”是万物各自有其然而皆可成就的天道,将自然法则应用于社会,概言之就是“推天道以明人事”,推阐天道是一个“知常曰明”的思想过程,明人事是引导社会向“万物并作”的境界升华,绝不仅仅是学着动物去猎食。在理解自然常理对于社会建构的启示意义时,古今语境的天壤之别,是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 而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里来看,社会共同体建构之所以经常出问题,症结并不在于人类的文明意志不够强烈,更不在于社会集结时缺乏排他性的选择意愿和能力,而在于缺乏真正宽容的精神,尤其是当所谓文明将宽容与排他性对峙起来,将宽容当做诊治排他性之病的药物时,宽容就沦落为以排他性为前提的工具理性,降格为缓解排他性紧张的临时措施,丧失自立为价值理性的基础。换言之,如果没有现实的排他性冲突,就不会想到宽容的本然合理性。而《道德经》所要朗现的,正是宽容的本然合理性。 根据《道德经》的思想逻辑,真正宽容的精神,来源于对万物常态常理的洞观。因为包括一切社会文明形态在内的世间万物,都遵循着周而复始、种根不变的秩序原则,这表明万物都有其自然而然的生成轨迹,有其本然合理的生成形态,尊重其轨迹,容纳其形态,是常理的应然要求,是统领社会之王者的本分,既非恩惠,更不是妥协,所以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操持什么样的理由,为王者都不能按自己的主观意志割不齐以为齐,不能奢求社会的所有成员都符合自己所设想的模式。唯其如此,真正的宽容精神才可能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中展现出来,毋须自我标榜,毋须娇柔做作。 宽容让社会舒展,而舒展让社会共同体更稳固,这个道理,在《道德经》第二十七章里被表述为“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一个社会,如果不是由民众的认同缔结起来的,反而依靠外力捆缚在一起,那么迟早有一天,内在的张力会挣断绳索,导致社会土崩瓦解。要避免这样的危机,就必须释放出宽容的精神,维护社会的舒展和稳固。而舒展和稳固,又是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必要条件,正如历史已反复证明的,在一个逼仄或动乱的社会里,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可言。所以《道德经》以类似演绎的方式推阐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如果不能从容地推行公平、公正,就只能成为某种特殊利益的维护者、代言人,又如何能成为天下的王?如何撑得起王道、天道的旗帜? 在本章的最后,我们想强调一点,《道德经》的这一思想,既是道家的,同时也是儒家的。如《尚书·洪范》说,“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其有极,归其有极”。没有偏斜,不私立一家之好恶,也就是宽容;不结党营私,不以党同伐异的手段撕裂社会,从而形成天下为公的格局,社会整体才可能舒展得开;不谋求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手腕操控社会,任由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我协调,被社会认可的公正原则自然就朗现出来。这样的社会共同体建构,符合王道、天道之极。显然,《尚书》的这段文字与《道德经》的第十六章,可以相互参证、相互诠释。而将儒道两家合起来看,可以说宽容、舒展、公正的“王道”,代表了中华政治文明的主流传统。 附《诗译道德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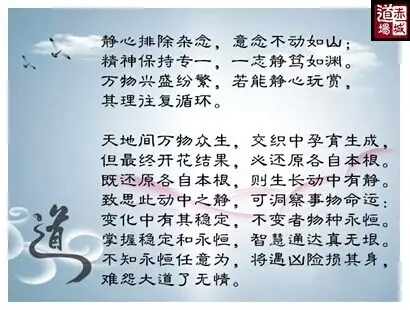 (图文转载自赤城宾馆微信)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