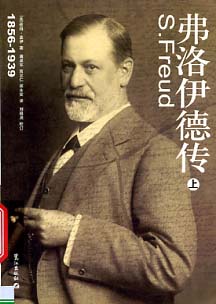 理论的突破常常生长于对以往理论大家思想的再思考之中。在西方喜剧理论史上,弗洛伊德的笑论思想富有重大理论启发价值,备受重视。我国学术界对弗洛伊德笑论的研究却一直处于译介和初级评价水平上,更不要说进行系统的、创造性的美学转换工作了。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则弗洛伊德笑论深层心理依据的难以验证性和理论解释上科学与玄学成份的冲突性,使人们对其评价的难度加大;二是旧理论框架的限制和新理论框架的模糊造成评价制高点和切入点选择难度的增高。 现在我国喜剧理论研究总体上处于相对尴尬的状态。一方面,建立在“四范畴”基础上的狭义喜剧理论研究范式面对纷繁多变的当代喜剧形态变体难以给出有效、规范的理论解释;另一方面,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喜剧元理论框架,致使传统“四范畴”本身的区分标准也常常纠葛不清,喜剧理论正成为一个无力的理论。构建一个更具逻辑力度、更具包容性和解释性的喜剧元理论框架成为当务之急。也正是在这种思维诉求下,弗洛伊德笑论逻辑建构方式的意义才彰显出来。 一、弗洛伊德笑论研究的历史状况 弗洛伊德笑论首次引进中国,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品文运动中。林语堂在《论幽默》一文中首次提到了《郁剔与潜意识之关系》一书,而真正对弗洛伊德作出全面、深度评介的,是朱光潜,他在《变态心理学流派》一书中,介绍了弗洛伊德在《诙谐和隐意识的关系》中对灰谐(wit)心理的有趣探讨,但未作评价;而在《文艺心理学》的《笑与喜剧》一章中,则重点讨论了弗氏的“心力节省说”,认为:一则弗氏的“心力节省说”是历史上“精力过剩说”、“自由说”、“游戏说”以及“鄙夷说”的合并和发展,特别是弗氏的“移除压抑”(removal pleasure)就是“自由说”所说的由紧张而迟缓,不同之处只是这种紧张在弗氏学说里起于意识和潜意识的相持,这是弗氏对“自由说”所加入的新成份。但这一说法是否成立,以弗氏隐意识全部能否成立为转移。二则弗氏的“心力节省”概念“颇有毛病”:语言的“节省”并不尽能引起快感,如“凡物下坠”不能引人发笑。换句话说,弗洛伊德并没有替诙谐时的“节省”寻出一个特点来。[1] 从60年代开始,陈瘦竹先生结合中国传统戏剧理论,对中外戏剧中的喜剧进行研究,形成了我国狭义喜剧理论研究范式。该范式的特点是重主客观的统一,重对喜剧艺术作品的分析。陈先生认为:(一)弗氏所谓的“敌意的笑话”完全缺乏社会内容,只注意满足本能的冲动,审美境界不高;弗氏将幽默态度的形成和发展,只从主体心理加以解释,完全脱离社会实践,这不仅非常玄妙,而且不能充分说明其特征。(二)可借鉴之处是不仅将笑话、喜剧性和幽默严格加以区分,而且关于幽默的性质和特征的论断极为精当。(三)心力消耗的节省和感情消耗的节省尚不能成为定论。[2] 80年代,西方现代派作品大量引入,带来诸多异于常态的喜剧形态,这导致我国喜剧理论研究又一个高峰期的到来。这一时期最大的收获是初步形成了我国广义的喜剧理论研究范式。该范式的特点是,注重对笑的心理机制和形式特征做心理学、语言学、逻辑学的综合研究。弗洛伊德笑论著作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被完整译介过来,如:1987年,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其中包括《论幽默》一文);198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弗洛伊德的《机智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一书。译者在《译者序》中指出了书中贯穿着“形而下的还原法,即通过对笑话结构的还原来把握机智的无意识根源”的特点,只是没有作进一步的生发。 由此,弗洛伊德笑论思想是在狭义喜剧理论研究范式和广义喜剧理论研究范式两种视野下被认知的:在狭义喜剧理论研究范式内,“审美境界”成为一把重要的尺子,弗氏满足本能冲动的“敌意笑话”倍受诟病,而幽默理论受到赞赏;在广义喜剧理论研究范式内,弗氏的“心力节省”和“形而下还原法”作为他的重要理论突破受到高度重视。但是两者都没有发现弗洛伊德笑论逻辑建构方式的重大价值。 二、弗洛伊德笑论概念的美学归位 讨论弗洛伊德笑论的逻辑建构方式,有必要先对他所使用的相关喜剧概念进行一下美学归位。这是因为,弗洛伊德的笑论是其对梦的机制和无意识研究的副产品,其初衷是为了他无意识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丰富,而且弗洛伊德笑论在使用机智、喜剧性等美学概念时,与一般意义上的美学概念多少有些出入,常常赋予自己的解释个性。 关于机智。 在弗洛伊德那里,“机智”实际上承担着双重职能:首先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喜剧性亚范畴而存在,其特征是具有强烈而显明的二元结构性(观念的对比、荒谬的意义、混乱与明了、第二级启蒙),用弗洛伊德自己的话说,就是具有“古怪”属性的急智类令人发笑的笑话形式。他自己也明确表达了概念的这种使用意向,即“矫正以往一些美学家和心理学家的错误研究倾向:总是把机智作为喜剧性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其次,正是由于机智具有喜剧性的典型结构特征,所以它在书中实际上承担了作为弗氏对喜剧性心理动力规律的分析载体的功能,在这种意义上,机智等同于本文使用的核心概念——喜剧性。弗洛伊德声言,机智技巧“和机智本质的关系比它和喜剧性的关系更加密切”。[3](P96)但是,弗洛伊德对机智的这后一种职能认识并不清楚。 弗洛伊德认为,“在机智形成过程中,一个思想流中断了片刻,接着它又突然以一条妙语的形式从无意识中冒了出来”,[3](P148)“当先前占据某些心理渠道的所有心理能量已经无用武之地,以致于使它可以自由地发泄出来时,人们才会笑”。[3](P128)而且他断定,“在形成并维持精神抑制的过程中需要一种‘心理消耗’”,[3](P101)此机智乐趣产生于抑制消耗的节省。 弗洛伊德特别重视机智的结构技巧问题,认为机智技巧的辅助性功能造成机智效果的不确定性。“具有更大理论意义的是一系列辅助性机智技巧,它们显然是想把听众的注意力从机智过程中引开去,以便于使后者可以自动地向前发展。”“通过使用这些辅助技巧,我们就可以正确地设想正是由于掌握了这种注意力,我们才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并重新使用自由投注。”[3](P132) 关于喜剧性。 弗洛伊德对喜剧性概念的使用在全书中呈现为一种游离状态。从全书看,有四分之三的篇幅是讨论机智问题,只在最后讨论了“机智和各种形式的喜剧性”。乍看,喜剧性似乎是和机智并列的一个二分概念,但到后来,幽默又被拉入进来,喜剧性最终成为一个与机智、幽默并列的三分概念。 弗洛伊德认为喜剧性有两种表现形态:一、儿童笑话所表现出来的“幼稚”。二、出现在人们的动作、形态、行动和个体特征上滑稽可笑性以及采用使人们滑稽可笑手段向喜剧情境转变的模仿、伪装、暴露、漫画、歪曲等。这两种形态的心理机制有所类似,即消耗的落差接近于最大值:“遇到幼稚时,我们通常能作出的那种抑制消耗突然变得无处应用了,而且它还通过笑而发泄出来。由于这种抑制的排除是直接的,而不是一种刺激作用的,所以就不需要把注意力悬置起来了。我们的行为象机智中的听众一样,无须作出任何努力,就能得到抑制的节省。”[3](P161)遇到滑稽时,“那个在其身体活动中付出太多的消耗而在精神活动中又付出太少的消耗对我们来说就显得滑稽可笑了。”[3](P175)所以说,“喜剧性”的乐趣产生于思想消耗的节省。 除了“思想消耗的节省”这个维度外,弗洛伊德还给我们指出了另一个区分维度:“可以把喜剧性解释成凡是与成年人不适应的一切事物都具有喜剧性”,[3](P207)“我们似乎很想把喜剧性的那种理想的特点转入幼儿的觉醒过程之中,而且我们似乎很想把喜剧性理解为重新得到‘失去了的幼儿之笑’的过程,这样人们可能会说:‘每当我在另一个人身上发现孩子气时,我都要因他和我自己之间的消耗差别而发笑。’”[3](P204)但他对这一点并不十分肯定。 很显然,弗洛伊德的喜剧性主要是指美学中的滑稽,但又不完全是指滑稽,还包括“幼稚”这一他自己命名的美学形态。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