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瞿林东  江湄  孙卫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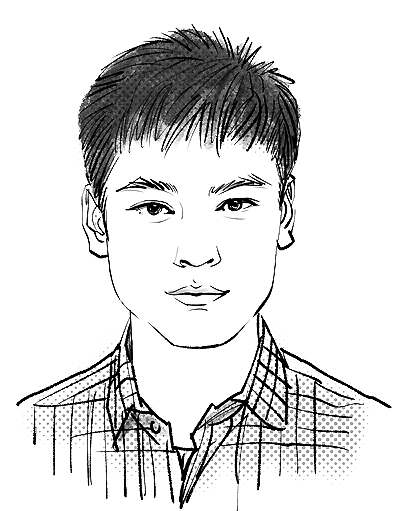 刘开军 【史学话题】 主 持 人:户华为 朱露川 特邀嘉宾: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瞿林东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江 湄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孙卫国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刘开军 编者按 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历程中,自先秦时人强调“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到司马迁撰《史记》强调“通古今之变”,再到南朝刘勰自觉提出“居今识古,其载籍乎”的命题……“居今识古”在人们进行社会实践和历史研究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一个核心观念。为了促进学界和大众对中国古代史学观念的了解,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中更好地发挥“居今识古”的现实功用为社会服务,我们特别邀请四位史学史与史学理论方面的专家,从概念提出、思想传统、具体践行以及现实关怀等方面,对中国古代史学这一核心观念和重要传统进行解读。 1、“居今识古,其载籍乎”:一个十分重要的史学命题 主持人:距今约1500年前,南朝梁人刘勰撰成《文心雕龙·史传》篇,其开篇提出“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这是中国史学中一个关于古今关系的重要命题。在刘勰以前,中国史学上已有这一思想认识,其思想渊源可上溯至先秦时期的史官制度和修史传统。从概念上看,中国古代“居今识古”这一命题是如何逐步形成的? 瞿林东:“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中国古代关于“居今识古”的认识,应当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逐步获得的。“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易·大畜》)这一古训大意是说:人们应当多识记前代之言、往贤之行,便多闻多见,以蓄积己德。这个“德”,既包括道德,也包括见识。道德重在做人,见识重在做事。而“前代之言,往贤之行”,正是后人引为借鉴的。在文字被发明出来以前,这里说的“言”与“行”有些当是人们在实践中口耳相传得到的,如《诗经》中的《雅》《颂》作为史诗,一方面有艺术夸张的地方,同时也包含着文明时代以前的传说,其中《生民》《公刘》等,读来都十分亲切生动。 当文字被发明出来以后,有了历史记载和历史著作,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所谓“前代之言,往贤之行”被记载下来,成为后人“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重要途径。周人指出,殷朝是“有册有典”(《尚书·多士》)的朝代,而孔子是整理古文献的大学者(《论语·八佾》)。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周王朝和各诸侯国都有史官记述国史,如《春秋》《梼杌》《乘》等名目的国史以及相关记载的出现,为人们认识“前言往行”提供了广阔和深远的时空条件。太史公司马迁说得好:“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话的意思是说,生活在现在的人们,要学习、记住过去的事情,是为了以其作为一面镜子,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 刘开军:古圣先贤素来重视推行教化,中国史学尤其讲究以史为鉴,这都需要一个前提,即“识古”。《尚书·酒诰》中,周公郑重地提出要以殷商的灭亡作为周的统治之鉴。倘若周公“居今”而不“识古”,连殷商的历史都不清楚,就谈不上总结经验教训。再看《尚书·无逸》篇中,周公举殷王中宗、高宗的勤政论说统治之术,核心是君王不可耽于享受、忘记小民的痛苦,同样发人深省。所以,“居今识古”这个命题的重要性不是我们讲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的。 主持人: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意思是说“载籍”是“居今识古”的重要途径。那么,“载籍”是如何发挥其“识古”之用的?同时,出于史官或史家之笔的“载籍”能否客观地反映历史面貌,成为“居今”能否“识古”的关键所在,人们在“居今识古”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能动作用? 瞿林东:处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通过当时所能接触到的“载籍”即史书(史乘)而“识古”,并从所识之“古”中获得知识、思想、智慧和修身之道,从而积累、提升自己的“德”,为社会所用。这就是“居今识古,其载籍乎”的价值所在。前面讲到司马迁所言“志古之道”的“志”,本意是记住的意思,我引申为学习、记住,联系刘勰说的“其载籍乎”,即学习并记住“载籍”中的记述,人们才能“识古”。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载籍”的数量、种类不断增加,内容越来越丰富,人们从“载籍”中获得的知识、教养、经验、智慧也不断提升。 春秋时期楚大夫申叔时认为,以不同性质的“载籍”教导楚王的继承人,可以使其在不同的方面得到提升。他指出:“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以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国语·楚语上》)这里可以看出“载籍”门类之多和内容的广泛。唐初史家撰修《隋书·经籍志》,将文献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仅史部书就有十三类,人们通过“载籍”而所识之“古”的范围更加扩大了。明清之际,王夫之论《资治通鉴》之“通”的内涵,强调:“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穹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读通鉴论·叙论四》)这种从思想上、理论上对“古”的概括,更加使人认识到“识古”的重要性。 进入近代,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从历史观和人生观的角度阐释了通过“载籍”而“识古”的重要意义。李大钊指出:“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史学要论》)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史通·史官建置》),这是“载籍”不绝于世的保证,也成就了中华文明记载连续不断的伟大事业。人在“居今识古”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不可忽略,当“载籍”从史官、史家手中传到社会不同人群和社会生活层面时,史注家、史学批评家、历史考证学者等,都在发挥各自的专长,推动“载籍”中的“古”焕发出自身的生命力,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活动和历史进程。当然,“载籍”中记述的“古”,不能与实际存在过的“古”同等看待。一是实际存在过的“古”不可能完全写入“载籍”,二是“载籍”中记述的“古”也可能因记述者的曲笔而改变了实际存在的“古”。就前者而言,表明人们对“古”的认识不可能是绝对的,但人们可以从记述者所记述的“古”中获得自己所关注的内容;就后者而言,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史学上有坚持直书、揭露曲笔的传统,从而使人们更容易获得有益的知识、思想和智慧。 刘开军:的确,“载籍”作为“居今识古”的媒介,其重要作用在于消除“今”和“古”之间的时间鸿沟。因为史书囊括今古,可以沟通历史与现实。历史学是人们认识过去的桥梁,能够有效地预防和治疗一个国家患上可怕的“失忆症”。不重视历史学,也就无法认识历史,更谈不上文明的传承和发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居今识古”这个命题已超越了学术研究的范畴,而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意义。当代史学工作者的任务是梳理、继承这个传统,将之用于指导我们的史学活动,并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尊重历史、学习历史、传承历史的风尚。 从认识主体来看,“居今识古”是人的一种自觉的思想追求和知识需求。在古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都渴望了解过去,表现出“识古”的浓厚兴趣。东汉末年,汉献帝特别希望知晓西汉的历史,但他没有充裕的时间阅读《汉书》,于是命荀悦删改《汉书》,写成一部更加简略的西汉史读本《汉纪》,这也是较早的帝王历史读物。至宋代,勾栏瓦肆、街头巷尾之中,有职业的“说话人”专门讲秦汉、说三国,听众多为普通民众。他们听史,除了娱乐,当然也有“识古”的目的。明清时期,历史知识进一步走向社会大众。近年来,社会上又兴起了一股“历史热”,其中虽存在良莠不齐的问题,但这也是今人努力“识古”的体现。 江湄:中国史家很早就认识到,对历史的记录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整理和编纂,更是人们对历史的一种深刻认识和再现,其中包含着基于现实需要的历史认识者的“思想”。战国时期孟子论孔子作《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相对于“事”和“文”,“义”才是史之所以为史的根本要素。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出,要以作者的“别识心裁”作为“撰述”的根本要素,唯“撰述”足以称“史学”,而“记注”不足以称之,这是章学诚对中国史学重“义”传统的精彩总结。中国史学的经典之作大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现实感和政治性,都有鲜明的经世倾向和丰富的思想含量,这与中国史学的重“义”传统是密切相关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面对中国的历史文献,不能仅仅将之当作“史料”来使用,而是必须深刻地意识到,其中包含着一个时代对于自身历史地位的想象和认识,包含着对于时代问题的诊断和思考以及对于历史前途的判断和希望。这些“思想”“观念”和“心态”构成了那个时代更深层次的历史真相,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是必要且首要的。联系到20世纪后半叶,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虽然使历史学的客观性遭遇到一种强烈的危机,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它也使历史学家对书写历史的意图更加自觉,“历史是如何被记忆和书写的”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一个前沿问题。人们普遍认识到,自己首先面对的,不是“历史”,而是对于历史的“记忆”和“书写”,这些“记忆”和“书写”中承载的情感、意图、心态和思想观念,同样是“历史”。史学理论的进展使客观历史本体与历史记载的区别不再绝对且更有细究的必要和意义,同时更加强调和突出了历史认识过程中一个基本的事实:人们只能借助于对历史的记忆和书写,才能对历史有所认知。这正应了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中的那句话:“居今识古,其载籍乎!” 2、“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一个优良的史学传统 主持人:在刘勰明确提出“居今识古,其载籍乎”之后,后代学者从不同角度将其作为一个重要命题展开论述,遂使其逐渐成为中国古人史学观的共识。请问,“居今识古”这一思想传统是如何贯穿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中的? 瞿林东:“居今识古”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古代史学重视史官,重视修史、著史,重视史学社会功用的优良传统紧密相连。汉、唐史家对此有明确的论述。东汉班彪意在续司马迁《太史公书》(《史记》),“作后传数十篇”,其所撰长篇“略论”,从“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论到司马迁著《史记》,是较早论述这一优秀传统的文字。文中有这样几句话:“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后汉书·班彪传》)对中国史学史的论述,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字,值得进一步关注和阐发。 唐初史家撰《隋书·经籍志》,其总序称:“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这是从广泛的意义上,强调史官对于“经籍”产生、发展的重大作用。其史部大序则进一步表明史官所应达到的标准及其职责的重要性;其十三类小序则概述了各个门类史书的源流与存佚,展现出史学发展的宏阔画卷。半个世纪后,刘知几撰成《史通》一书,其《六家》《二体》《史官建置》《古今正史》《杂述》等篇,具体地描述了这一优良传统的发展轨迹,把中国史学中的史学自觉精神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这是清代思想家、诗人龚自珍的名言(《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箸议第九》)。这充分说明,悠久的中国史学传统,以及许许多多优秀的史家、史籍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之深、之大。当今的中国史学者,身居改革开放的中国,面对多元的世界文化,要以广阔的视野和虚怀若谷的胸襟,吸收外国同行有益的思想、方法和成果,用以提高自己、丰富自己;同时,也要真诚地、清醒地对待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创造出反映时代要求而又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史学成果。 刘开军:刘勰的贡献在于,他把先秦以来的这些思想提炼为一句文字简短、指向明了、意蕴丰富的话,推动了这一传统的最终形成和发展。刘勰之后,“居今识古”成为一句名言,不断被后人引述论说。而关于“居今识古”的相似表述更屡见于史册之中。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说修史旨在“多识前古”。无独有偶,唐太宗也从自己的读史经历中由衷地感慨:“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修晋书诏》)当然,在司马迁之前,孔子不仅具有明确的借文献认识历史的自觉意识,而且还是一位“居今识古”的实践者。史载孔子“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即从古代典籍中求得学问。同时,他又整理《诗经》,作《春秋》,为后人“识古”提供了可能。 淳化三年(992年),徐铉撰写《邠州定平县传灯禅院记》,提出:“居今识古者存乎书”,从他紧接着所写的“金匮石室之宏规,名山京师之故事,此而不务,何以为能”来看,他说的“存乎书”也就是历史典籍,这和“居今识古,其载籍乎”的思想和表述都如出一辙。在另一篇文章中,徐铉还直接劝诫士子们要“居今识古”(《泗州重修文宣王庙记》)。要之,“居今识古,其载籍乎”的传统,导源于先秦,发展于两汉,定型于南北朝,成熟于唐代,历宋元明清而代有传承,其流不绝,一直滋养着中国传统史学不断成长。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和传统,中国史学才能够生生不息,史学家无论是在盛世的喧闹还是在衰世的没落中,都以理性的态度、深沉的忧患和恢宏的器局书写历史,让后人得以认识历史,总结历史。 江湄:“居今识古”体现了中国史学的自觉精神。中华文明很早就具有历史意识的自觉,明白“居今识古,其载籍乎”的道理,从而形成了发达连贯的历史记载和编纂的传统,在晚清今古文之争中,章太炎明确提出,孔子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孔氏,古良史也。辅以丘明而次《春秋》。”(《訄书·订孔》)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在于开创了史学传统,使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意识有了基础和根据:“夫发金匮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丘明始……令迁、固得持续其迹,迄于今兹,则耳孙小子,耿耿不能忘先代。”而印度、波斯与中国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但是由于没有记载和编纂历史的传统,以致近代遭到帝国主义侵略后,无法追述自身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无法建立自身历史的连续性:“而故记不传,无以褒大前哲,然后发愤于宝书,哀思于国命矣。”(《国故论衡·原经》)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面对中国现代国家及其民族意识的创建,对这一点尤其有深刻的体会和认识。 孙卫国:事实上,不独中国古人有“居今识古”的思想传统,古希腊历史学家也曾有相近的表述。赫卡泰厄斯就曾强调“只有我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我才把它记载下来”;被誉为“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的波里比阿特别指出:“真实之于历史,正如双目之于人身。如果挖去某人的双目,这个人就终身残废了;同样,如果从历史中挖去了真实,那么所剩下的岂不都是无稽之谈?”所以“求真”作为古希腊历史学的一个基本底色,也由此开启了西方史学的求真传统,正因为真实的历史被记载,因而“居今识古”才成为可能。 3、“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一件具有现实意义的史学工作 主持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这是中国古代史家对史学社会功能所作的深刻总结,通过居今识古,人们可以沟通古今,鉴往思来,这反映出中国古代史学在求真的同时,讲求经世致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曾指出:“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这正是基于中国古人的认识传统,对史学在当代的发展提出的期许。请大家谈谈,“居今识古”在当下如何发挥其现实功用? 瞿林东:史学在社会历史中诞生、成长,它需要良史、求真和著作的积累;同时,史学也要回到社会现实中发挥作用,使人们获得经验、智慧和对历史前途的辨别能力。这是“彰往察来”的古训所要求的,也是“居今识古”的现实诉求。 中国古代史学不仅追求求真,也讲求致用。自先秦以下,中国史学历来有经世致用的传统,由史家本人宣称,其所著史书,正是为施政作参考,至晚当始于《通典》著者杜佑。《通典》自序明言:“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这位“以富国安人(民)之术为己任”的封疆大吏这一治史宗旨,不仅受到当世人的称颂,而且深得后人赞许,乾隆《重刻〈通典〉序》称赞《通典》“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另一历史巨著的作者司马光在其《进书表》中说,《资治通鉴》撰述的重点,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从而“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从撰述重点到撰述目的,《资治通鉴》经世致用的撰述宗旨十分明确。宋神宗称它有资于治道,故赐名“资治通鉴”,是非常恰当的。清人龚自珍撰有《尊史》一文。意谓史家、史学之所以受到尊重,是因为“能入”“能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入乎道”,这比“能入”“能出”,又提升了一步。可见,史学之于“道”,是多么重要。这些都表明,从求真走向致用,是一项具有重要实际意义的史学工作。 刘开军:“居今识古”是一项古老的传统,同时又有现实意义。“识古”从来都不仅是史学家的事情,而且是一项关涉社会全体的事业。以我的浅见,“居今识古,其载籍乎”的现实意义,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古”与“今”是相对的,由“居今”而“识古”,再由“识古”而进一步“识今”,循环递进、不断深化。人们常说到“古往今来”这个成语。什么意思呢?“古”成了往,“今”也就随之而来了。在认识论上,古和今不能分开。对此,东汉时王充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论衡·谢短》)清代乾嘉学者王鸣盛把“知今不知古”称为“俗儒之陋”(《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二“唐以前音学诸书”条)。1918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耐人寻味的文章,题目叫作《今》,里面有一句话:“‘现在’就是所有‘过去’流入的世界。”按照我粗浅的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今”是“古”的延续,“今”里面有很多“古”的基因。可见,不“识古”也就不能真正识今。 第二,“居今识古”思想不断循环深化,使得人们有可能少走弯路,不走歪路。历史上,知识精英们从未放弃过“居今识古”的传统和使命,他们勤于撰述,不断探寻“识古”之道。为了认识历代成败兴衰之迹,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为了掌握古代的典章制度、运用其中蕴含的治国思想,有“九通”之作。为了总结古代的文学、艺术成就,历代正史中设立了《艺文志》《经籍志》《儒林传》《文苑传》等。为了寻找抵御外侮的良策,王韬著《法国志略》,黄遵宪作《日本国志》。今人研读这些典籍,不仅认识了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也能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上理解今天的政治、文化、学术特色,更好地融入到当下如火如荼的时代洪流之中。 第三,“识古”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变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更加直观地彰显了“居今识古”的现实意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寻求出路,回答中国该往何处去的问题,学术界开展了一场有关“识古”的大讨论,这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新生命派、动力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家出现了激烈的交锋。最终,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种影响直至今日。 第四,“居今识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来说,亦有其特殊价值。若着眼于国情而“识古”,就将“识古”落到了实处,可以看清楚古代历史文化认同的轨迹,这对于民族融合和国家一统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辽兴宗在位时组织翻译了《贞观政要》和《旧五代史》。金代的科举考试内容中,就包括“十七史”。瞿林东先生主编的五卷本《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也是这样一部“居今识古”的教科书。生活在今天的人们,熟知过去两千多年间各民族间的融合,尤其是思想观念上的认同,对于处理好民族问题和边疆问题均有重大意义。 总之,政治家“识古”,可以周知历代治乱之迹及其利害,更好地治国安邦;思想家“识古”,可以为思想的锤炼提供资料和素材,提出并解答思想史上的一些命题;文学家“识古”,可以从文学的盛衰流传中体察人世百态,创作出兼有历史底蕴和时代气息的佳作。当代的史学工作者毫无疑问肩负着引导人们认识历史的重要使命,牢记司马迁所说的“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和顾炎武的名作——《文须有益于天下》,既有志于写古,也不忘论今。 孙卫国:“居今识古”,最重要的就是要切合时宜,为当下社会现实服务。诚如李大钊所言:“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史学要论》)这也就是“居今识古”的用意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 历史学是门开放的学问,常做常新,所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思潮对它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但它之所以能屹立不倒、不断壮大的根本,则是始终坚持对真实历史的探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史家也认为史家关注历史,实际与当下密不可分。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言:“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相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历史学家因为现实问题,回眸历史,从中找寻着所研究的问题。另一位英国著名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在一首著名的诗中写道:“无人能令/时光倒流,草原欣荣,百卉奔放,但我们不悲伤,情愿在/残余的时光/再寻回/以往的力量。”从这首诗中,我们或许也可以感受到“居今识古”的韵味,也为当今史学工作者的坚守,带来一些诗情画意。 人物素描:郭红松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