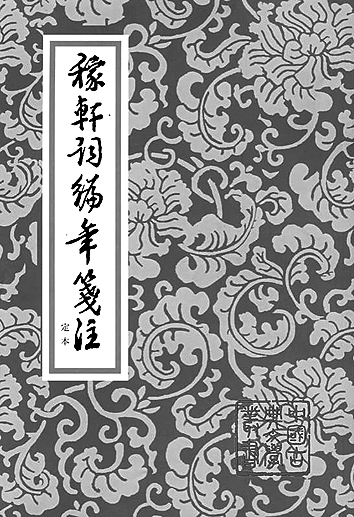  1952年邓广铭先生在北京东厂胡同一号书斋内。 资料图片  邓广铭先生与师生们在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 资料图片  邓广铭先生部分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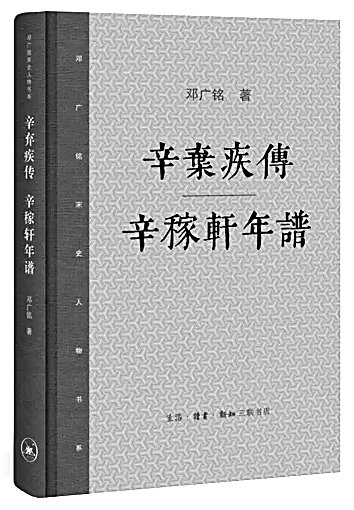 邓广铭先生部分著作  邓广铭先生部分著作 我的老师漆侠先生是邓广铭先生招收的第一位研究生。1987年,我考入河北大学,有幸成为漆侠师的入室弟子。作为邓广铭先生的再传弟子,相对而言,在有幸近距离接触邓先生并且与之有过深入交谈的学生中,次数最多者,大致非我莫属。在邓广铭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回想起多次拜见先生的场景,历历在目,感慨万千。 1、 “望之俨然” 20世纪80年代前期,我在兰州读硕士的方向是宋史,很早就读过邓广铭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宋辽金》《岳飞传》和《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等著作,以及那几年邓先生发表在报刊上的多篇论文。1984年我到四川、河南、杭州、上海和北京等地访学,拜见了当时能见到的众多宋史名家,如王曾瑜、朱瑞熙、徐规、梁太济、胡昭曦、张秉仁和周宝珠等,唯独未见邓先生和漆侠师。此前风闻两位先生太严厉,令人生畏,不易接近,所以尽管有一次在北京逗留了十多天,而且在北大校园转过一天,但踟蹰再三仍未能到邓先生府上登门拜访。直到1987年,我考入河北大学宋史研究室师从漆侠先生,才得以见到邓先生。 很感念漆侠师对我的偏爱。1987年9月19日早晨,我刚下火车到河北大学报到,行李还没打开就被宋史研究室的人拉着上了去石家庄的火车,说已被漆侠师任命为第四届中国宋史研究会年会秘书组组长。第二天全天报到,下午3点多,漆侠师招呼我跟他一块去接邓先生。当时我内心激动万分,也很感谢漆侠师在第一时间把我引荐给邓先生。 记得那天到了石家庄简陋的车站,火车晚点,漆侠师不住地看手表,不时地向出站口张望。约4点钟,漆侠师说:“老师来了。”我循声望去,看到张希清老师搀着邓先生的手臂缓缓走出站门,漆侠师赶紧走上前向邓先生请安,然后把我介绍给他,说是今年新考进来的博士生。只记得当时邓先生向我微微点了一下头。第一次见邓先生印象极深刻,我觉得心目中的大学者就应该是像邓先生那样有伟岸身躯和儒雅风度的人,亦即孔夫子所说的“望之俨然”。 第二次近距离接触邓先生是在河北大学。1989年5月下旬,国家教委主持新中国成立40周年教学成果奖评选活动,漆侠师的教学成果《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治史、执教、育人》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国家教委组织专家对漆侠师的教学成果进行鉴定,出席鉴定会的专家有邓广铭、张政烺、何兹全、胡如雷、王曾瑜和藤大春等史学界和教育界著名学者,邓先生担任组长。那时我正读博士研究生二年级,有幸全程参与接待工作。鉴定会上,邓先生一边听诸位专家发言,一边不时翻阅漆侠师《宋代经济史》的场景,至今还总是浮现在眼前。 第三次与邓广铭先生近距离接触是在1991年。我在《跟随漆侠师学宋史》中曾简要提及拜见过程:“那是在1991年8月,国际宋史研讨会召开前,漆侠师带我到北大朗润园邓先生的府上向邓先生汇报会议议程。那天进门落座后,漆侠师的恭敬和拘谨都在一声带有浓重山东乡音的紧张问候语‘老师,您好,我是来给您汇报国际宋史研讨会的’中传递出来,漆侠师一直前倾着身子面向邓先生,椅子只坐了前半截,汇报完一个问题,就问邓先生一句‘老师,这样行不行’,汇报了四五个问题,也连续追问了四五次。汇报完,邓先生说留下来吃饭,漆侠师说不麻烦老师了,已经在外面有准备了,然后说要到邓先生家对面的宿白先生家坐坐就匆忙告辞了。一到宿白先生家,漆侠师就恢复了常态,谈笑自若。”会议于8月9—14日在北京盛唐饭店召开,漆侠师又让我担任大会的秘书组组长。会议期间,因会务问题我多次向邓先生请教,聆听邓先生的指示。邓先生的开幕词对当时国内宋史研究在国际宋史学界的地位、现状及其未来发展方向有精辟的概括,直接影响了其后对20世纪宋史研究学术史的总结。 2、“即之也温” 虽然邓先生不再出席宋史年会,但我还是有幸拜见过先生几次。此后我每次去北京,漆侠师都给我钱,让我买茶叶或水果代他看望邓先生,我也因此有机会近距离聆听邓先生讲述他的研究计划和对国内外宋史研究现状的评论。也许是隔代亲的缘故,在北京大学朗润园10公寓206室的邓先生府上,每次与邓先生交谈30分钟左右,邓先生很健谈,每次谈话其实我几乎插不上嘴,或回忆,或评论,或谈笑,总是娓娓道来,根本不像是年逾八旬的老人。尽管我知道先生年事已高不能太劳累,但每次都不忍打断谈兴正浓的他,每次都是邓小南老师出来让邓先生服药或添水,我才能借机离开。 现在想起跟邓先生交谈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邓先生谈修改《王安石传》的计划。记忆最深的是邓先生说除了要补足一些史实外,最重要的是与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研究范式告别,他甚至挥手做了一个一刀两断的手势。我在《评邓广铭、漆侠五十年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中对此作过专门的论述,“似表明他不再坚持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中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政权之间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的观点”。 二是邓先生谈当时宋史研究的现状。他希望宋史研究能真正摆脱那种为意识形态注解、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非正常状态,而回归实证史学的优良传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宋史学界悄然向实证学风转向,实证性的专题研究已占据宋史研究的主导地位,热衷辨析史事,究心典章制度,蔚然成风,这不能不与邓先生的大力提倡密切相关。 三是邓先生回答我的请益。那时我拜见邓先生,由于入道时间短,内心不免惶恐,不知该问些什么问题,生怕问题太浅显,见笑于他,就径直问先生最近在做哪些方面的研究,邓先生说正在整理和编辑自己的论文选集,说是应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由此大致谈到自己为什么选宋辽金史为研究对象,然后又说到王安石在宋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后来在1995年初,我买到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拜读自序时才知道邓先生讲的内容我在之前已亲耳听到一小部分,为此感到莫大的荣幸。我也问过邓先生他的哪些成果最能代表自己的学术,邓先生说在他人看来是《稼轩词编年笺注》和《宋史职官志考正》,但是他自己更看重四部人物传记:《王安石传》《岳飞传》《辛弃疾传》《陈亮传》。而且,邓先生说在有生之年重新修改了《王安石传》之后,希望再修订《岳飞传》等其他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三次交谈中最令人感慨的是,每次邓先生都说他有很多想要研究的问题,有很多要整理的文献,就是感觉时间不够用,担心来不及做,很焦急。每次听到邓先生如此说,我的心灵都受到深深的震撼,由此也鞭策自己珍惜时光,希望能在有限的生命里多做一些事。后来得知邓先生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时日,几次吟及辛弃疾祭奠朱熹的文字:“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那是“他晚年所以坚持重写《王安石传》及修改其他著作,为不能全身心从事于此而终日焦躁,都是为其学术名誉的传世久远负责。这种对著述的‘高标准、严要求’,对于他而言,并非是单纯的学术‘精益求精’,而是以中国文化中此种源远流长的‘不朽’的终极关怀为基础的”。 我为漆侠师递送给邓先生的《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是漆侠师为完成邓先生的嘱托而写,这篇论文即是后来同名著作的大纲,因而漆侠师完稿后第一时间就是请邓先生过目。我递送漆侠师大作之后大概一个月,邓先生就将论文打印稿寄给漆侠师,邓先生在信中为漆侠师写成的大纲感到高兴,并给予很大的鼓励和很高的评价,同时在漆侠师的打印稿上像批改学生作业那样有抹改,有批语,还有校正。望着满篇的“修改”真迹,邓先生待学生那种不论年岁和知名度的率性真情跃然纸上。1994年4月在成都举行的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五届年会开幕式上,作为邓先生之后的第二任会长,漆侠师所作的报告即是经邓先生修改润色的论文,同年漆侠师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支持。其后一直到邓先生遽归道山之前,漆侠师都在努力完成老师的嘱托和遗愿。 1997年夏秋之际和11月下旬,漆侠师带领郭东旭、姜锡东和我一同赴京,两次探望住在北京友谊医院的邓先生,当时邓小南老师接待了我们,并告诉漆侠师有关邓先生的病情。第一次时邓先生很清醒,思路一如往常敏捷,表示他会很快回家的,自己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让漆侠师及我们不用为他担心。待到11月再去探望时,邓先生仍然清醒,但话语已不多,漆侠师坐在邓先生病床前,我们三人则站在一旁,默默待了片刻,然后就匆匆告别,我们随漆侠师上前与邓先生一一握手,邓先生跟我握手后向我点了一下头。走出病房,邓小南老师对我说邓先生当时已不能多说话,向你点头表示他认出你了。我很激动邓老先生还能记得我,那是最后一次见到邓先生。 1998年刚过了元旦不久,就传来邓先生遽归道山的噩耗。漆侠师后来带着郭东旭、姜锡东和我参加了在八宝山举办的邓先生的告别追悼活动,以及邓先生逝世一周年时在北大举行的悼念追思活动。 3、“听其言也厉” 在纪念刘浦江教授的文章《畏友浦江》末尾,我提到,我爱读浦江撰写介绍和纪念邓广铭先生的系列文章,前后他一共写了13篇,如《大师的风姿——邓广铭先生与他的宋史研究》《不仅是为了纪念》《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独断之学 考索之功——关于邓广铭先生》《“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邓广铭教授的宋史研究》《一代宗师——邓广铭先生的学术风范与学术品格》等。我是邓先生的再传弟子,当然希望对老师的老师有详尽的了解,这是我喜欢读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在读的过程中,除了感知浦江知恩必报的情怀外,浦江通过描述邓先生的学术经历、治学方法乃至心路历程展现出的那种敬畏学术的精神,引起我的强烈共鸣。 我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上的大学,在国内同时期宋史研究者中算起步较晚者。大学时代比较喜欢世界史,中国古代史的成绩是所学课程中分数最低的。大学毕业后考研究生选择宋史方向主要是为毕业后找工作,当时并不喜欢宋史,直到1987年考入河北大学跟随漆侠师,我才真正走上研究宋史的学术道路。也是跟随漆侠师学习宋史,才使我对20世纪宋史学科奠基人邓广铭先生的学术有了全新和深刻的认识。可以说,我在宋代经济史的学习上是刻意模仿漆侠师,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得到答辩委员“颇有师风”的评语,应该说很符合我的实际情况。 在文献和宋史史料学习上,我更多的是模仿邓先生。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漆侠师不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平素的聊天交谈中,都会讲述当年邓先生的读书方法及学识,譬如漆侠师给我们讲述宋代基本文献时就列举邓先生开列的七部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宋史》《文献通考》,同时强调阅读《宋元学案》的重要性,鼓励我们多读邓先生的书,常对我们说“你的老师不如我的老师”,所以受漆侠师影响,自然会有意识拜读邓先生的论著;第二,我读本科时,甘肃师大历史系主任金宝祥先生在入学典礼上致辞时强调读名著重要性的话语一直激励着我。他说,学习宋史,邓先生是最大的名家,当然要选择读邓先生写的名著。事实上,通过读邓先生和漆侠师的著作及其治史经验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对于起步晚而初学宋史的我来说,自然是有很大益处的。 在邓先生诸多著作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之所以这么说,原因是邓先生的成名作、代表作学界早有很高的定论,那已是心向往之的不朽,但是相对于初入宋史之门的我来说,自选集所集中展现的邓先生治史的心路历程和举一反三的治史方法,更适合自己摸索学习的途径。因而我很认真地通读过这部论著选集,其中有的篇章读过三五遍,如《自序》《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辨析》《王安石在北宋儒学学派中的地位——附说理学家的开山祖问题》《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朱陈论辩中陈亮王霸义利观的确解》《〈宋史·职官志〉抉原匡谬》《陈傅良的〈历代兵制〉卷八与王銍的〈枢廷备检〉》等,只有认真读了邓先生的文章,才真正理解邓先生所说的:“‘史学即是史料学’的提法,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一命题的本身,并不含有接受或排斥某种理论、某种观点立场的用意,而只是要求每个从事研究历史的人,首先必须能够很好地完成搜集史料,解析史料,鉴定其真伪,考明其作者及其写成的时间,比对其与其他记载的异同和精髓,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基础工作。只有把这些基础工作做好,才不至被庞杂混乱的记载迷惑了视觉和认知能力而陷身于误区,才能使研究的成果符合或接近于史实的真象。”只有读懂了这些治史箴言,才能使其变换成自己研究宋史的钥匙和路径。 从上大学到读博士期间我没有专门学过目录学和史源学,在这方面的知识主要是从邓先生、漆侠师、王曾瑜先生的相关研究论著中揣摩而来,并有意识地边学习边实践,特别是邓先生对几部重要宋代文献整理的研究论文:《略论有关〈涑水记闻〉的几个问题》《〈涑水记闻〉点校说明》《陈龙川文集版本考》《陈亮集增订本出版说明》《〈宋朝诸臣奏议〉弁言》等,这些给我启示最大。其实,邓先生提出治史入门有四把钥匙——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如果要领会其精神实质,我以为从邓先生有关整理和研究文献论著中就能得到最好的答案。邓先生整理文献、研究文献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不是为了整理文献而整理文献,亦即不仅仅是为了搞清楚一部文献的来龙去脉,而是结合有宋一代的史实作相互交错的研究,不仅使文献通过整理得以成为坚实可靠权威的新善本,而且也使相关重大史实得到清晰梳理和最大限度地还其本来面目。 1995年以后,我的研究方向从宋代经济史转到宋夏关系史和王安石变法研究史,如果说能够取得些许进步的话,那就与我努力将从邓先生、漆侠师和王曾瑜先生所学来的目录学、史源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研究中有着直接的关系。 记得有一次在东北师范大学开会,韩东育副校长请与会的几位专家座谈,当得知我是漆侠师的学生,便顺口说你是胡适、傅斯年、陈寅恪、邓广铭一系的,你的史学传承很厉害呀。由此想到早年拜见兰州大学史学名家赵郦生先生时,先生对我说的一句话:“你的老师和你老师的老师邓广铭都是史学的正宗。”我还记得2004年一次在杭州开完会,与邓小南老师和张希清老师坐同列火车返回北京,途中乘着酒意说过我是当然的邓先生事业的再传者,而且理所当然要在宋史学界高扬邓先生和漆侠师的大旗,继承他们的衣钵,大有舍我其谁之势。现在想起来不免有点狂妄自大。学术需要薪火相传,邓先生晚年对自身学术事业不朽的念兹在兹,对于创建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作育人才的急切和不遗余力,既是对于自身学术名誉传世久远的在意,同时也是对自己开创的宋史学能够后继有人的期许。从这个角度来说,传承邓先生、漆侠师的宋史学是一项义务,更是一份使命。 (作者:李华瑞 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