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曾海军 世界上的文明,有已经死了的,没有人会费心它是否还在活着;也有仍然鲜活,而不会有人怀疑它的生命力。但对于中国的古代文明,它的死活至少是比较成问题的。曾经一度有人希望它快些死掉,或者就以为它真的死了,不然怎么会被称为“游魂”呢。现在么,许多学人正大论古代思想的现代意义,某些思想可能是要让它死掉的,另一些思想则不妨发扬光大。但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能做到意见统一,这种争论表明古代中国的文明纵然还活着,也一定活得很憋屈。尽管“取得精华,去其糟粕”的口号很令人生厌,但现代学人不还是充当着这种角色么?在精华与糟粕的取舍之间,许多思想被肆意提取,妄作理解。比如孔子的一句“礼之用,和为贵”一下子变得如此时髦,而另一句“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却丝毫也提不得。或者他所声称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会儿遭痛斥,一会儿却又有人说好话。这如果不是现代人理解得离心离德,难道还是孔子在前言不搭后语么?  孔子:必也正名乎?(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一、“正名”的前前后后 孔子生逢春秋乱世,周王室大权旁落,各诸侯国纷争不止,所谓“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第十六》)。实际上,不仅仅是诸侯国之间陷入无道的局面,诸侯国内部也由于权力的争夺,而造成君臣父子失序。面对这种“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尽管并无回天之力,却于栖皇之中坚信仁义精神之不可失,礼乐制度之不可无。孔子一生致力于将天下无道变有道,不过,若就其所提出的具体政治主张而言,似乎很难有能让现代人称奇的高招。如果将孔子视为是为诸侯王献计献策的谋士,那么他的主张恐怕还不如《墨子》中的守城术那样来得吸引人。因是之故,孔子的政治主张多被现代人所轻率解读,如对于孔子面对君臣父子的失序状态所提出的“正名”思想,便是鲜明的一例。尽管论及其现代意义的人特多,却分明有意无意地遗其要义。 《论语》中在两处不同的地方,记录着孔子所论及的“正名”思想。两处地方的具体情境有异,但所面临的现实政治状态则一,即都陷入于君臣父子的失序之中。其一处为: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第十二》) 尽管这一处没有直接言名为“正名”,但通常认为这便是“正名”思想的具体内容。另一处则径直提出“正名”之义: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第十三》) 通常认为,《论语》中记录的孔子言论,很多时候都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语境。在这里,前一处是针对于齐景公时失政于大夫,造成“君臣父子之间,皆失其道”(朱熹语)的局面,孔子才答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后一处的“正名”则是具体针对于“正世子之名也”(刘宝楠语),亦即为流亡于卫国之外的蒯聩正世子之名。就齐、卫两国当时具体的政治状况而言,整个儿就是一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局面。孔子无论答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是说“必也正名乎”,认定其在表达着同一种政治主张大概问题不大。众所周知,在春秋时代像齐、卫两国的这种政治状况,并非只是一时、一地的现象。孔子面对这样一种乱世,而一心致力于恢复天下有道的礼制秩序,“正名”便是作为这样一种努力所提出的具体政治主张。 如果是作为一种应对乱世政治的招数,孔子的“正名”主张提得可谓既不新颖,亦不高明。连当时的子路一听都觉得很没劲,竟然张口就说孔子迂腐。子路这人是鲁莽了一点,但作为孔子的高足,必定也是有识见的人,他说孔子迂腐,自有现实的缘由。一来想必“正名”并非是孔子一时灵感迸发的创造,可能是平时多有提起而逐渐成熟为一种政治主张;二来作为一种现实的应对,这一主张对于想成就霸业的诸侯王而言,显得不够务实。后一点也可以从孔子奔走列国却鲜有功业看出来。这么说来,孔子的“正名”主张一开始就显得不够吸引人,按理说也不应该为现代学人所关注,但没想到偏偏就经常为人所论及。这一现象值得好好琢磨。 现代学人关注孔子的“正名”思想,缘自两个方面的兴奋点。一是自认识论的框架出发,由荀子的《正名》篇上溯至孔子的“正名”;一是自意识形态的批判出发,由董仲舒的“三纲”说上溯至孔子的“正名”。以传统西方哲学的认识论眼光来看,古代思想文本中除了《墨子》中的“墨经”六篇,就要数《荀子》一书中的《正名》篇最值得现代学人称道了。通过一些认识论范畴的打理之后,便有了为人所熟知的“天官”“簿类”,“心有征知”一类的“哲学命题”出现。既然荀子如此得西方认识论的要旨,孔子的“正名”就不能不作为思想的源头,进入现代学人的法眼了。但传统思想之于现代学人而言,总是批判的热情高过继承的愿望,对于董仲舒的“三纲”说,可谓自“五四”以来就一直为人所不齿。他的那句“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与宋人的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道,成为传统文化罪恶昭彰的两句标志性用语。“三纲”的源头,不能不追溯到孔子的“正名”,这就是现代学人关注的另一层缘由。从两个方面的关注焦点来看,都是在孔子“正名”思想的外围作战,这种做法如今大概已没什么市场了。不过,自后一方面而言,由于同时纠带着现代性的平等理念,使得从这一战线又衍生出另一战场,即围绕着董仲舒的“三纲”说与孔子的“正名”论之间的渊源问题,展开了持久的争论。有人着力强调这一渊源,无非是要表明孔子与恶名远扬的“三纲”说脱不了干系,显示出对儒家的创始人毫不留情。与此不同,另一方面是有人出于对传统儒家的同情心态,力图将这一渊源切断,本意当然是希望保持孔子的某种“清白”。不过,无论是哪一情形,都说明董子的“三纲”思想要么令现代人生厌,要么让现代人避之而犹恐不及,而他们之间实则分享着共同的精神资源,此即现代性的平等理念。双方都表现出同样地热爱平等,而仅仅只是不一样地对待传统罢了。或许,两者之间的共同处比差异处更值得深究。可以说,正是双方这种平等的现代性精神理念,塑造了孔子的“正名”思想在今人心目中的基本形象。 孔子自春秋时代道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后,现代学人给我们疏理的一个思想脉络是,至孟子而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荀子而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荀子·王制第九》),接下来就是董仲舒的“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第五十三》)。无论是力主自孔子而至董仲舒为一脉相承,还是声称董仲舒之“三纲”另有源头,双方在材料引证上并无太大差异,可见关键发生在理解上的不同。由于双方都秉持现代性的平等理念,又在董仲舒以君臣父子取法于“阳尊阴卑”的不对等性上理解相同,于是差异仅限于孔、孟、荀一系下来,他们对于君臣父子关系的论述,究竟是不是对等性的。笔者以为,就凭着上述的几句文本材料所得出的结论,不过就是表达了对原始儒家是否愿意持一种同情姿态而已。正是现代学人出于这种对等性的衡量,定格了孔子的“正名”思想所具备的现代性意义。孔子所论君臣、父子关系是否具有对等性,似乎成为现代学人最为关心的问题。于是,在这一意识背景下,论及孔子“正名”思想的现代意义,进一步发生功能化的误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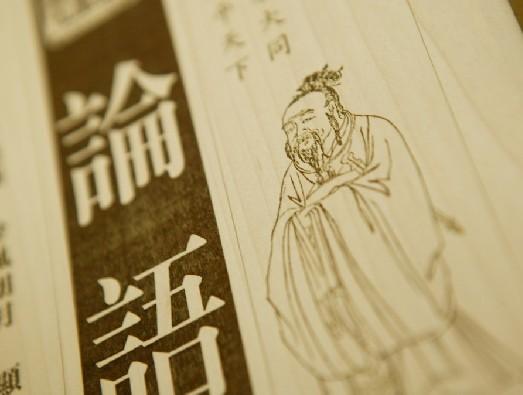 《论语》(资料图 图源网络) 二、功能化的误操作 对于孔子的“正名”思想,通过现代学人的悉心研究,就其关涉的现代意义而言,往往被揭示出以下两方面的相关涵义:一方面是以“名”指名位,强调与名位相符所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另一方面则是名位之间的对等性,即名位上的责任相互对等、互为条件。将“名位”的内涵置换为权利和责任,同时做出对等性的要求,这大概就是展开孔子“正名”思想现代运用的最强音。 将某个职位赋予明确的权与责,并以此考察这一职位上的任职者,这一极具现代性特征的操作方法,竟然方便地与孔子的“正名”思想贯通起来了。现代社会依然十分强调层级分化与功能差异,这充分体现在对不同职位的划分和规定上。它一方面源自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另一方面又与人与人之间丰富的差异性相吻合。不同职位被确定不同的权与责,它意味着既要求与这一职位相称的人来承担,又要求承担这一职位的人,其所作为符合相应的权利与责任。从“某种程度”上说,“循名责实”正可以视为是对这一情形的表达,这里的“实”区别于一般的具体事物,而指某一职位上的人所需要达到的实际状态,“名”则是类似于职位的名称。在“名”与“实”之间,需要进一步分辨的其实不是“实”,而是“名”。前者主要是曾经惯于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打量,才会弄出麻烦来。就“名”而言,现代社会中的职位分途主要表达一种功能上的差异,在现代人看来,不同职位的划分主要出于一种功能意义的不同。正出于此,现代人可以颇为骄傲地宣称,在一种普遍人格的照耀下,总统与乞丐的差别,显示的不过是大厦的顶层与底层的差异而已。但令人困惑的是,如何来理解现代社会中的不同“角色”呢?因为古代社会中所运用的“名位”或“名份”,显然不仅仅对应于今天的“职位”,同时还包括“角色”。将类似于父子之间的不同角色,视为是一种功能意义上的不同,想必也不是所有现代人乐意接受的。但随着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地赋予不同的角色以明确的权责,使得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关系越来越被功能化,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此而言,“循名责实”无论是对职位,还是对角色,表达的都是一种类似的功能上的操作。而这一操作据说就显示出与“正名”思想所包含的观念相通,即强调履行与名位相符的责任。但恰恰对于孔子的“正名”思想,如果仅仅只是作这样一种了解,它甚至都难以与现代性的社会分工区分开来。这虽然大大方便了现代学人大谈“正名”思想的现代意义,却完全遮蔽了这一思想原本具备的深层义蕴。 古代社会的“名位”可以等同于现代社会中的权与责吗?显然不行。古人的“名位”是有等级性的,而现代性的权责观念讲究的是平等。不过,现代学人会继续说,将“名位”的内涵置换为权与责的观念,不正是将古代思想运用于现代社会的具体体现么?笔者以为,“运用”也还有一个是否得法的问题,总不能是怎么样方便,就怎么样用。就这一具体“运用”而言,至少有买椟还珠之嫌。表达一种功能性上的分工,无需借助于孔子提出的“正名”思想,教科书上不是说“原始社会”就已经有了社会分工么?其实,分工大概是所有群居动物的基本现象,只不过通常声称动物是出自本能而已,就人类而言则是社会现象。孔子所提“正名”思想显然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这一基本涵义在荀子表达的“明分”思想中更为清楚: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亩,刺屮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守时力民,进事长功,和齐百姓,使人不偷,是将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孰,是天下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餧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荀子·富国篇第十》) 直至现代社会的权责观念,依然以这种分工现象为基础,这相当于就是一个常识。古代的“正名”思想,或者现代的权责观念,显然都不在于表达出一种常识,而是就着社会分工来表达什么样的理念。可以说,分工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现象,可谓古今中外概莫例外。但具体赋予分工以一种什么样的意蕴,或者说如何来塑造这种分工的形象,那就是古今相别,中外有异了。常识告诉我们,社会需要分工,同时也告诉我们,分工就是一种差异。一方面是事有大小,另一方面人有智愚,不同的人胜任不同的事,而且必然形成高下不同,层级有异。但如何塑造这种差异性的分工,接下来就不再是常识层面的事情了。高下之分究竟是人格有别的等级性,还是人格平等的差异性,这显然不是常识可以分辨得清的。古人着意于前者,荀子从“农夫众庶之事”说到“圣君贤相之事”,其用意昭然。现代人则深恶于这种等级制的言说,而让平等理念大行于世。如果今人以为平等只是一种常识,那显然是误会了。这一理念有着非常艰深的理论系统,它的普及就像革命事业一样来之不易。在这种平等理念的观照下,社会分工趋于一种单纯功能化的意义。即是说,社会分工的差别,仅仅只是出于功能上的需要,就像是机器的零部件一样,没有尊卑、贵贱之别。这非常切合被压迫阶层的强烈愿望,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成功地以现代性的方式抒写出来。我们耳熟能详的总理与掏粪工的故事,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愿望。 同作为一种基于社会分工的言说,从“正名”与权责之间也可以看出一些相通的基本意思。比如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或者进一步说,不同的人做与之相称的事,并且要求不同的人把相应的事做好。但这与其说是作为理论的内涵,还不如视为是理论的起点,据此而获得“正名”与权责相通的依据,有点不靠谱。“正名”与权责对于不同的人完成相应的事,其所做出的约束是不同的。人们更为熟悉的是,现代权责观念是通过赋予个体的权利,而同时做出相应责任的划分。所谓权责明确,现代人崇尚的是程序上的正义。与此相比,对于古人的“正名”观念实则相当陌生,由此以熟悉的权责观念去理解“正名”,就显得更不靠谱了。现代人非常清楚,基于平等理念的权责划分,不利于个体道德自觉性的提升,尤如程序正义可能会损害到实质正义一样。固如是,才不难明白中国学人对孔子“正名”思想的浓厚兴趣。从“正名”思想中读出一种道德自觉性是没问题的,但如果直接过渡到现代性背景下的责任感或义务感就有问题了。就责任或义务对提于权利而言,仍然不与古人语境中的道德担当相应。在现代性的观念背景下,以为孔子的“正名”思想更侧重于责任感一面,完成是似是而非的看法。现代性的责任感或者是义务感都离不了来自对权利的明确自觉,而它们就社会分工而言,始终只是功能化的意义。也就是说,高度的责任感成就的不过是良好地实现某一职位或角色的功能,它不关乎人的尊卑、贵贱,更与人禽之辨无关。相比而言,难道说孔子的“正名”思想也不过是在表达这样一种功能化的责任感么?将孔子的“正名”思想用来强调现代职位或角色的责任感,看来不过是一种功能化的误操作。  高贵(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三、一种高贵的意蕴 为了显示出今人运用古代思想的轻率,不妨先从追溯“循名责实”的出处开始。与今人很轻便地用上“循名责实”一语不同,它的出处却充分显示出法家的严酷,其云:“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仅就“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而言,确实与现代社会的职位分途若合符节,但其后一句“操生杀之柄”,却将古代的气质与现代性品格之间的对峙赫然标举出来。动不动就“操生杀之柄”的说法,在现代人的眼里,无疑会显得面目可憎。这也是上文之强调“某种程度”的缘由所在,“循名责实”的“实际程度”远不是功能化的操作能表达的。这种古今之间在精神气质上的对峙,比照上文普遍人格的说法,就是渊源于与等级人格之间的根本差异。可以说,普遍人格的观念之所以能如此持久地令现代人沉醉于其中,即在于能有效地防止“操生杀之柄”的恐怖。但今人在运用“循名责实”时,似乎早已忘掉了这一层,这是不是有些太大意了。当然,现代性的意义转换是允许的,担心的只是毫无一点自觉性,全凭胸中私意一通乱用。就法家的“循名责实”而言,自觉地化解掉“操生杀之柄”的恐怖性,而置换为“因任而授官”的功能性意义,这并无不可。它有效地防止了恐怖的杀戮,其意义不言而喻。但对于将孔子的“正名”思想,置换为一种权责观念,那就得另当别论了。 无疑地,“正名”思想同样塑造一种等级人格,但古代的等级人格并不只是呈现为法家的恐怖面目。为了防止恐怖的屠杀而打破等级人格,这种代价兴许还是值得的。但若只是为了瓦解等级人格而不惜一切代价,这种做法未必就是绝对“政治正确”了。“正名”所塑造的人格是等级性的,它事关人的尊卑、贵贱。但尊卑、贵贱之等,却不是用来造成上、下之间的压制,更与恐怖无关。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孔颖达疏云:“礼以体别为理,人用之当患于贵贱有隔,尊卑不亲。儒者用之,则贵贱有礼而无间隔。”儒家正是于尊卑、贵贱之间易生隔阂这份心都用上了,才有“和为贵”之真精神提得出来。今人所倡“和谐”口号,可曾识得此意么?“名位”就是成就自身人格意义的道场,在种种“名位”之外,并无一个抽象的人格意义悬在那里。在“名位”上的践履,不仅仅成就着人的尊卑、贵贱,同样也事关人禽之辨。在“名位”上立不起来,如父之不能为父,或者子之不能为子,那就有可能连人之为人的意义都丧失掉。但现代的权责观念则是,有一个抽象而普遍的人格意义悬在那里,先在地保障了所有人平等地享有人的尊严,而名位上的作为只能体现出功能上的好坏。当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时候,所谓君要像个君的样子、臣要像个臣的样子之类,用现代的责任感完全不足以描述出这种在相应名位上的担当。责任只是来自于一种权利的赋予,是相对于权利的履行,而名位上的担当则具有绝对性,它是具有人格意义的践履,甚至就是上达于天的精神路径。无论是君臣、父子,还是其他人伦关系的一方,在实现自身的精神提升时,同时也就意味着促成对方的转化。这是来自于一种使命的担当,岂是区区一种相对于权利的责任感可以表达的?亦非单纯所谓“自觉性”的说法可以道尽。与现代人追求一种平等的享有不同,古人着意于人的尊卑、贵贱之等,更看重的是下对上、人对天的高贵追求。自此一眼光观“正名”所塑造的精神意蕴,就不再围绕着是否具有对等性的问题了,从而自孔、孟、荀一系,“正名”的思想脉络应当是,经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而至荀子的“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荀子·正名第二十二》)可见,孔子提出“正名”思想,就不在于是否呈现出了对等性,而恰恰是基于一种尊卑、贵贱的秩序所提出的一种复礼主张。在儒家思想脉络中,礼以别贵贱可谓是一种常识,破坏了贵贱之等,扰乱了尊卑之序,就是所谓的礼乐崩坏。孔子的“正名”旨在要求,在不同名位上的人,要提升尊之所以尊、守住卑之所以卑之义。人只有陟黜于一种恰当的尊卑之序中,才能意识到高贵的深重意蕴。平等的理念先立一抽象而普遍的人格意义予以保障,在升降、起落之间无关乎尊卑而弭平一切,仅剩下功能化的差别。就此而言,“正名”的高贵意蕴,才具有反思现代性的深度价值。 论到一种高贵的意蕴,就不能不提到柏拉图那著名的“高贵谎言”了。上文提到,赋予分工的差别以一种什么样的意义,不仅古今有别,中外亦有异。同作为一种等级人格的塑造而言,古代的精神气质是相妨的。但具体的精神内涵上,亦有莫大的分别。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为一种等级人格做出如下立论:“他们虽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但是又由于同属一类,虽则父子天赋相承,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不一而足。所以上天给统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做后代的好护卫者,要他们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所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种金属。如果他们的孩子心灵里混入了一些废铜烂铁,他们决不能稍存姑息,应当把他们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安置于农民工人之间;如果农民工人的后辈中间发现其天赋中有金有银者,他们就要重视他,把他提升到护卫者或辅助者中间去。”尽管柏拉图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这不过是一个“高贵的谎言”,我们要追究的倒不是柏拉图为何要撒下这弥天之谎,而是说这一谎言何以显得“高贵”。在柏拉图那里,借助于这一“谎言”,无非是可以确保一种等级制度的安排,可以为人们所愿意接受。等级制度如果是基于一种等级人格所做出的安排,那么它就显得天经地义。问题是,谁来宣称人格的等级性?正如上文所指出,事之大小与人之智愚造成了社会分工的差异性,这是一个常识。但证明人格的等级性,却与证明其平等性一样艰难。柏拉图的这一“谎言”,正在于如此明晰地将人格的等级性呈现出来,从而为等级制度提供出形上证明。进一步的问题是,等级制度为何又显得“高贵”?大概古人对于人性的洞察,一早就明明白白的。与往上的追求相比,人确实太过于容易往下跌落了。无论是与“天”合一,还是与“神”相遇,古人至少都致力于一种精神或灵魂上的提升。现实的等级制度可以呈现出人的尊卑、贵贱之序,兴许还能保持一份对高贵的向往。可见,不管等级制度在历史经验中,被统治集团运用得多么糟糕,但至少对于哲学家或思想者而言,其立意却是“高贵”的。就此而言,孔子所云“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第十七》),“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第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第八》)之类,其意与柏拉图的“高贵谎言”就不乏相通之处。甚至不仅其意如此,当柏拉图说到,由不同材质铸造的人应该放到相应的恰当位置上时,在某种意义上,这同样是表达出一种“正名”思想。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孔子所云“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并非是表达一种不可移的根据,这与柏拉图的金银铜铁说区别明显。不过,在孔子那里,至少“上知”与“下愚”未曾移的时候,仍然表现为一种等级人格。这种区别并非不重要,但就塑造等级人格的精神气质,追求一种高贵的品格而言,古人显得更为一致。笔者强调这一点,实则是为了揭示出孔子与柏拉图之间,在“正名”的高贵意蕴上所包含的更大差别。在柏拉图所表达的“高贵谎言”中,核心之处在于,严格按照不同材质的铸造而放到相应的位置,如果护卫者的后代混入了废铜烂铁,也“决不能稍存姑息”,立马就放到农民中间去。听起来这表达的是一种在等级制下极具正义性的做法,等级人格的设定,不正在于要达到这样一种理想状态么?按照人格的等级状况而形成恰当的尊卑、贵贱之序,可以最好地引导人类趋于“高贵”。一种完全颠倒的等级制度,显然只能将人类导向邪恶。然而,这种理想性所预设的前提,是一种丝毫没有传统习俗的气息,人与人之间完全处于理性真空状态的社会生活。这也是柏拉图所设想的理想国之为“乌托邦”的真正缘由所在,他是站在生活世界之外的形上之处,在理性真空状态下所做出的纯粹建构。大概正是由于这种纯粹的建构过于清澈、明晰,才使得它不能不表达为一种“谎言”。与此相比,孔子的“正名”思想就显示出更为尊重传统习俗得多,但这并不妨碍这一思想所具备的理想精神,同时却又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构建,更不会表达为一种“谎言”的形式。可以理解的是,无论是对于孔子,还是柏拉图,一种君不君、臣不臣的局面意味着陷入到不正义的状态之中。但当这一局面出现时,正义原则所要求的,究竟是在相应的位置上换入更恰当的人呢,还是督促和转化相应位置上的人担当起来,做出进一步的提升呢?或者换一种说法,比如面对皇帝的低能,为何一位能臣非得认为把自己换上去才算是正义的,而恪守臣子之责,尽心尽力辅佐皇位之人获得转化和提升,难道就算不上是一种正义之举么?应当说,这两种情形都能获得正义的解释,关键是这种正义性由什么来奠基。就后一情形而言,这一正义性正是由父子之间的血缘亲情获得奠基的。在父子关系当中,当出现父不父或子不子的情况时,如何可能考虑在父或子的位置上换入更为恰当的人呢?正是父子关系的这种绝对性或者说无可更改性,意味着父子之间只能于相互转化和提升处用力。而父子之间天然的血缘亲情,既为这种转化和提升提供充沛的情感滋养,又需要在这种行为过程中获得进一步的培育。可见,孔子的“正名”思想,其核心之处在于,与柏拉图将政治等级隔绝于自然血缘之外不同,君臣关系是与父子伦常一起道出来的。当然,两者对于正义的致思路径虽异,对于正义都立意于“高贵”则同。于孔子的“正名”思想而言,既见其古今之殊,亦明其中外之别,而后可解一种高贵的意蕴。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