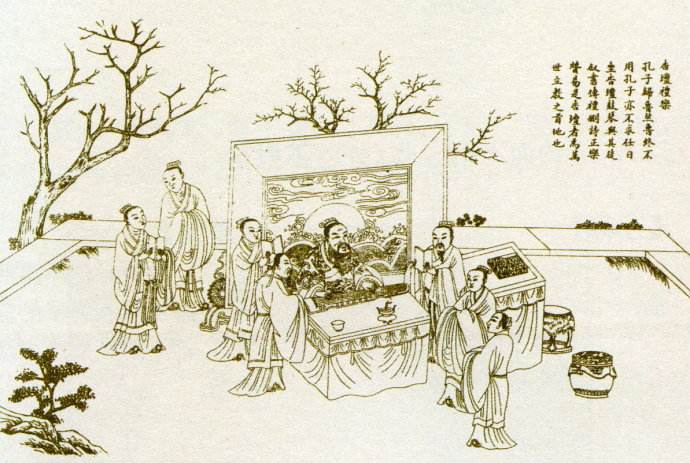 由《论语》所载,可看出孔子及其原始儒学对前代礼乐传统的三大贡献:其一,孔子在继承先王礼乐文化的基础上,将礼乐的核心内容凸显为社会秩序之上的人伦和谐;其二,孔子又从礼乐的两个方面,创新原有的先王礼乐文化:一则从其社会政治功能出发,进一步将传统礼乐文化重塑为以社会秩序和人伦和谐为终极目的,以礼教、乐教为主要内容,以政治伦理平民化为主要途径的礼乐教化论,从而儒学也由之发端,二则以仁、敬释礼乐,以发掘与开显原有先王礼乐文化的内在人性及其心理基础。其三,更为重要的是,孔子所谓的社会秩序和人伦和谐的双重实现,不但以政治伦理的平民化、普及化为中介和内容,而且离不开人们的仁、敬等人性本质。孔子将传统礼乐文化的根基,安放在“仁者爱人”的生命跃动中,也使原始儒家礼乐思想所致力的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在“慎终追远”的血缘亲情、“为仁由己”的道德自觉与“出门如见大宾”人伦关怀中最终得以实现。孔子这种以道德伦理为本位的新的礼乐观,既为传统礼乐找到了一个人性基础,也对礼乐的性情前提作了进一步的推究与论证。 在孔子之前,上古暨三代的宗教礼乐传统,经过周公制礼作乐的制度化、政治化改造以后,这一作为周代宗法社会等级规范的礼乐制度,便已初具伦理学意义。但是,孔子却将主要用于政治领域的西周礼乐制度,进一步伦理化而使其具有了完整的伦理学意义与社会意义,由此形成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西周时期的礼乐伦理化,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推行敬德宗孝等伦理观念的贵族教育,以培养有道德的统治者利于姬周统治。从孔子开始,将西周礼乐教化的伦理内容扩大到人伦关系的各个方面,而且提出“有教无类”的全民教育思想,将西周以来礼乐演变的主流由礼乐政治化转向为礼乐的伦理化,从而使以道德伦理为本位的礼乐观构成了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中心。在孔子等原始儒家看来,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从小到大,就必须要经过礼乐熏陶,“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礼,无以立。”在礼乐诗舞浑然一体的潜移默化中,让人在各种人伦关系和社会场合中体味、首肯人之成其为人之本然,进而以这种道德自觉认同现实伦理。具体说来,就是首先要在人伦社会的大网络中,找清个体所处的位置与所扮演的特定角色;紧跟着是通过礼教、乐教等,习染先在于个体的社会所包括的各种人伦关系及由之所赋予个体的各种人之应然,后者也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各种外在的行为规范“礼”;接着,在礼乐的长期潜移默化下,将社会所赋予的这种人之应然言行内化为道德伦理的自觉意识乃至伦理习性的自然养成;最后,各种人之应然的行为规范“礼”最终达成浑然一体的人之本然的道德伦理情感的“仁”。以道德伦理为本位的孔子礼乐观,实质是使每个个体在平时礼乐的教化中,于芸芸众生之中区别于自我而又调适于社会,自我与他人在对待与推己及人、换位思考中和谐相处。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各类人伦关系中,个人主体以自觉于自身的相应道德伦理,如敬、宽、信、慈、孝、悌等,修养身心而又融洽社会。在以外在的“礼乐”养成个体的道德心性或促成主体道德自省的同时,将世间的这些人伦关系及其相应伦理范畴,内化为个体的道德伦理自觉意识乃至自身的生存需要,使礼乐最终符合人类成其为一个和谐社会统一体的伦理要求与道德诉求。 如此看来,道德伦理相比于以政治秩序为中心,对孔子礼乐思想来说,前者更具有先在的优位性,且在孔子看来,依社会各成员的道德自觉而达成的社会伦理,涵盖甚或重新规范了其特定领域的政治伦理。相比于“礼不下庶人”的礼乐文化传统,这种优位性更趋明显:例如,周公的传统礼乐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礼乐制度,为以姬姓各级贵族为代表的周代统治者提供了政治准则与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而孔子礼乐思想则将礼乐施用的对象扩充为全社会成员,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在传统礼乐习染下,将外在的全社会各种对待的伦理关系,潜移默化地内化为社会各成员的“仁者爱人”的道德自省与“克己复礼”的主体自觉。 孔子礼乐思想道德自省与主体自觉,更甚于重政治的秩序,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视礼乐中的秩序与等级蕴涵。实际上,孔子重塑传统礼乐文化的终极目的之一就是社会秩序,因而孔子不能不看重礼乐文化所蕴含的社会的秩序性与政治的等级性——其理想政治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下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大力主张周礼的恢复和遵守,也是旨在重返周王政治权威下的社会秩序。不过,这种社会秩序与政治等级的实现和维护,在孔子看来,其实是不仅需通过礼加以推行和保证的,“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而且更是以包括君臣关系在内的人伦之间的对待与和谐相处、彼此相互尊重各自人格为前提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更为重要的是,孔子的这种礼乐秩序论,是离不开整个社会的人伦和谐的,最终是以全方位的各种伦理之道德自觉的达成而实现的。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