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渊明 道教是在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传统宗教,它是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沿袭方仙道,黄老道某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而于东汉后期形成。它以道和德为教义的核心,吸收了道家哲学的部分内容,以神仙思想为其中心思想,精、气、神的理论是其思想的最高理论。道教历经一千八百多年的发展传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教义思想,并在其宗教的教义思想支配下,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崇拜仪式和规戒。 道教的思想理论体系虽是宗教神学,但它的内容复杂,和中国文化极其广泛的联系。中国古代文化有些为道教所继承和发展,有些赖道教得以保存下来。道教对于中国文化不仅在历史上,甚至到现在还产生着一定影响,而道教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尤其深远,本文试图梳理出中国文学在道教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在中国漫漫历史长河中的发展变化,并从中透视道教与中国文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由战国末期到秦、汉之间,作为代表而足以影响上下社会各阶层的,应该算是儒、道、墨三家,到隋、唐以后,便以儒、佛、道为代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必然要吸收以上几家的思想,由此也形成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结构,即大多数文学作品中包含着儒、道、佛以及墨家的观念,而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贯穿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对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塑造,对中国古代的文艺思潮都有深远影响,更有甚者,道教的很多题材直接进入文学作品,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道教对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塑造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过去的教育,大体是走儒家孔、孟思想的路线,为建立人伦道德,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教育。儒教对于道、佛两教,素来便有视为异端的因袭观念,所以对于道家与道教在中国教育文化上的功劳多不愿提及,而实际在知识分子的人格道德教育中,大多都以儒家的思想做规范,以道家与道教的精神做基础,道家与道教的戒条,也就是中国文化教人为善去恶的教育范本,它以天道好还,福善祸淫的因果律做根据,列举许多做人做事、待人接物的条规,由做人做事而直达上天成仙的成果,都以此为标准。从汉、魏开始,经晋代抱朴子的提倡,一直流传到两三千年。它主张的道德,是着重在阴德的修养,所谓阴德,便是民间俗话所说的阴功积德;阴功,是不求人知,被人所不见,人所不知的善行,如明求人知,已非阴德了。这种为善的主张其实正合儒家的本意,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在潜移默化中已经接受了这样的道德观念,于是也相信有一种超越自然力量的“道”存在于世间,而这个“道”在一般人那里就是“良心”,就是一种敬畏观念,而在知识分子那里,便成为一种道德行为规范,如果这个知识分子考取了功名,他就要为民做事,多行善举,如果这个知识分子没有得到功名,他也应该相信这是“道”及命运的安排,他还会乐于接受这个事实并继续行善。可以说,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观念里已经打上了道教的深深烙印。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些文人进行文学创作也多半遵循这样一个观念,就是人在世应多行善事,行善事会有好的报应(不同于佛教的轮回观念,道教认为今生修善今生就可以得到回报),于是在他们的笔下,好人有好报,大团圆的结局比比皆是,这些都是文人思想观念的一种体现。 在道教观念的影响和塑造下,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也有较强的适应性,他们不仅能入世,也能出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但他们都能安然处之,道教主张轻功名,重生命,道教的主要经典《道德经》大抵以虚静无为、冲退自守为事,这种不与世争的观念使得中国古代文人在失意之时能够得到一种自我解脱,儒教使中国人处于工作状态,道教使中国人处于游戏状态,道教的自然主义,正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的心灵的止痛药膏。在这种处世哲学下,中国文人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在不同的心境下写出不同的作品,李白是这样,苏轼是这样,还有很多的文人都是这样,在一种淡泊的心态下也让他们的文学作品有了更多的风采。  庄子 道教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潮的影响 道教的思想观念直接脱胎于道家,也把道家的原始文本《老子》和《庄子》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经典,这些思想汇入中国古代的文艺思潮中并与儒家、佛家等其他的思想融合,在中国古代的文艺长河中不断前进,魏晋玄学主要融合儒道,以儒解道,促生了玄言诗和山水诗,使文艺侧重追求自然之美,到唐代诗歌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之分,道教对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极大,一些诗人如李白、李贺等受道教思想的影响以丰富的想象为诗歌插上腾飞的翅膀,而唐人的笔记小说中,道的成分更重,宋代文人受儒道佛观念影响,既能以积极的心态入世,又能以超然的心态出世,并用自己的笔记录内心的感受,自明清以来,文学作品中的鬼神观念不断加强,而且有了更多的善恶报应观念,体现了一种文化大融合的现象。 纵览中国古代文学史可以发现,浪漫主义的文学思潮贯穿始终,而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潮直接来自道教及道家思想的启发。一般认为,中国文学浪漫主义传统的源头是庄周的《庄子》,庄周继承了老子的思想,是道家思想得创始人之一,《庄子》则是一部浪漫主义的寓言哲理著作,寓言故事并非人世间所真正有的事情,一般都是作者通过现实生活中所残留的现象来想象而构成的虚拟世界,庄周在其幻想的国度里构建了自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的理想世界,其丰富瑰丽的想象开启了中国古代浪漫主义的大门。屈原的《离骚》现实叙述与幻想驰骋相交织,同时蕴含着哲学、宗教、文学等多重因素,是远古神话传说的直接的和完全的继承者,这种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也在后世薪火相传,汉代的辞赋家贾谊、建安时代的曹植、正始时期的阮籍、两晋六朝时的左思、郭璞、鲍照、陶渊明、盛唐的李白、中唐的李贺以至宋代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派以及明代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汤显祖的“意趣神色说”等浪漫主义的美学理论,明清的小说家吴承恩、蒲松龄,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发展了这一优良传统,甚至清代的现实主义巨著《红楼梦》的开端部分也极具浪漫主义色彩,“游幻境”的片断实际上是对人物形象的一次总结,具有强烈的神奇魔幻的色彩。 道教思想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道教强调自然无为,以柔克刚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弱者道之用”、“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道家对阴柔的重视,使中国文化有了一种柔性特征,这也使中国文学形成一种以追求从容徐缓、沉郁豁达、缠绵悱恻为美的阴柔风格为特点的潮流。 二、道教还强调“有生于无”、“唯道集虚”、“致虚极守静笃” 这种对虚的重视,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观念,也使文艺形成了虚实相生的审美追求,在文学作品中强调给读者想象的空间,尤其是诗中“无字处皆其意”,追求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空白之美。 三、“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反者道之动” 道教对循环论的重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艺对圆形意味的追求。小说戏曲的故事进程也多要曲折离奇:先是由合到分,然后中间经过无数的曲折,最后又由分到合,以大团圆作为结局。 总而言之,道教的思想观念中崇尚自然“无为”,反对“有为”妄动,反对人为物役,欣赏率性“逍遥”,老庄重视自然,反对人之妄为对自然本性的束缚;孔孟则强调礼教,主张“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老庄的思想影响文艺,使之以追求自然美为最高境界;而受儒家影响的文艺则推崇雕琢美,在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中这样两种观念也明显并存,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各有侧重罢了。 道教题材直接进入古典文学作品 中国古代的很多文学作品受到了道教的影响,甚至还有很多作品直接以道教神话故事为题材,使得中国古典文学表现了丰富多彩的特色,其中魏晋游仙诗、玄言诗、山水诗,唐代山水诗、田园诗、吟咏道教的诗、宋元的话本、元明的戏曲以及明清的小说很多都带有一定的道教色彩。 早在东汉行世的道经《太平经》中,即可找到有关修身养性的“七言歌谣”。如该书卷三十八所载《师策文》就是一篇。这篇歌谣在用韵上“句句连押”,除了开头“师曰”二字外,全用七字一句,其中有云:“治百万人仙可待,善治病者勿欺绐。乐莫乐乎长安市,使人寿若西王母,比若四时周反始,九十字策传方士。”可视为七言诗的雏形。差不多与《太平经》同一时代问世的《周易参同契》则有四言诗与五言诗的句式。魏晋时代,道教诗词的种类随着道教活动的扩大和神仙传说的流播而增加。此时,用以暗示炼丹方法的七言炼丹诗以及四言咒语诗在道门中秘行。七言炼丹诗的主要代表作有《黄庭内景经》与《黄庭外景经》。该书企图以人体五脏六腑作为诸意象联结的链条,通过对各藏腑神明形象的描绘,以唤起修习者的内在感觉图像,达到内炼金丹的效果;但作者又怕“泄漏”天机,故又大量使用隐语,如以“娇女”指代耳朵,以“重堂”指代喉咙、以“灵台”为心脏等等,行文具有譬喻、隐喻的特性。至于咒语诗尽管比较缺乏语言的修饰,但却注意气氛的渲染。像《太上洞渊神咒经》卷十二所载《三天真王说清除瘟疫星宿变度神咒》,描述五帝及天兵天将各执兵器绞杀妖精的场面,颇有战斗的火药味。当然,就文学的艺术手法角度考察,无论是七言炼丹诗,还是咒语诗,都比较缺乏艺术感染力。与之相比,游仙诗的艺术造诣则略高一筹。所谓游仙诗即是一种歌咏神仙漫游之情的诗歌作品,其体裁多为五言,句式不一,其最初都是道士创作,如晋代道士郭璞就有大量游仙诗问世。魏晋南北朝间,不仅道士作游仙诗,许多著名的道外文人也热衷于游仙诗的创作,以至所作诗章成就甚至超过道内人士。如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竹林七贤、陆机、郭璞、沈约等,都属其中的佼佼者,而这些诗歌多半都涉及道教题材。如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还有嵇康、阮籍等等也有各自的作品行世。此外,这一时期,随着道教斋醮法事的开展,道门中还注意创作仙歌道曲词,配乐演唱。有些仙歌道曲的体式还为文人们所雅好,如步虚词即是其中之一。步虚词属于乐府文学,唐代吴竞《乐府古题要解》称步虚词为“道家曲”,“备言众仙缥缈轻举之美”。步虚词一般为五言十首,演唱时依八卦九宫方位,绕香案“安徐雅步,调声正气”,循序而歌,以象征天上神仙绕“玄都玉京山”斋会之情景。供演唱用的步虚词主要见於《太上洞渊神咒经》卷十五《步虚解考品》,还有收入《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中的《空洞步虚章》,也在道门的斋醮法事中广为应用。文人创作步虚词杰出者有北周之庾信。他的十首此类作品模拟道门步虚之韵律,且有重辞采、工对仗之特色。如第一首“混成空教立,元始正涂开。赤玉灵文下,朱陵真气来”[viii]遣词造句既能化用古书典故,又进行了一番锤炼。与步虚之类仙歌道曲存在着一定关系的“玄歌”、“变文”,在唐前也为道门传法布教服务。今所见敦煌写本《老子化胡经》卷十即收有玄歌、变文若干首。玄歌即“玄道”之歌;变文则是演述神变之事的一种体式,玄歌变文可咏可唱,前者一般为五言,后者则多为七言,融叙事与描绘于一体,且有故事性,语言较为通俗,故易于民间流行。 隋唐以来,中国诗歌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唐代道教由于得到朝廷的大力推崇,也进入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从隋唐诗人王绩、王勃、张九龄、李白、李贺、李商隐等文集中都不难找到反映道教生活、创造神仙境界的作品。在这样一种崇道的氛围下,大量的山水诗、田园诗和大量吟咏道教的诗词也都沾染了道教的仙气,田园诗在内容题材上多描写自然之貌,得自然之神韵,讲究对意境的营造,非常注重对言外之韵的追求,如: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皆寂,惟闻钟磬声。(常健:《破山寺后禅院》) 一路经行处,茵苔见屐痕。白云依静渚,芳草闭闲门。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深。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刘长卿《寻南溪道士》) 读这些诗,你就会感觉到总有一种道家气味漂浮其中。而王维的诗则更进一步,达到了司空图所言的“思与境偕”、“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的诗之至境: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反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 细心品味,你就会深切体会到这些诗所内含的意韵与道家所崇尚的“圣人无我”、“涤除玄览”、“和光同尘”是多么的契合。 吟咏道教的诗歌也比比皆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非李白莫属。李白被后人称为诗仙,除去他飘逸的诗歌风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教信仰在他头脑中的根深蒂固。李白自少年起便仰慕道教,与上清派道士司马承祯、吴筠结方外之游,并最终成为上清派第十二代传人,作为一名道士,他熟悉道教神仙典故、道教教义;作为一个诗人,他继承前人诗歌成就而又发扬光大并从道教的宗教思维模式中获得激情。两者相辅相成,造就了他的诗才。纵观李白的诗文,有许多是吟咏道教的神仙诗,当然更多的是受老庄道家思想濡染而创作的浪漫不羁、超然物外、孤高飘逸,一叹三绝、千古吟唱的浪漫主义文学杰作。如其在《登泰山诗》中这样咏道: 清斋三千日,裂素写道经。 吟咏有所得,众神卫我形。 云行信长风,飒若羽翼生。 此诗描写清斋修炼后生活,幻想出诵经修炼后众神卫形、飒若羽生的情景。其飘然欲仙的理想,正是李白的境界,而李白最负盛名的游仙诗则是《梦游天姥吟留别》: 海客谈瀛州,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 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 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瞑。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 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 清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 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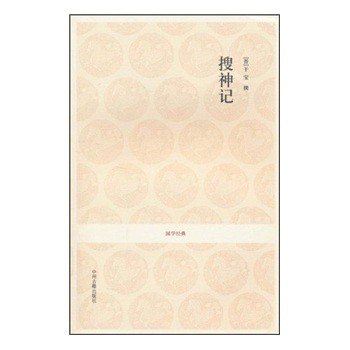 《搜神记》书影 小说、戏曲中的道教元素 小说在其成型发展的过程中也与道教有着颇深的渊源,志怪体、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四大类小说类型多与道教有密切联系。志怪小说以《搜神记》为代表,记述的内容多与道教相关,有的是以神仙故事、道人事迹为基本内容的,有的以地域方位为基本框架,叙述诸方名产、珍贵物品及由此演成的奇闻异事,有的杂记天上星宿神明、卜筮占侯、仙凡婚配故事,梦故事,内容驳杂,形式不拘一格。隋唐开始,中国小说进入重要发展阶段,在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出现了传奇小说。许多文人广泛搜罗当时流行于民间的各种神仙故事传闻加以创作。例如李复言《续玄怪录》中的杜子春;谷神子《博异记》中的阴隐客;陈翰《异闻集》中的仆仆先生;李隐《潇湘录》中的益州老父;皇甫氏《原化记》中的冯俊、采药民、伯叶仙人;戴孚《广异记》中的刘清真、麻阳春人;薛用弱《集异记》中的李清;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卢山人等等。在这些作者所撰的故事中,无论是酒徒、园叟、药贩、工匠、乞丐、胡人、书生、逸人,还是臣僚与富豪,只要虔诚信仰道教,努力修炼,都会成为有高超道术的神仙。例如唐皇甫牧《三水小牍》写道士赵知微结庐於凤凰岭,幽夜练志,有“分杯结雾之术,化竹钓鲻之方”,能使阴霾笼罩的黑夜变成明月当空朗朗之夜,还能使浓阴密雨停止等等,颇为神奇。此外,还有一些作品虽然没有直接以神仙道士异闻为题材,而是以梦幻故事、历史故事、人情世事为题材,但却通过各种故事情节来表现道教的思想观念。诸如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以梦为框架,宣传荣华富贵乃虚幻不足求的道教人生观,穿插了道士催梦、解梦以及仙女下凡奏乐的种种情节,故事的发展有起有伏,扑朔迷离。张鷟的《游仙窟》取材于初唐文人所熟悉的冶游生活,作者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他奉使河源,途径积石山,投宿神仙窟,与崔十娘、五嫂邂逅交好的故事。再如唐无名氏《李林甫外传》写一丑陋道士劝李林甫当宰相“慎勿行阴贼”,当为阴德,广度世人,无枉杀人,如此则三百年后“白日上升矣”。此浸透了道教关于“欲修仙道,先修人道”的观念。文中还有道士授李林甫以竹杖,令其腾空飞行的描绘,具有浓厚的道术气味。唐代以降,道教传奇小说继续发展,宋代有吴淑《江淮异人录》、王陶《谈渊》、蔡襄《龙寿丹记》、苏辙《游仙梦记》等,都是搜奇猎异空气中产生的作品,故多怪异之谈,其故事的梦幻色彩颇浓,并保存了一些特异功能的传闻资料。宋元时期,出现了“话本小说”:所谓“话本”,就是说故事的底本。故事取材多样,神仙鬼怪是重要内容之一。道教话本小说即指以神仙鬼怪为内容、以道教信仰为宗旨的一类小说。此类作品往往将民间传说系统化,对一些关键性的细节进行加工,以道教法术描写警示世人。如《西山一窟鬼》《西湖三塔记》《定州三怪》等著力描述精灵鬼怪,渲染恐怖气氛,这是道教神仙鬼怪思想在市井生活中的一种反映。在这一时期中,还出现了模拟小说话本之体制进行创作的作品。如冯梦龙的《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以及凌蒙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与《二刻拍案惊奇》。文学史上将此五部作品称之为“三言”、“两拍”。此类拟话本小说题材多种多样,其中亦不乏表现道教神仙思想观念或反映道教生活的篇章。例如《吕洞宾飞剑斩黄龙》、《旌阳宫铁树镇妖》等等。明清时期,中国小说创作更加繁荣。此时在话本及拟话本小说基础上,出现了长篇章回体小说。其中也有一批作品是以道教生活为题材、以道教思想为宗旨的作品。如《封神演义》、《四游记》、《韩湘子全传》、《吕仙飞剑记》、《禄野仙踪》等。这类作品可称为长篇章回体道教小说。其特点有三。第一,把历史故事和神仙故事融汇在一起。第二,将民间流行的神仙故事进一步加工。第三,作品的字里行间渗透著道教修炼成仙的义理。此外,还有一些作品本是用以宣传佛教思想,但其中亦深受道教影响,如《西游记》即是如此。至于由此衍化而出的《唐三藏西游释厄传》、《西游记传》一类“西游续书”,则更有浓厚的道教色彩。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文学史上具有极高的价值,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共有短篇小说431篇,其故事大多涉及神狐鬼怪,作者在自序中承认是“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有人说,《聊斋志异》是一部写鬼写狐的神怪小说;也有人说,蒲松龄通过写鬼写狐来讽刺黑暗的现实社会,但无论如何神仙鬼怪的题材是构成其小说的骨架,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建构了道教的另外一个仙狐世界,成为中国文学中夺目的明珠。 元明以来的戏曲也吸收了很多道教的元素,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院本名目》记载,金代流行的院本戏剧甚多,其中属于道教神仙题材的有《庄周梦》、《瑶池会》、《蟠桃会》。至于南戏的传统剧目当中尚有《老莱子斑衣》,此亦出于道教的神仙故事,而到明清两代,众多戏曲存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神仙道人故事为题材的,例如《邯郸记》、《东方朔偷桃记》、《吕真人黄粱梦境记》、《茯苓仙传奇》等数十种。另外,有为数不少的作品虽然不是专门演述神仙故事,但却多杂有这方面内容,无论是婚恋题材、历史题材还是公案题材,我们都可以看到不少神仙景观的铺排、道教法事活动的描写,有些作品情节的推进往往有赖于神仙道人的"点拨",这些现象都表现了道教思想对传奇戏曲的影响。 中国的文明史是伴随着中国宗教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目前发现的甲骨文多半是占卜、祭祀的文字,随着文明的进步,道教的思想体系逐渐成熟,中国文化也深深地打上了道教的烙印,老庄道家的哲学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中国道教的思想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民族共识,尤其是中国文人的内心深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塑造了一代代的中国文人,使其具备了刚柔相济的品性,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传承者和发扬者,而以老庄道家为始端的浪漫主义文艺潮流也一代代流传,不仅在文学上,甚至在文艺的诸多领域催生出一批批杰出的人才,以道教内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层出不穷,不仅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内容,也不断推动中国文学向前迈进,为中国古典文学画上了辉煌的一笔。 原文链接:http://whfawong.blogbus.com/logs/2835250.html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