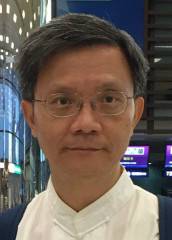朱子的世界秩序观之组成方式:朱子的天人关系思想析论 作者:吴展良(台大历史系教授) 来源:原载于 《九州學林》五卷三期(2007秋,香港)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二月初四日辛亥 耶稣2018年3月20日 一、绪论:世界秩序或人间秩序? 宋代人所建立的世界秩序观,对近世中国与东亚文明影响甚深。大抵中国与东亚近世有关宇宙人生各方面的看法,都与宋人所建立的世界秩序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其中又以朱子的世界秩序观最具有代表性,也最值得我们深入探究。朱子的世界秩序观所涉及的范围至广,大抵秩序一词与「理」的含义十分接近,研究朱子理学思想的作品中,讨论到秩序问题的自然很多。当我们对于朱子所说的「理」有不同的诠释时,对于朱子的世界秩序观也会有不同的理解。[1]笔者对于朱子的理学思想及世界观另有作品专门加以研究,在此不可能也不企图对于朱子的理学或世界秩序观做一全面的说明。本文所谓的「朱子的世界秩序观之组成方式」,实有一特殊的问题意识。 此问题意识起源于学界近年来因为余英时先生的巨着《朱熹的历史世界》所引发的重大争论。余先生此书别开生面,对于理学所源出的政治文化生态,有非常周详而深刻的分析。学界也因余先生的大作而注意到宋人建立一全面性新秩序的大企图,然而对于这种秩序乃至理学的基本性质则莫衷一是。余先生认为朱子的秩序观起于他对于理想政治或人间秩序(含家庭与人际关系)的关怀,从而投射到形上或宇宙论的层面。他并且提出了哥白尼式的「回转」说,希望现代学者不要只注意哲学化了的「道体」问题,从而误以为理学可以抽离实际的历史情境。杨儒宾先生则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朱子的内圣之学与价值体系自有其追求绝对与普遍道体或真理的基础,并不是为了政治问题而服务。他认为余先生书中所质疑的哲学化的道体与人间事务分离的问题,从理学传统「理事不二」的基本理路来看并不真的存在。朱子与理学的学术思想与其说是对抗现实世界中的王安石的新学不如说是对抗更久远的佛学而产生。学界所已知的传统「理学大叙事」其实已足以解释朱子学的基本性质。对于理学的研究,哥白尼式的「革命」并不必要。[2]而刘述先先生则一方面承认余先生所提出的新角度之价值,同时为新儒家重视形上问题的研究方式作了辩护,并指出余先生研究方式的限制。[3]这些文章,引起不少后续的讨论。[4]余先生与杨先生也都进一步写文章提出各自的看法,不过双方的交集似乎并不多。[5] 余先生所指出理学家深涉世务,其思想不可以抽离实际的历史情境来研究,尤其不能只注意哲学化了的「道体」问题之说法,对于朱子学与理学的研究,实有重大的贡献。对于理学与王安石新学以及北宋儒学的密切关系,亦有深刻的阐发。然而该书之所以引起上述的争议,除了学风的差异外,其关键在于各方对于朱子的秩序观之组成或形成方式有很不同的看法。也就是说,对于天道与人事或所谓形上及宇宙的秩序与人间的秩序究竟是何种关系?其发生的先后次序及组织方式为何?有非常不同的认识。关于朱子的秩序观的组成方式,前述双方的看法虽各有其道理,却不免有过多的「二元对立」之倾向。根据笔者的研究,朱子的世界观及其思维与认知方式,具有「整体观」的特质,基本上视一切事物为一不可分割的整体。[6]因此很难说他根据了理想中的人间秩序而建立了形上或宇宙的秩序观。也绝不能说他所认识的道理或道体,是「冥契」而得,超乎物外,中间不涵盖人间秩序。人间秩序、心性之理、宇宙秩序在他的思想中其实交织成一片。彼此互相增强,而很难有内外、主客、天人的明确分野。这秩序观既非脱离了时代与个人生活的背景凭空而生,也并非没有恒常或所谓超越的层面。专就政治与人间秩序,或偏就超越及普遍的层面立论,不免都有所不足。所以与其说朱子所追求是一种人间秩序,不如说是一种世界秩序,而包含了上述所说的各个层面。 为了证实上述的说法,本文将仔细分析朱子思想中的天人关系。而这个问题,虽然不等于,却涉及了自然与人文、本质与现象、恒常与变化(constancy and becoming)、超越与实存之关系等问题。从现代学术的角度来看,朱子的世界秩序观具有四个主要成分:宇宙秩序、身心性命的道理、伦理秩序、以及现实的政治社会秩序。宇宙秩序偏于天与自然,现实的政治社会秩序偏于人与现象,至于身心性命的道理与伦理秩序则跨越了天与人。传统上理学乃至哲学的研究,多偏就前三者立论。而余先生所谓的「人间秩序」,则多就后者立论,兼及伦理秩序。笔者则认为在朱子的思想体系中,天与人乃至前述四成分实有密不可分、彼此呼应的关系。所以上述的分类与提问的方式,在现代学术而言虽为必要,却也有造成误解的危险性,必须非常谨慎地处理。 对于朱子而言,所谓天人本为一体,互相包含融合。人生一切亦本为宇宙的一部份,而宇宙的道理,与人生的道理同为一种道理。所以究竟而言,天与人实不能二分。然而一般人生未必能充分表现宇宙原有的元气淋漓,刚健不息,所以天人亦可分言。自然与人文、恒常与现实之间,未必没有矛盾。天人分合之际,本为一大问题。传统的思路与现代大为不同。本文将主要从天人这两个层面,来探讨朱子的世界秩序观之组成方式。 对本文的问题意识讨论至此,我们有一个基本问题仍必须做进一步的交代。前文在使用秩序与理字时并未严格加以定义。然而当我们用秩序一词来说明「理」的概念时,这本身就是一种现代诠释,不能不先作一番语意分析。朱子所谓的「理」,原意指「文理」、「条理」,或曰「阴阳五行不失条绪」处为理。这种理的概念,深具依乎天地运化及自然脉络之意,故又称之曰天理。然而现代中文「秩序」一词,其含义多从西文的order来。主要是人为(artificial,logical or comprehensive)或上帝的安排(arrangement),均属有意志的控制性作为。所以用现代的秩序一词来阐释朱子的「理」的概念,实有变自然作人为的危险。这一点在在讨论朱子思想中的「理」究竟是一种人间秩序或世界秩序时,当然会有所影响。当我们用现代意的「秩序」来诠释「理」时,很容易将朱子的思想解释成一种人为的、着意的人间秩序之安排。然而朱子原本的思想,可能更倾向于一种天地人生自然的道理。如此说来,「秩序」一词是否就不能用了呢?其实中文本有「秩序」一词,其古义可以同时含括自然与人文的次序与等级。[7]如果我们不把「秩序」一词,限于order的意思,而取其广义的说法,可以包含任何型态的规律或次序,则「理」字也不能不说包含了某种秩序。 虽然如此,朱子思想中的「理」,内涵深邃复杂,并非「秩序」一词所能包括。对于朱子而言,合理的,都蕴含了某种秩序,但有秩序的,未必就合理。理的含意深,它指向并蕴含一种深层的秩序。然而表面的秩序,未必合于人心,也未必适于人事,所以并不见得合理。朱子的理世界,蕴含了一种「世界秩序」观,这是一种深层而普遍的世界秩序,然非表面的、人为的秩序。 学界过去并无以朱子的世界秩序观为名的专门研究。以「秩序」或order为名的研究,也只有:丸山真男,〈朱子学と自然的秩序思想〉,氏着《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二章第二节(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52);Schirokauer,Conrad.“Chu Hsi’s Sense of History.”in Conrad Schirokauer and Robert Hymes ed.,Ordering the World:Approach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等寥寥数项。[8]其中Ordering the World一书的名义与「世界秩序观」最为相近,然而Schirokauer一文的重点在于处理朱子的历史与政治意识,与本文所要处理的「世界秩序之组成方式」不同。丸山真男则认为朱子学中政治社会(或曰人间)的秩序,基本上奠定于自然法。根据这种自然法所建立的秩序,永远不易,缺乏近代的变革性。且不论朱子的所建立的世界秩序是否永远不易,丸山真男认为朱子的人间秩序观本于其自然法的说法,与余先生之说大为不同。这也表示我们必须对此问题做出进一步的研究。 二、一体浑成、天人合一的世界秩序观 现代学界习惯上将朱子的秩序观分成宇宙的秩序(自然法)及人间的秩序这两大范畴;或宇宙秩序、身心性命的道理、伦理秩序、政治社会秩序等四个层面。这样的分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与研究上的方便性,然而当我们如此分类(categorization)时,却很容易受现代的思维方式与世界观的影响,而将这些分类看成不可跨越的基本分野。其实对于朱子而言,宇宙与人生,以及上述四个方面实有一体难分的关系。而其所以难分,在于朱子认为人与天地同构且一体相应。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天人合一或曰天人一理。《朱子语类》记载: 问:「天未始不为人,而人未始不为天。」曰:「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凡语言动作视听,皆天也。只今说话,天便在这里。顾諟,是常要看教光明灿烂,照在目前。」[9] 天人本只一理。若理会得此意,则天何尝大,人何尝小也![10] 这是说人生的一切,包括其中的道理,都来自于天,所以人的身心性命乃至人间一切种种,莫不源自于天。宇宙与人间,或曰自然界与人文界的道理本是一个道理,不能分而为二。[11]所谓天与人在名及义上虽然有别,然而其道理及本性则一。既然本来是一个道理,所以朱子本人并不会将世界的秩序判分成天与人两大范畴或宇宙秩序、身心性命的道理、伦理秩序、政治社会秩序等四个层面,更不会追问其间的基本关系为何。相反的,在《语类》与《文集》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朱子的语言及思维自由地出入上述各种分类之中,将所谓不同类别的事物彼此连类比论: 世间自是有父子,有上下。羔羊跪乳,便有父子;蝼蚁统属,便有君臣;或居先,或居后,便有兄弟;犬马牛羊成群连队,便有朋友。[12] 人得其气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气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无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无所知。且如人,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气,所以识道理,有知识。物受天地之偏气,所以禽兽横生,草木头生向下,尾反在上。[13]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张之爲三纲,其纪之爲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14] 像这一类的话语,如果我们固守现代的分类,几乎只能将其列入不能理喻的胡话或专断蔽固的教条。然而这一类的语言与思维,其实充斥着朱子的作品。我们必须跳脱现代人的思维与分类,另求索解之道。从现代的世界观来看,宇宙秩序不等于身心的道理,更不等于伦理秩序、或现实政治、社会、经济秩序。同样地,身心的道理也不等于伦理秩序、政治秩序或现实社会与经济的秩序。现代人认为上述领域虽皆密切相关,然而各有各的逻辑,不能混为一谈。在学术分类上,也各自从属于不同的范畴与科系,而有不同的本体及方法论上的假设与出发点。因此,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朱子的世界秩序观,就不免觉得非常奇怪,而要追问其中的关系。譬如究竟是人间的秩序决定了理学所认定的宇宙秩序呢,还是宇宙秩序或某种超越的源头决定了理学家所相信的人间秩序?我们若将自然与人文界的道理分割来看,读了前面数段引文,很容易认为朱子其实是将他所相信的人间秩序有些勉强地套在宇宙自然界之上;然后反过来,如丸山真男所说,用这套自以为是的「自然法」来强力地规范人世,形成一套僵固不变的伦常秩序。然而朱子的思想如果如此勉强而教条化,则他那大量复杂细腻、博大精深的有关宇宙人生基本哲理的讨论,岂不是难以解释? 问题的重点在于朱子对于世界并不采取天与人、自然与人文乃至超越与实存等二分法。相反的,他不断强调这些层面一体难分的关系。换言之,当朱子观天时,他并未忘记人,而且将人当作天的一部份;当他体察人事时,他也未曾忘记天,而企图认识那通贯一切人事与自然的道理。用格物补传的话来说,就是「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15]这所谓「即凡天下之物」,并不分自然人文,更不分现代的各种学门,而是不断地从天地人物一切万殊之中,去认识那一贯的道理。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理学家从天道秩序来规范人世,也经常看到他们从人的立场出发来论天道。我们且看下面两段话: 问:「『天命之谓性』,此只是从原头说否?」曰:「万物皆只同这一个原头。圣人所以尽己之性,则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若非同此一原,则人自人之性,物自物之性,如何尽得?」又问:「以健顺五常言物之性,如『健顺』字亦恐有碍否?」曰:「如牛之性顺,马之性健,即健顺之性。虎狼之仁,蝼蚁之义,即五常之性。但只禀得来少,不似人禀得来全耳。」[16] 问:「濂溪作太极图,自太极以至万物化生,只是一箇圈子,何尝有异?」曰:「人、物本同,气禀有异,故不同。」又问:「『是万为一,一实万分』,又如何说?」曰:「只是一箇,只是气质不同。」问:「中庸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何故却将人、物滚作一片说?」曰:「他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重声言两「则」字。能尽物之性』,初未尝一片说。」[17] 上一段说人与万物的「性」同出一原,而此「性」表现在每一事物之上。下一段则说虽然同出一原,但是气禀有所不同,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此处所谓「性」的意义,是说万物一体同源的「性」,与我们平常所使用,只就一物而言的性质颇为不同。朱子认为万物之性,本来一体同源,所以我们不能止于个别之物,而必需通过对于众物之性质的研究,而认识到那一体之性。「天命之谓性」的「性」,是就宇宙生生不息的根源,也就是所谓太极而言。万物都来自此生生不息的源头,自然同具此本源之性能;而离此万物,亦无从认识那一体同源之性。万物既然同具此一本体,所以理论上来说,万物各自都有无限的可能。然而唯有人似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朱子进一步认为天地本然的性能只有在人身上表现得最为完全,其他万物都只能领会及表现天地中一枝一叶的「性能」。上述的性字,根据程朱学派「性即理也」的说法,都可以换成理字。一物之所以稳定地呈现某种性质,即其内涵有某种必需依循的理路或曰秩序;而万物之运化所依循表现的秩序及理路,亦由其性质决定。朱子一再强调理一分殊,而且强调必需从分殊处入手来认识「理一」,就是这种「特殊」的世界观之表现。 这种万物一体同源的「性理」论,出于朱子的「整体观」,与现代本于「分析观」的物性或物理观点大为不同,而颇难为现代人所理解。这种观点所论的天命之性,或天地之性,是就天地万物整体的性理,尤其是就其根本、根源的性理而言。因此朱子也称此性理为太极,即所谓万物一太极。此根本之性必然遍布一切事物,故又称物物一太极。从这种观点出发,天与人同出一太极,所以分享同一种道理。宇宙的秩序与人间的秩序同源同体,不好说谁反映了谁,反而是永远互相映照。 从分析观点所认识的事物之性质,强调每一事物自有其特质与运作的逻辑。然而从整体观出发所认识的性理论,所看重的是如何从分别的事物中去认识到那根源性且遍布一切的道理,即所谓一体同源之理。从分析观点来看,万物大为不同,人性与物性虽有类似处,但物类万殊,性质各异。对人有价值的,对其他生物未必有价值。但从整体观来看,万物之所以能生的道理在本源上是相同的,所以讲到究竟处是一个道理。同样地,从分析观点来看,天地自然的规律、身心性命的法则、伦理及政治社会的秩序各有各的逻辑,不可混为一谈。然而从朱子的整体性思维方式(holistic mode of thinking)来看,这一切在根本上都是一源且一体的。虽然是一体,不害其中有万殊。上述的各类秩序中,依然有其分别。同时认识其会通与分别,才是朱子理想中的世界秩序。 三、天道与政治社会思想 前节虽已指出在朱子的思想体系中,天与人或说自然与人文有一体同源的关系。然而面对现代学界所必然提出的种种质疑,我们仍然必需进一步回答究竟在朱子具体的政治与社会思想中,两者是如何结合的。尤其是必需说明,在所谓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中,对于天道的认识,是否其实是被有关人道的看法所主宰? 余先生在其名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曾指出: 宋代理学家是将「理一而分殊」当作人间秩序的最高构成原则而提出的。程颐首发此说于〈西铭〉和朱熹〈西铭解〉末段所做的推论便是明证。换句话说,张载和程、朱都事先构思了一个理想的人间秩序,然后才将这一构想提升为宇宙论或形上学的普遍命题。[18] 余先生并引用杨时、林粟、陆九韶等人对于〈西铭〉的批判,详细分析此文及理一分殊说的政治社会含义。[19]余先生的分析深入当时的历史情境,诚为他人所不及。对于理学家言行所具有的政治意涵之深切剖析,更是发人所未发。理一分殊及〈西铭〉代表了程朱一系的世界观,其中确实包含了他们最高的政治社会,或曰人间秩序理想。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有关政治社会理念的争论,应属正常。余先生所指出理学家极重视政治与人间秩序的种种现象都确实存在,然而理一分殊以及理学家「宇宙论或形上学的普遍命题」是否基本上是张载和程、朱所事先构思的人间秩序的反映呢?却似乎仍值得进一步的探究。 朱子论理一分殊时说到: 圣贤之言,夫子言「一贯」,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张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20] 认为张载所说的理一分殊即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意思。关于这个一贯的「理一」,《语类》记载: 或问「理一分殊」。曰:「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21] 指出这一贯之道本身不可言,只表现在分殊的万事万物之中。我们必须即此万殊中,认识此理一。理一分殊是对于这全体一贯道理之基本「组成方式」的形容。这一贯的道理遍布宇宙人生,无所不在,万物之理彼此映照,合而为一体,然而其中自有无限的差异与分别。此说固然反映了人间的秩序,也同时反映了天地万物之理: 问理与气。曰:「伊川说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箇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箇理。」[22] 大抵天人无间。如云『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于天』。圣人能全体得,所以参天地赞化育,只是有此理。[23] 在朱子看来,人生源于宇宙,其道理本来一贯,因此「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箇理」。所谓天理,就是「无所为而为」的自然之道。人生的自然与宇宙的自然,同属一个大自然,其中的道理必然相通。不仅是朱子,首倡理一分殊的小程子也笃信天人不二: 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圣人本天,释氏本心。[24] 或问:「介甫有言:『尽人道谓之仁。尽天道谓之圣』」。子曰:「言乎一事,必分为二,介甫之学也。道,一也。未有尽人而不尽天者也,以天人为二非道也。」[25] 明言天人不可二分。大道为一,兼包天人。不能尽天理,亦不能尽人道。圣人之作为均本乎天理自然。王安石的学问不能合天人,佛家的道理只本乎一心,都为程子所不取。换言之,理一分殊之说,也必须在天人合一、大道一贯的世界观中去理解。 从这种理一分殊的观点来看,一切的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虽属分殊,其实亦通于理一。而且舍弃实际政治社会以及人生点点滴滴的经营,亦别无他处可以寻觅那一贯的道理。所以朱子等理学家之经营「世务」,不但不与其对于一贯的理一之追求冲突,反而是其求道的必经之途。从这个意义来看,余先生在所大量发掘出来的理学家深入参与现实政治社会之改造与人间秩序之建立的「现象」,实为其思想体系中应有之义。[26]然而投身于实际政治社会的改造,并不就意谓着他们所思考的一切都环绕在「人间秩序」之上,或始终以其为第一序的问题。相反的,我们一再发现朱子习惯于从任何一件小事,无论其为人生界或自然界,连结到贯串宇宙人生的「理一」之上。他所要问的第一序的问题,与其说只是人间秩序的完成,不如说是包含了人间与宇宙秩序的「豁然贯通」之「理一」。这种从天地人物一切万殊中探索那一贯之道的思维方式,即其「格物致知」说的精义。[27]而其探索的方式,是无论所谓人文与自然,皆在探索之列。在朱子看来,不达于天道,实不足以解决人世的问题。他所编的《近思录》中特别选录了周濂溪《通书》中「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一条。[28]学圣人,就是学天道。朱子深切地相信一切人生的道理必须本于天道,合乎自然。人生虽为天道的重要部份,然而天道与自然则不限于人生。 以下我们将进一步检视以〈西铭〉为中心所呈现出来的张载及朱子的政治与社会思想。余先生强调〈西铭〉中所表现的宇宙秩序是人间秩序的反映,而且是家庭宗法秩序的扩大,这话确实有其道理。然而,反过来说,〈西铭〉中所呈现的道理,又何尝不是宇宙秩序的反映。换言之,传统的家庭宗法以及政治社会秩序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效法了天地自然的重要内涵。〈西铭〉原名〈订顽〉,是为《正蒙》〈乾称篇〉的一部分。《正蒙》十七篇,开宗数篇均畅论天道,其后才及于人事。〈乾称篇〉为第十七篇,是为最后一篇。我们从文章的顺序,也可以推见张载当初如何看待天道与人事的关系。张载的入室弟子范育在为《正蒙》作序时说: 浮屠以心爲法,以空爲真,故正蒙辟之以天理之大,又曰:「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老子以无爲爲道,故正蒙辟之曰:「不有两则无一。」至于谈死生之际,曰「轮转不息,能脱是者则无生灭」,或曰「久生不死」,故正蒙辟之曰:「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爲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虚。」夫爲是言者,岂得已哉![29] 指出此书阐明「天理之大」、有无通一、「虚空即气」以及万物之聚散等天道的基本原理,其基本目标在驳斥佛、道两家相关的说法。换言之,《正蒙》一书实以阐明天道,建立合宜的世界秩序为第一义。对于宋代的理学家而言,佛、老的宇宙及世界观,既与他们观察天地之所得不合,更与儒家传统的人生态度及社会伦理格格不入。所以他们要本于《易经》,建立一套合于天道及儒家伦理的宇宙及世界观。佛家的空义及道家的无为义,在他们来看,都不能代表这世界最高的「道」。而学者若于此道体本源处认识稍有偏差,其所产生的后果将极为巨大。所以他们必需对于这最高的道理,作最深刻细腻的研究,企图使其丝毫没有任何误差。这也就是宋儒对于「道体」的问题之所以如此「讲究」,所谓「牛毛茧丝」无所不辨的根本原因。既然如此,他们所讨论的天道性命之微言,当然会对于他们的政治社会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正蒙》一书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张载透过此书,建立了一个贯通宇宙、身心性命、伦理及政治社会秩序的大体系。而其思维方式并不单从任何一方面出发,而是通观全体。从张载与宋儒万物一体的思想来看,人道亦为天道的一部分。当张载论天道时,他其实同时在通观天地自然、身心性命、社会伦理、政治经济与古今事变,而企图找出其中「一以贯之」的道理。天道与人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交织影响,而不能说某方面主宰了另一方面。 《正蒙》始于〈太和篇〉,所发挥的主要是易经的天道;该书终于〈乾称篇〉,「乾称」一词源于《易‧说卦》,所说的仍然是《易经》的思想。大《易》言天道而通于人事,论人事而合于天道,首重「天人合一」之义。〈正蒙‧诚明篇〉说:「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以尽明。」[30]指出人心人事要与天道合的思想。〈乾称篇〉则说: 以万物本一,故一能合异;以其能合异,故谓之感;若非有异则无合。天性,乾坤、阴阳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万物,所受虽不同,皆无须臾之不感,所谓性即天道也。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体。在天在人,其究一也。[31] 提出「万物本一」的思想。「天地生万物」,万物虽不同,然而彼此却都能互相作用感应,这显示出万物同出一源,本来为一物、一气的关系。在张载看来,设若二物出于绝异的根元,则彼此之间应互不相涉;能互相影响感应,就表示其中相通。万物所赋之「性」,其实都从「天道」来。无论「在天在人」,究竟的道理只是一个。然而万物毕竟「有异」,否则亦无所谓合而为一。这种思想,正是程、朱所谓的「理一分殊」,而其思路显然不限于「人间秩序」的反映。以上所述,是〈西铭〉一篇最切近的思想背景。〈西铭〉一文言简而意深,我们必需将他放入上述的脉络中来理解,才能深入其内涵。 〈西铭〉以「乾称父,坤称母」作始。[32]这种以天地类比作父母的思想在历史上远有所承。「乾称父,坤称母」一句出自《易‧说卦》:「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说卦〉在此句之下接着说:「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这段话所显示的乾坤之义,实远超过人间秩序或其反映,而表现为古人对于遍布于万物万事,跨越了天地人三方面的世界基本原理之探索。这种探索的性质,如之前所分析,表现出万物一体与「整体观」的特质。因此乃以类比的方式,将凡是具有刚健性质的事物,称之为乾,而将具有顺应性质的事物,称之为坤。宋代士人对于经书大抵皆能背诵,当张横渠与宋代士人读〈西铭〉时,他们思想中都有这个大背景在。当张载说「乾称父,坤称母」,他是以创化世界的乾坤之道比作父母。表面上看起来,他所相信的宇宙秩序确实反映了人间秩序;然而深一层看,他本来就认为这人间秩序是天地秩序(如日月、昼夜、雌雄)的一部份。朱子解释〈西铭〉时说道: 问西铭。曰:「更须子细看他说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则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气,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气;从这里便彻上彻下都即是一箇气,都透过了。」又曰:「『继之者善』便是公共底,『成之者性』便是自家得底。只是一箇道理,不道是这箇是,那箇不是。如水中鱼,肚中水便只是外面水。」[33] 这段话中以乾坤比作天地、男女、父母,贯穿了天地人事。朱子认为人从天地也从父母来,所以天地就是父母,父母也就是天地。背后生长发育人物的道理只是一个,也就是就是《易经》所说「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育万物的道理。宇宙如水,人如鱼,鱼在水中,内外皆水,所以人间的秩序其实就是宇宙的秩序,「只是一箇道理」。 如前说述,〈西铭〉原名〈订顽〉,为《正蒙‧乾称篇》中的一部分,所发挥的正是易经的义理。「乾称」二字出于〈说卦〉,〈说卦〉开头便说: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这里所表现的易道显然是一种包含了神明、天地、一切阴阳变化与人伦道德的世界秩序。朱子说这段话:「兼三才而两之,总言六画」。[34]《易经》与宋人所讲的道理或曰世界秩序,一直是兼天地人三才而立言。三才,乃至一切事物,又都可以各分动静刚柔的两个层面,亦即分阴分阳,所以「六位而成章」。这样的思想,固然反映了人间的秩序,但是却不能说「张载和程、朱都事先构思了一个理想的人间秩序,然后才将这一构想提升为宇宙论或形上学的普遍命题」。 〈西铭〉紧接着「乾称父,坤称母」说「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从《易》学上来说,《易‧说卦》在「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后立刻说:「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所谓「乾坤六子」。换言之,当张载说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时,他心中有我的生命来自于乾坤阴阳相揉,实乃天地之子,而与天地为一体的思想。「天地之塞,吾其体。」是说我的身体得自于天地之气。「天地之帅,吾其性。」是说我的性情得自于天地之所趋向。从这种思维出发,假以修养,此身心可与天地合一。相较于超越的上帝创造人,人永远不能与神合一且必须听命于神的犹太─基督教思想,张载的西铭所呈现的基本上是一种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想。也只有在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背景上,人的修为才会往「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的方向发展。这种思想若只说他反映了人间秩序,实在太忽略了其所从出的儒学大背景,亦忽略了「天道」在宋人思想中的重要性。充其所至,当人的修养与精神境界提升,超越了小我的各种限制,心量日益广大,充其所至,可以感受到天地与我为一体,天地所至皆等于我的身体。如《孟子.公孙丑上》篇所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35]从修养上来说,这是一种非常高的精神境界。 深一层看,张载的思维,还包含了宋人「生命化」的宇宙观。朱子曰:「西铭一篇,正在『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两句上」。[36]感受并认为天地与我同体,是张载与朱子所体认的世界观之基本特质。世界既与我同体,则世界上一切事物不仅与我相关,且为我生命的一部份。世界运化的道理与我的身体运化的道理,同为一个道理。在宋人来看,这都是阴阳五行。人的生老病死以及朝代的盛衰兴亡,如天地的春夏秋冬;人的作息,必须依照昼夜或曰日月的运行;人体分男女,本身就是一阴一阳。《正蒙‧太和篇》阐释「一阴一阳」的道理时说:「画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画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气易,犹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梦,百感纷纭,对寤而言,一身之昼夜也;气交爲春,万物糅错,对秋而言,天之画夜也。」[37]这里所显示的道理或秩序,显然不能只用「人间秩序」来形容,而必须扩大到包含阴阳五行、身心性命的「世界秩序」。更进一步分析,在古人来说,所谓人间的伦理秩序,也必须源本于人的身心性命,而合乎宇宙的秩序。在朱子与张载的思想中,宇宙、国、家与我身好比四个同心的圆,具有一致的基本原理且层层相涵。其中的道理只能说是互相映照,一气相通,却不能说是谁决定了谁。人生努力的方向在于推扩我的心量,使我能照顾关怀更多的人与物,极其所至,乃与天地同体。然而人毕竟有此身与小我的限制,所以道理虽然只是一个,行为上却只能循着修齐治平的道路,一层一层地向外推扩。 宇宙、国、家与此身既然分享相同一的道理,在构造上也有类似之处。〈西铭〉以天地比父母,以天子比父母的宗子,以天下人为我的同胞,万物为我的同类。推「爱亲」、「事亲」之心于爱国、爱天下人与事君。这是典型的化家为国,乃至化家为宇宙的思想。如此说来,身、家、国、天下皆为一体,又为一层层扩大的同心圆。家人与我一体,处处血肉相关。而天下及天地万物与我的关系,则好比扩大的家庭,亦为扩大的「身体」。这种构造固然反映了所谓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人间秩序,也表现了扩充后的身体与心灵。然而真正贯串其间的,与其说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人间秩序,不如说是一体之仁。而此一体之仁的背后,则是以天地之仁德为中心,「理一而分殊」的世界观。朱子说: 西铭大纲是理一而分自尔殊。然有二说: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别;自万殊观之,其中亦自有分别。不可认是一理了,只滚做一看,这里各自有等级差别。且如人之一家,自有等级之别。所以乾则称父,坤则称母,不可弃了自家父母,却把乾坤做自家父母看。且如「民吾同胞」,与自家兄弟同胞,又自别。龟山疑其兼爱,想亦未深晓西铭之意。西铭一篇,正在「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两句上。[38] 又说: 「他不是说孝,是将孝来形容这仁;事亲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样子。人且逐日自把身心来体察一遍,便见得吾身便是天地之塞,吾性便是天地之帅;许多人物生于天地之间,同此一气,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党与。[39] 我的身躯与天下人与物同气,我的心灵与天下人与物性情,我既感天下一切的人物与我同体同性情,乃产生有痛养相关的一体之感。这贯串其间的,是所谓一体之仁。天下万物,随其与我的亲疏远近不同,而有不同的对待,这就是理一分殊。《朱子语类》载: 因问:「如先生后论云:『推亲亲之恩以示无我之公,因事亲之诚以明事天之实。』看此二句,足以包括西铭一篇之统体,可见得『理一分殊』处分晓。」曰:「然。」[40] 这「推亲亲之恩」与「事亲」的主体,是具有一体之仁的我的生命。若无此主体,则一切皆无。所以与其说朱子及张载的世界观是「人间秩序」的反射,不如说它源于那一体仁之理一,而随其与我关系的「等级差别」表现出万殊面貌的世界秩序。〈西铭〉所要追求的,与其说是某种固定的人间秩序,还不如说是那种「民胞物与」的胸怀。只要有此胸怀,就能致力于建构理想的人间与世界秩序。这种以一体之仁与理一分殊为中心的世界观,源自理学家对于身心性命的探讨,也来自于他们对于天道的长期体会。这些探讨与体会固然与人间秩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却不能化约为人间秩序的投射。简单地说,若无以家庭宗法为中心的人间伦理,固然不可能产生以〈西铭〉为中心的思想;然而若无张、程、朱子等人对于「一贯之道」、「法天」、「一体之仁」、「无我」等以人合天,大其心胸的追求,也不可能产生如此恢弘的思想与无私的感情。 四、内化的超越 前述朱子的一贯之道与理一分殊的思想,其实源于中国古代的「此世一元观」。宋人不谈超越的造物主或创世神话,而认此天地自然为真实,并相信其中的一切同出于一源且同具一种道理。[41]既然不论是否别有超越的根源,于是全心经营此世,并以此世的存在为真实的代表。从西方现代哲学来看,这是一种「存在先于本质」(existence prior to essence)的思想;或更正确的说,这是一种「即存在即本质」的思想。既然是「即存在即本质」,所以「理一」不可离天地万物而别寻,只能「分殊」地显现于万事万物之中: 「如这众人,只是一箇道理,有张三,有李四;李四不可为张三,张三不可为李四。如阴阳,西铭言理一分殊,亦是如此。」又曰:「分得愈见不同,愈见得理大。」[42] 所有的分歧,都有他的道理。而且是「分得愈见不同,愈见得理大。」也就是说那终极、根本与至高的道理,只内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离此天地人物的繁变,并无他处可寻一超越至高的道。世界的伟大,正表现在他的丰富性上。这种思想,既不离开现世以追求终极的超越,也不拘限于现世的生活或价值之中,而要追求那含容一切的理一或曰大道。这样的思想,我们无以名之,只好称之为「内化的超越」秩序观。[43] 「内化的超越」思想及「此世一元」的世界观之最大特质,就是他们所强调世界的「一体不可分性」。在朱子来看,要包含此处处相关相应,一体不可分的世界,才是道理的全体与真实。为了要形容这处处不同,却又一体不可分的世界,他所用的语言乃与本于「分析观点」建立的现代语言大为不同: 问:「『理性命』章注云:『自其本而之末,则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故万物各有一太极。』如此,则是太极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44] 正如之前的分析,朱子认为天地万物的道理只能是一个,所以万物莫不源于此理。他以「太极」或「月」来形容此抽象的道理之全体。万物同出于此一,所以「自各全具一太极」。然而看单一事物,却又不足以认识此理一,而必需就天地万物的繁变去认识那一贯之道,由此而有朱子的格物致知说。他一再强调离开分殊或万物存在之实,别无他处可寻此抽象的一。却又时时提醒人不能忘却一切的事物本为一理。这种以此世为中心的世界观,合一与多,超越与实存为一,是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最大特质。所谓「理一分殊」说,最重要的是表现天地万物的「一体不可分性」,所以程朱之学乃以强调「一体不可分性」的〈西铭〉为其世界秩序观的代表。既然他所强调的是天地万物的一体不可分性,其中所言的道理并不分天道或人事,反而强调天道与人事的合一。这种天道与人事合一的思想,其实是宋代理学家共同的信念。此天道与人事合一,并不是用形上宇宙观去规范人生,也不是直接将人生观投射到形上宇宙观上,而是天人之间不断的交流融合。[45] 这种世界观与思维方式,既不会将「人间秩序」作为第一序以决定第二序的所谓宇宙形上秩序,也不会用一个超越的「自然法」或「道体」反过来决定人间与世界的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丸山真男、部分新儒家以及杨儒宾先生的说法,确实颇有值得商榷之处。丸山真男认为朱子的社会伦理思想奠定于其自然秩序或自然法的思想,已如前述。部分新儒家高扬超越、先验、绝对的道体,以其为万事万物之极则的思想,则已有余英时先生多次为文加以批评。[46]而杨儒宾先生对于朱子的诠释,也同样遭受到余先生类似的质疑。杨儒宾先生的思想取向是否可以归为新儒家,并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然而他的说法之所以引起余先生类似的质疑,似乎也确实有其原因。 杨先生并不认为理学的「理」世界或「形上」事业可以离开「气」或「形下」的世界来谈,而且相当强调体用与理气不可分离。[47]从这一点出发,他对理学家的一些解释,将是恰当的。然而他同时说:「他们(理学家)毋宁认为源头的理世界是种绝对的真实。它会安顿政治秩序,会安顿天体秩序,会安顿世界(所谓枯槁有性),甚至会安顿鬼神的世界。」[48]他提出「(理学家)工夫论的目的几乎都是要对先验的道体、性体之类的概念有一比感官经验还真实的体验。……这样的经验大概就是宗教经验中震撼力最强的冥契经验。」[49]杨先生并认为这些理学家具有宗教性格,其「终极关怀」独立于政治秩序之外,所以「当余先生将理学家定位为政治性格的儒者,他们以安定政治秩序为终极的意义时,他无意中摧毁了理学家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亦即摧毁了理学家辛苦建立起来的绝对性、普遍性的道德价值」。[50]他并总结地说:「传统所侧重的那种先天的、普遍的、绝对的天理(太极、道、良知)观所涵盖的层面,『政治秩序』的理论架构却无法讲的通。」[51]这些说法,就不免引起余先生的强力批判了。余先生坚决认为从「理学家作为一整体和理学家作为一士大夫集体」的层次来看,其「终极关怀」绝不「仅在于个人体证与讲论形而上的『太极』或『天理』」[52]而杨先生前述有关「先验的道体、性体」、「绝对的真实」、「绝对性、普遍性的道德价值」这些话,在余先生看来,只能是杨先生个人或「理学大论述者」的信仰。绝非历史上理学家的真相。[53] 纵观这两方面的辩论,我们可以发现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所谓「超越、先验的道体」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杨先生倾向于认为理学家通过宗教性的冥契经验而认识到的所谓超越、先验的道体;这样的体验是其价值世界的核心,不能窄化成现实政治性的追求。余先生则强调历史上的理学家始终未曾忘却在现实世界建立「人间秩序」的终极目标,至于个人是否有神秘体验而进入「永恒的精神实体」,既不可知,更不可能根据个人的神秘体验就建立「绝对性、普遍性的道德价值」。[54]对于同样一群理学家,在解释上竟产生如此激烈的对立,不能不说一贯的道(理一)与分殊的现实世界之关系似乎始终未曾厘清。 至少对于朱子而言,理一非超越独存而就在分殊之中,所以不能离开实存的万事万物去认识。朱子强调:「为学之道无他,只是要理会得目前许多道理。」[55]至于代表他为学方法的《大学‧格物补传》,也绝无宗教上「冥契主义」的倾向。这理一既然散在万事万物之中,且不能离开事物(气质)而独立存在,自然不是「先天的、普遍的、绝对的」。因此也必须要穷究天下事理才能豁然贯通。朱子成日孜孜为学,这样的学术性格,与宗教家并不相类。因此,高悬一超越而绝对真实的理世界,以其为朱子为学的终极目标,确实绝非朱子学的真相。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若不将宇宙秩序、身心性命道理、经世济民的大业、伦理的秩序做整体且有机的结合,并进而深入探索「理一」为何物,恐怕也未能充分显示出朱子思想的丰富性。朱子思想的精义,正在于打通天人内外以及超越与实存之区隔。他既然认为万物一体且「天人一理」,他所研究的一切事物,无论其为人间或自然,其实在分殊中都见会通。从现代学术分类来看,政治与宗教、自然与人文似乎分属于两个很不同的领域,然而从「天人合一」以及「内化的超越」之观点来看,这些都是学问中同时应有之义。无论朱子的学术及思想体系是否能够成立,至少对于他而言,政治、伦理、身心性命、宇宙、道体、眼前的一草一木,都是相通的事物。他的思维自由地出入这些领域,并用一生的努力企图将他们融合成一体。我们并不需要勉强将其思想的某些部分当作第一序,某些当作第二序。高扬超越的「绝对真实」,的确会太将朱子的思想「哲学化」并「宗教化」,而严重改易他的真实面目。将实际的「人间秩序」当成一切的出发点,虽然较能够贴近他们实际的历史作为,却未能充分说明他们对贯通天人的「理一」之追求。唯有见其超越的追求于实际的历史作为,得理一于分殊的事象,才能够更完整地呈现朱子学思的面貌。 结论 「天人合一」与「万物一体」是朱子的世界秩序观的一项基本构成原则。在这个原则中,人文被视为天地自然中的一部份,所以人道或曰人间秩序的完成,预设着必须合乎天道。程子说:「未有尽人而不尽天者也」,朱子则认为「天人一理」。程朱一派对人生道理与人间秩序的看法,离不开他们对于天地自然之理的观察。然而反过来说,正因为他们视人生为自然界不可分割的关键部分,所以他们对于天道的认识,也不离开那最切近也最容易观察体认的人生之道。在朱子的世界秩序观中,宇宙自然、身心性命、家庭伦理及政治社会的道理打成了一片。我们从他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字〈格物补传〉来看,他织成其思想体系的方式,是无分天人、内外而一体浑融的。这是一种认为一切事物在根本上不能分割的「整体观」思维方式,而与其「万物一体」且「生命化」的世界观密切呼应。在这样的世界观与思维方式之中,人间秩序与天道必然密切地交织相融。投入政治及社会的建设不仅对人有意义,并且同时具有「宇宙性」的价值,所以乃有理学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思想。 从现代的分类观点来看,朱子的思想经常跳跃于不同的「现代领域」之中,而其论述往往没有清楚的「逻辑」线索。然而从「万物一体」的生命化观点来看,各种不同「领域」的事物本来息息相关,不能严格地判分。形成一件事物的原因是多重多维的,而不能从单一、线性的逻辑线索(linear causality)来看。植根于线性因果观的的第一序或第二序的发生学问题,在「万物一体」的世界观中通常并不那么重要,至少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因为任何单一的事物,在这样的世界观中,都是多样事物交织而成。人间的秩序,自然也不例外。 然而这不是说朱子的思想一片浑沌而不重视事物的分殊。相反的,朱子建构他的世界秩序观另外一项基本原则正是高度重视事物的分别性。他对于万事万物的分类方式及其所使用的语言,虽与现代人颇有不同,却自有其丰富的意涵。他强调离开具体、个别的事物之理,别无所谓理一可言。一切的分别,虽统一于「理一」,然而正是因为有种种的分殊,才见得理一的丰富与伟大。朱子「理一分殊」的思想,同时形容了这个世界的丰富性与统一性,而成为他世界秩序观的另外一个构成原则。 从「理一分殊」的构成原则来看,现实政治社会的种种属于分殊,然而其道理均通于理一。朱子强调理一必然在分殊中见,所以从事现实政治社会的工作,不仅不妨害他对于大道的追求,反而是其中应有之义。既然是从分殊当中去认识理一,所以朱子等理学家经常会就具体的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发出一番深刻的义理,而且他们平日所谈的「玄言」中通常也都有深刻的政治社会意涵。整体来看,他们的思想一方面时时反映出他们爱家爱国,建立「人间秩序」的追求,一方面同时表现出追求「理一」,以合乎天道并建立「世界秩序」的胸怀。这种学术及思想性格,继承了「志于道」与「仁民爱物」的儒学传统。不空谈「一贯之道」,而要在实践中完成成己成物的目标。而于此同时,他们也成功地回应了佛教与老庄在天道性命之学上的挑战,提出了一套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宏伟体系。「天人兼尽」,是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是他们的人生目标。 注释: [1]「世界秩序」一词,对于现代读者而言,多半会想到world order,意即世界政治的架构性秩序。然而本文所谓的「世界」取其中文原意,包含此有限时空中的一切,不专指世界政治而言。至于本文中所用「秩序」一词,取义亦与英文order有所不同,详参下文。 [2]杨儒宾,〈如果再回转一次「哥白尼的回转」──读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当代》195期,2003年11月号。 [3]刘述先,〈评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九州学林》第1卷第2期,2003年冬季号。 [4]参见葛兆光,〈拆了门槛便无内无外:在政治、思想与社会史之间──读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及相关评论〉,《当代》198期,2004年2月号。陈来,〈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述评〉,《二十一世纪》第79期,2003年10月号。葛兆光则认为双方的争议,有过份强调内外、主客之分的嫌疑。这种二分法其实并不必要。此说甚有见地。陈文则着重于介绍余先生开拓新视野的贡献。 [5]余先生对于杨、刘两位先生的质疑,分别提出了答辩。对杨先生的文章与论点,批判尤多,认为杨先生误读了他的基本观点,并犯了不少史实方面及解读原典的错误。参见:余英时,〈我摧毁了朱熹的价值世界吗?──答杨儒宾先生〉,《当代》197期,2004年1月号;余英时,〈「抽离」、「回转」与「内圣外王」──答刘述先先生〉,《九州学林》第2卷第1期,2004年春季号。余英时,〈简单的说明〉,《当代》199期,2004年3月号。杨先生则一方面接受了部分余先生的指正,一方面对其基本论点做了更进一步的说明。(杨儒宾,〈我们需要更多典范的转移──敬答余英时先生〉,《当代》198期,2004年2月号。) [6]相关论证请参见拙作〈朱子世界观的基本特质〉,「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大学,民93.3.14-15) [7]《书‧尧典》「寅宾出日,平秩东作」。「平秩」所辨为日月始升的秩序。(曾运乾,《尚书正读》[台北:联贯,民60],5-6)。《书‧舜典》「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注曰:「秩,序;宗,尊也。主郊庙之官。」疏曰:「主郊庙之官,掌序鬼神尊卑,故以秩宗为名」。(《十三经注疏》[一八一五年阮元刻本)],《尚书‧舜典》,卷三,页二十五。)郊庙之官,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礼」,排序其尊卑,必须兼通天道人事。(同前) [8]另有许耀明,〈朱熹的理学与法律思想——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正当性的探讨〉(台北:台湾大学法律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9)一文。该文尚属初探,可商榷处颇多。 [9]《朱子语类》(台北:正中,民59),卷十七,页十四~十五。 [10]《语类》,卷十七,页十四。 [11]这背后实表现出一种机体化(organismic)或曰「生命化」的世界观,亦即认为宇宙与人具有类似的基本性质,其运化的基本原理与人及各种生命一致。换言之,是将宇宙看成一个广义的大生命,而将人看成一个小宇宙。(参见拙着:〈朱子世界观的基本特质〉) [12]《语类》,卷二十四,页二十六。。 [13]《语类》,卷四,页九。 [14]《朱文公文集》(台北:台湾商务,民69)卷七十,〈读大纪〉,页五。 [15]朱熹,《四书集注‧大学》(台北:艺文,民67),页六。 [16]《语类》,卷六十二,页十。 [17]《语类》,卷五十九,页二~三。 [18]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台北:允晨,民92),202。余先生书中类似的说法不少,参见同书170,219,242,251。另外在〈我摧毁了朱熹的价值世界吗?──答杨儒宾先生〉,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57。 [19]同上,201-218。 [20]《语类》,卷二十七,页二十。 [21]《语类》,卷二十七,页七。 [22]《语类》,卷一,页一。 [23]《语类》,卷八十七,页十六。 [24]程颐,《二程遗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十一下,页二。 [25]《二程粹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上,页二。 [26]详参《朱熹的历史世界》,是为余先生此书的首要论旨。 [27]参见朱熹,《四书集注‧大学》,页六。 [28]朱熹,《近思录》(台北:台湾商务,民65),卷二,29。 [29]张载,《正蒙》(台北:里仁,民70),范育序,5。 [30]〈正蒙‧诚明篇〉,20。 [31]〈正蒙‧乾称篇〉,63。 [32]〈西铭〉见〈正蒙‧乾称篇〉,62~63。 [33]《语类》,卷九十八,页十五~十六。 [34]朱熹,《周易本义》(北京:北京大学,1992),169。 [35]朱熹,《孟子集注‧公孙丑上》,页七。 [36]《语类》,卷九十八,页十五。 [37]〈正蒙‧太和篇〉,9~10。 [38]《语类》,卷九十八,页十五。 [39]《语类》,卷九十八,页十七。 [40]《语类》,卷九十八,页十四。 [41]详参拙作,〈朱子的世界观之基本特质〉。 [42]《语类》,卷六,页三。 [43]学界早有关于传统儒学「内在超越」问题的讨论,可与此相参。然而各人对于何谓内在超越的理解与定义颇有不同。学界最早提出此说者当推余英时先生,其贡献不可磨灭。(参见: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台北:时报文化,民73)];辛华,任菁编,《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近儒学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1992)然而余先生对于儒学,尤其是其中涉及天道的看法,与本文所论实有所不同。另外汤一介先生曾为此问题出过《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一书。汤先生认为在程朱的思想中:「天理是客观的精神,心性是主观的精神,客观的精神与主观的精神只是一个内在的超越精神。」(汤一介,〈内在超越问题〉,哲学在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这与本文所强调「理一分殊」、「天人合一」式的「内化超越」又颇为不同。为避免混淆,本文特别用了「内化的超越」一词。「内在超越」是相对于基督教与理性主义的「外在超越」传统而言。「内化的超越」则兼指「理一」即在「分殊」之中,此超越之道,不在外求,而已内化于事事物物当行之理之中。张灏先生也曾用过「内化超越」一词。他说:「天人合一的思想则以内化超越为前提,蕴含了权威二元化的激烈批判意识。」(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40)又说:「内化道德以内化超越为前提,内化超越则以‘天人合一’的观念出现。」(〈儒家的超越意识与批判意识〉,杜维明主编,《儒家发展的宏观透视》﹝台北:正中书局,1997﹞,285)其强调天人合一的观点与本文相通。然而张先生偏重「内化道德」,并认为从朱子相信「礼制也是植基于超越的天」这一点,可以看出「一种变相的宇宙神话仍然盘据在朱子的思想里。」(《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45-47)仍然从自然与人文二分的现代观点来批判朱子的思想。笔者则认为朱子「整体观」的思维方式,必然企图将宇宙的道理与人生的道理融合为一。其思想似乎不限于「内化道德」,也不宜简单地用「宇宙神话」来批判他所建立的世界秩序中「上合天道」那一面。 [44]《语类》,卷九十四,页三十五。 [45]乾隆皇帝题「长春书屋」诗句:「人心小天地,闻之宋儒语。一气总涵春,所以首四序。」也充分反映了这种思想。 [46]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以及《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民80) [47]杨儒宾,135-136。 [48]同上,136-137。 [49]同上,137。杨先生在讨论这类体验时,较多引用陆王一派,尤其像杨慈湖一类的人物。对于朱子本人是否真有「冥契」的经验,却未深入讨论。 [50]同上,138。 [51]同上,139。 [52]余英时,〈我摧毁了朱熹的价值世界吗?──答杨儒宾先生〉,55。 [53]同上,69,72。 [54]同上,67,71-72。 [55]《语类》,卷一百一十八,页十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