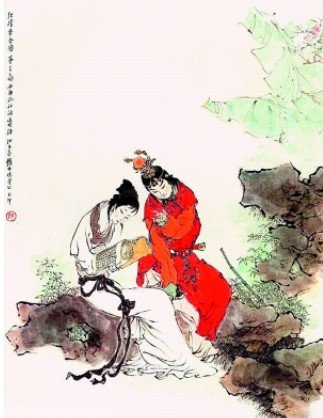 红楼梦研究一度被推广为一项“全民运动”,而本世纪以来,热闹的红学似乎红得有些尴尬。(图片来自《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 虽然位列20世纪中国的三大显学,20世纪上半叶,《红楼梦》研究尚不脱知识阶层的逸趣雅好或智力游戏,却因其中一位爱好者毛泽东,在中国大陆被推广普及为全民运动。此后很长时间里,中国红学研究的学术交锋里,或显或隐流露着政治较量的兵刃气。 “文革”之后,红学在索隐、考据、阶级论的道路外,重新回归小说本身。在知识仍带有光环的时代里,红学是专家的,也是普罗大众的,《红楼梦学刊》作为一本学术刊物,第一辑发行达8.5万册。同时,学界亦积极向大众提供文化产品,1987年的电视剧《红楼梦》受当时红学潮流影响,结局设置以探佚结果取代了流传更广的后四十回,虽然对此改编红学家内部犹有争议,老百姓却只管对着电视机唏嘘垂泪。 但这个世纪,红学开始红得尴尬。索隐派借助强势媒体“卷土重来”,民间研究者、爱好者借网络展开言说空间,红学界作为共同的对立面,在双方的相互印证中,被树为一个压制异见的强势组织。同时,在学术生产后劲不足、缺乏有效诉诸大众的文化产品、应对时代转型的反应迟钝,以及一个学术团体面对权力资本的微妙处境的共同作用下,以中国红楼梦学会为代表的红学研究界的公众形象一落千丈。 这种遭遇可能只是当下学术界困境的一个投影,但红学因其红极一时,成为最容易被捕捉的案例。起朱楼的盛况依稀,宴宾客的场面犹在,下一步哪怕楼塌了,也不失为传统悲剧收梢;但在这个时代,还可能出现更残忍的结局:或漠不关心,或当个笑话。 89岁的冯其庸坐在主席台上,身边是86岁的李希凡,以及被李希凡称作“小胡”的71岁的胡德平。这是11月23日“纪念伟大作家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大会暨学术讨论会”的开幕式,这位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声音洪亮思路清晰地作了10分钟的发言,在回顾了20世纪红学发展,表达了新世纪的新期待后,他略作停顿,全场掌声适时响起,然而冯其庸接着说:“但扩展思路、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不是让大家去想入非非,学术研究要认真踏实、实事求是。” 1954年向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发难而受到毛泽东肯定的李希凡,批评了目前存在的“秦学”(刘心武对《红楼梦》的猜谜式研究)、否认曹雪芹著书以及彻底否定程高本的观点:“学术需要百家争鸣,以便让我们更好地接受《红楼梦》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但争鸣不是奇谈怪论,是要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 用自己的话说,冯其庸已经“看不清,对着耳朵说才能听到;李希凡同志比我好一些,他的听力还行”,但这些年的红学聚讼,他们看来还是了然于心,并有所回应。然而这一场景,印证的更像是红学研究在当下的传播困境:在场的都是“自己人”,与批驳对象没有直接对话机会,意见往往只能由媒体一鳞半爪地转达。最残忍的是,连刘心武都见好就收地不提红学会很多年,红学界的老先生们却还是习惯性地摆出了对阵的架势。对他们来说,这也许是对待学术论争的应有态度,但在习惯了一切都以信息乃至以景观观之的当代观众,看上去也许更像一群白头老者在“闲坐说玄宗”。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