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学如何走向开放与自由 作者:刘东(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副院长) 来源:原载于《斯文:张栻、儒学与家国建构》,周景耀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5月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五月十五日丁卯 耶稣2017年6月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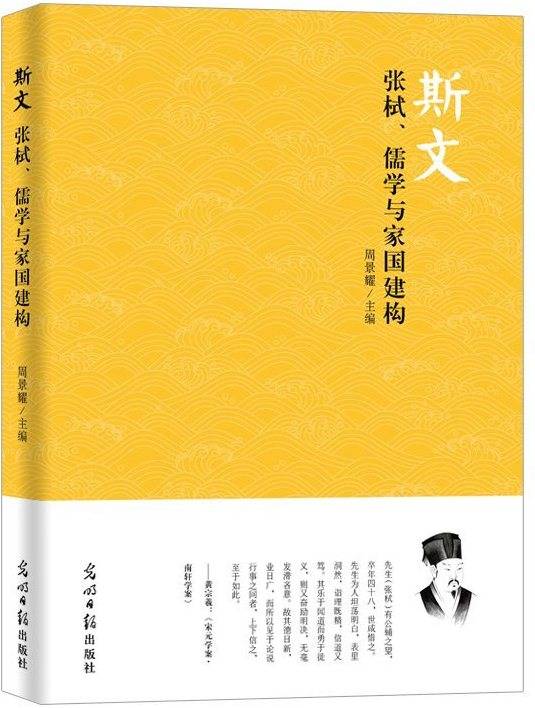 (一) 我们都知道,孔子曾经向着“德之不修”和“学之不讲”的状况,表达出特别深切的忧虑。而如果再参照他那个年代“礼崩乐坏”的现实,我们就不难由此体会出,对于学术话语的“讲说”或“讲谈”,至少从孔子的角度来看,对于文化传统的传习与发展来说,具有相当关键的、乃至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因为,一旦这样的“讲说”或“讲谈”被冷落了下来,载有文化精义的经典就要被束之高阁了,而文化的内在运脉也便要渐渐式微了。 正因此,对于学术话语的这种持续“讲说”或“讲谈”,便应被视作支撑起一种文化传统的、须臾不可稍离的深层推力。更不要说,这种来自主体内倾的文化动力,对于由孔子所开出的这个文化类型而言,又具有远较其他文化更为重要的意义。 这是因为,此种文化的特点恰在于“无宗教而有道德”;也就是说,它决定性地舍弃了在它看来并不可靠的、至少也是属于未知的外在神学支点,转而去向更有把握体会到的、来自主体的仁爱之心去寻求支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曾这样来总结此种文化模式的独特贡献:“善于自我救度的、充满主动精神的人类,实则只需要一套教化伦理、提升人格的学术话语,去激发和修养社会成员的善良天性,就完全可能保证日常生活的道德判断,从而不仅维系住整个社会的纲常,而且保障人们去乐享自己的天年!”[i] 我们知道,到了两千多年以后,为了维持这种话语本身的生机,以保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状态,现代学者冯友兰又在他的《新理学》一书中,把儒家后学对于它的“讲说”或“讲谈”活动,区分成了“照着讲”和“接着讲”两种。而沿着他的这种思路和句式,我跟着又把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关系,发展到了再从“接着讲”到“对着讲”的关系。 ——回顾起来,我当时正在北大比较所工作,也就是说,当时我正集中关注着文明边界上的问题。所以,按照自己当时的心念,如果能把上述两组辩证关系再串联起来,那么,借助于这三种接续产生的、针对全部既有人类智慧种子的,既严肃又灵动的讲说态度,就有可能牵出一条足以把我们引领出“诸神之争”的红线。 正是为了克服片面囿于某一传统的“接着讲”,我们就必须把它进一步解放为“对着讲”!事实上,每天都摞向我们案头的西方学术译著,和林立于我们四壁书架上的中国古代典籍,已经非常鲜明和直观地提示着我们,如今不管谁想要“接着讲”,也至少要承袭着两种精神传统去开讲,——而且是两种经常在相互解构和解毒的传统! 由此很自然地,如果我们自信还并非只是在以西方传统或中国传统为业,而是在以思想本身为自己的事业,那么两种传统之间的“对着讲”,就无疑是一种更合理也更宽容的学术选择。[ii] 在那以后,我虽然又调到了清华国学院,工作的重心也随之有所调整,可自己在这方面的持续关注,却没有发生过丝毫的转移或变迁。毋宁说,我倒是发现了这种种从“照着讲”到“接着讲”再到“对着讲”的、越来越丰富和细腻的讲说方式,对于如何开展国学本身“讲说”或“讲谈”,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为了能充分展开这种想法,我又需要在开头的这一节里,先来讲清在这三种“讲说”方式之间,究竟是如何渐次升华和不可分割的。 首先应当看到,学者们所以会一再地提出和细化这类区分,而先从“照着讲”走到了“接着讲”,又从“接着讲”走到了“对着讲”,当然是因为大家都在具体“讲说”的过程中,不断意识到列在后面的那种“讲说”方式的必要性。——比如说,即使只打算去“照着讲”,实际也不会只是在老实巴交地照本宣科,而必须充分调动起阐释者的积极性,否则就什么想象力都发挥不出来,什么新意和创见都“讲说”不出来,从而也就势必要被后人所忽略或淘汰了。 正因为这样,正像伽达默尔早已向我们展示过的那样,在作为一种有机过程的“讲说”活动中,真正称得上卓有成效的“照着讲”,就只能是充满参与精神的“接着讲”,哪怕有人挑明了要严格地采用汉学(汉代之学)的方法。 进而言之,由于文化之间越来越密切的交流,已使得任何统绪都无法单独自闭,又使得任何想要在哪条单线内进行的“接着讲”,都会不自觉和程度不一地变成了“对着讲”。——比如,如果只看其表面的宣示,唐代韩愈口中的“道统”曾是何等的森严和排他,所谓“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iii],可在实际的文化操作中,等到这个“道统”在后世真被继承下来,获得了被称作宋代“道学”的精神后裔,却不仅没对佛老进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iv] 反而被后者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没有印度文化的传入与接受,其立论重心原在仁爱之心的儒家,顶多也只会以康德式的“主观的合目的性”,去虚拟地提出《易传》中的天地解释,以充当自家学说内核的、拉卡托斯意义上的“保护性假说”。而宋明理学的那些基本命题和图式,什么“格物/致知”,什么“主敬/主静”,什么“天理/人欲”,什么“道心/人心”,什么“天地之性/气质之性”,就不会照后来的样子被诱发出来。 ——尽管话说回来,又必须是沿着儒家学术的基本理路,和不失这种人生解决方案的基本特色,这类的诱发才会显出积极的效果;正因为这样,在先秦时代曾经看似平分秋色的“儒分为八”,也就不可能获得同样的思想史地位。 既然说到了这里,就不妨再跟着补充说明一句,人们以往在这方面,似乎未能以同等的注意力看到,理学家之所以能顺利汲取当时的“西学”(西域之学),则又是因为早在他们的时代之前,中原文化便已针对着外来的佛学话语,而长期采取了“对着讲”的文化策略,从而既逐渐化解了其外在性,又悄悄把它转化为可以优势互补的思想材料。 而这也就意味着,不光是在理学家那里,实则早从佛学刚刚传入开始,这种“对着讲”的过程就起始了。——这也就从另一个重要的角度,益发证明了我所提出的“对着讲”的普遍化和有效性。 更不要说,尽管在一方面,正如我以前已经指出过的,“冯先生当年想把‘接着讲’跟‘照着讲’划分开来,其本意无非是赋予后者以学术合法性,以便名正言顺地对经典进行创造性的发挥。——这样一来,如果他在‘贞元六书’中想要代圣人立言,就只需照顾这些言论是否贴合儒学的内在走向,而不必计较是否确有先贤的语录可供征引”[v] ,可在另一方面,这位自觉要来做个“宋学家”的现代学者,实则又在宋明理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揉进了西方哲学的要素,于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当年借以自况的这种“接着讲”,也就属于一种照顾面更广的“对着讲”了,也即又不光是在中印文化之间来“讲说”,还更是接续着中、西、印三种文化的统绪,来进行水乳交融的、你中有我的“讲说”。 出于同样的道理,现代中国著名的“新儒学三圣”,也即性格既鲜明、贡献亦突出的熊十力、梁漱溟和马一浮,这些学者从一个方面来说,当然也都是“接着”宋明理学来讲的,而且或许正因为此,他们才如此不约而同地,全都突显了自己的佛学渊源,而这自然就已经属于“对着讲”了;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所共同发出的学术话语,还又在同时回应着西学的强烈冲击,而或隐或现地回应着外部世界的挑战,——甚至,即使是在那些看似未涉西学的命题中,如果细绎其立意的初衷亦莫不如此,而这就更要属于自觉的“对着讲”了。 (二) 接下来要说的是,上一节文字中的这一番考察,又鉴于晚近以来急转直下的思想情势,而显出了更加要紧的方法论意义。 说实在的,如果我们的国学还像以往那样,既受到了普遍的忽视,又受到了普遍的蔑视,那么,尽管其中的问题仍很要命,却不会照现在的这个样子表现出来。然而,晚近以来的戏剧化变化却是,随着综合国力的戏剧性增长,我们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作为其内核的学术文化,也在对于“礼崩乐坏”的再次惊呼中,并且在作为一种西学的后殖民主义的强力助阵下,突然表现出了全面的复振之势。——而由此一来,作为沉重历史的某种惯性表现形式,长期受到文化激进主义熏陶的人们,就难免要生出嘀嘀咕咕的狐疑,误以为这只是在简单地走回到过去,和径直地恢复已被抛弃的传统,包括其中所有曾被认作“悖理”的东西。 要是果然这样的话,那么即使我本人也必须坦率地承认,别看它在表面上又被普遍追捧着,可国学却不啻陷进了另一种危机中;而且这种危机,也并不比国学当年被毁弃时更轻,因为这会使它的研究者太过飘飘然,再也意识不到一味抱残守缺的坏处,想不到再到交互文化的思想场域中去澡雪自己。——不过,也还有一种可能是,这类危机更多地只是出自“国学热”的批评者本身,因为只要是对照一下前文中的论述,大家也就不难发现,这些人的方法论仍嫌太过陈旧,以致还是把对于学术话语的当代“讲说”,只是狭隘地理解为“照着讲”,充其量也只是在“接着讲”。 不待言,正像我以往明确指出过的,休说只打算去“照着讲”了,就算只打算去“接着讲”,这样的文化诠释活动都显得狭隘,从而,它最终也只能把我们引领到“诸神之争”甚至“文明冲突”的沼泽地中: 以往那种仅限于某一脉络内部的“接着讲”,在显出相当的开放和灵活的同时,毕竟也还有其狭隘和独断的一面,——因为无论打算接续着何种精神传统来开讲,这样的主讲人都已先入为主地设定了,所有的真理都已穷尽于此一传统的基本取向,而后人与时俱进的诠释工作,哪怕再充满灵感和再富于创意,也不过是把真理从以往的隐性推演到应时的显性罢了。 受这类前定预设的无形制约,即使外来文化构成了某种刺激,也只能刺激得固有的文化更加强劲和周到。所以骨子里,在对于文明价值的此种本质主义的理解中,各文明的原教旨根本是老死不相往来的。而由此展现出来的世界图景,也就好比是存在着许多生存竞争的文化物种,它们尽管从未拒绝过相互撕咬和吞食,但这种彼此消化却很难有助于共同的进化,而只能表现为一场撕咬——猫若咬了狗一口就长出一块猫肉,狗若咬了猫一口就长出一块狗肉,直到文化食物链的哪一环被嘎然咬断为止。[vi] 然而,无论是当真想要这么做的人,还是亟欲批评这种做法的人,显然都没有能与时俱进地意识到,对于任何文化传统的言说环境,都已发生了根本不可逆转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的最大特点,就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学术性的话语言说,都只能发生在交互文化的大环境下。 ——缘此,正如我以往在论述梁启超时所指出的,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对于祖国文化的回望,其实并不像汉学家列文森所说的那样,只是反映了一种眷恋故土的顽固怀旧情感;恰恰相反,他当时实则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从更为广远的世界性的“大空间”来看,从各方水土中接引出来的各种殊别文化,都注定会使人类意识中的那个叠合部分受益。也正因此,梁启超才会在他这本意识大大超前的著作中,对于自己未来的运思进行了这样的筹划: 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vii] 更加“巧合”的是,基于前文中给出的方法反思,尽管我在北大比较所时并没有想到,然而照现在看来,实则在梁启超所筹划的这些运思步骤中,便已然不仅包涵了“照着讲”和“接着讲”,还其包涵了“对着讲”。由此可谓心同此理的是,原来在我目前任教的这个清华国学院,从来就有人在心怀远大地憧憬着,靠着这三种循序渐进的“讲说”或“讲谈”,或者说,循着自家文化本根的逐步扩张与生长,文明历史的过往进程不仅不会被戛然中断,而且其中各种智慧种子反倒会在交互的合力下,不断地发生碰撞、嫁接和交融和共生,并最终发扬光大为足以为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 无论如何,惟其有了这种延续中的上升,从地球各个角落中生长出来的智慧种子,才有可能同时去向某一个中心集聚,并最终在我们的哪一代后人的宽大头脑中,被决定性地熔铸为真正足以被普世所接受的“普适”精神。——不管这种辉煌的未来远景,只照眼下来看是怎样的模糊虚渺,然而也只有等到了那一天,才能最终化解掉“文明冲突”的内在根源,从而最终消除掉正要毁灭整个人类的心魔;而马克斯·韦伯所深刻刻画的、令人绝望的“诸神之争”,也才能真正转化为整个世界的“诸神之合”。 这当然是谁都愿意接受的前景。——不过,正是为了逐渐地走向这种前景,我在这里却要平衡地再度提醒:一方面理所当然的是,对于任何严肃的思想者来说,无论他最初出生于哪个具体的时空,他由此所属的那个特定思想场域,尽管会向他提供出阿基里斯般的力量,却不应构成他不可克服和摆脱的宿命;恰恰相反,他倒是正要借助于从“照着讲”到“接着讲”再到“对着讲”的学术言说,借助于不断拾级而上的、足以“一览众山小”的文化间性,而不断地攀越着文明的高度,和走向思想的合题。 然而,另一方面也需更加注意的是,即使是在这种交互文化的场域中,或者说,恰恰是为了稳健踏实地踏进这种场域,我们又必须不偏不倚地看到,一种入土很深和基础强固的、足以作为充沛泉源的文化本根,对于任何一位具体的历史主体而言,都仍然具有非常关键的、不可或缺的意义。 而这也就反过来意味着,即使是生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那种误以为自己可以不凭任何文化本根,便能游走和投机于各个文化场域之间的“国际人”,尽管可以自诩为“最超然”或“最先进”的,并且还往往会据此而轻视本国的国学,可在实际上,都不过是最没有力道和最缺乏理据的。——这样的人,除了要频频地返回本国来拾人牙慧之外,也就只能再到国外去进行有意无意地逢迎,以经过刻意掐头去尾的本土案例,去逢迎地验证那些由别人所创造的、似乎“必由一款会适合你”的“先进”理论。而由此一来,即使原本是在别家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智慧资源,一旦到了这些国际学术掮客口中,也就只能被变成唇齿之间的无根游谈了。 这些人彻底忘记了,那些被他们舞来弄去的“最先进”的理论,其本身也有一个生存和生长的特定语境,从而也必须如剑桥学派的“历史语境主义”所示,要自然而然地从本土的文化土壤中产生出来。——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一种可以不属于任何具体文化的理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并不存在的,正如一个可以不属于任何特定社群的个人,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不存在的。 这些人也彻底忘记了,任何一位具体的历史主体,只有基于他本身的文化语言,也只有基于他自己亲切的生活经验,才有可能对一个无所不包的文化语境,获得真正周全、鲜活而微妙的把握,而一旦丧失了这种全面的、涵泳其间的把握,那么,单靠对于某种外文材料的生吞活剥,他本人对于某种外缘文化的理解,也就只能是干巴巴的和教条式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就决不可忽视埃德蒙·柏克特别强调的那种“根植于一地”的人类情感,相反倒把它视作由此而去拓宽心胸的、必不可少的精神出发点。 这些人更是彻底忘记了,如果他们可以用如此轻慢的态度,来对待自己故国历史中的古人,那么,他们自己的后人也就有了同样的理由,来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曾经活在当下的自己,从而使得自己也同样变得什么都不是,并且终究把人类的历史糟蹋成一系列不相连的断点,变成永远在向外发散、而决不会集聚起来的一片空虚。——回顾起来,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以赛亚·伯林才令人印象深刻地讲述过:那位自以为已经充分“国际化”的、不再以犹太人自居的奥托·卡恩,曾经朝着纽约街头上的犹太教堂悔不当初地说:“我以前也曾在那里做过礼拜”;而既身为犹太人、又身为残疾人的著名发明家施泰因梅茨,则语气坚定地、毫无愧色地像他回敬:“而我以前却是个驼背!” 还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才在解说儒家有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时,指出了文化本根与人格成长之间的正比关系——“它不光是首尾相顾地指示了修身的目标,还又通过把人格境界的高度与个人认同的广度依次相连,而脚踏实地地规定了人格成长的确定意涵,以及推动这种成长的来自主体之间的道义力量。如果说,近代那种把全体同胞都视作黑暗势力的个人主义或唯我主义理念,其本身就是一种执迷的幻觉,那么,儒学所传播的却是另一种暗示:在这里,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为己之学和利他主义均已合而为一;从而,越是敞开心胸去拥抱更加广阔的天地,越是跟此身所属的社群息息相通,自我的主体性反而会越发强韧,个体的生命境界也就会呈显出一种同步的增长。”[viii] 说到这里,也就有必要再来回味一下。——前面在“照着讲”、“接着讲”和“对着讲”之间所做出的那些区分,毕竟都只是相对而言的,也就是说,它们毕竟都属于对于学术话语的同一个“讲说”过程,而且也只是在这类“讲说”的自我递进中,才逐渐从其内部分化和升华出来。正因为这样,如果前文中更多地是从解释学的角度,来阐明这种学术言说的“发散”一面,那么到了本节的结尾之处,则需要再从古典学的基本预设,来强调这种学术言说的“聚敛”一面。无论如何,惟其有了这种基于经典文本的、不可随心所欲的向心力,后人对于学术话语的“讲说”,才不会成为随风飘走的、断了线的风筝,而文化的统绪才有可能成为有机发展的线索。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我以前就已指出的那样,这三种层层递进、不断开敞的“讲说”态度,又表现为从来都不能彼此分离的:“正像‘接着讲’的态度从未把‘照着讲’简单撇弃一样,‘对着讲’的态度也不会把‘接着讲’简单撇弃,因为连‘照着讲’都不会的人当然就谈不上‘接着讲’,而连‘接着讲’都不会的人也同样谈不上‘对着讲’。”[ix] 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只有在一种小心翼翼的平衡中,才能确保既不会固步自封,也不致丧失自我。 (三) 我们沿着上述理路又不难推知,这条从“照着讲”到“接着讲”再到“对着讲”的阐释线索,决不会仅限于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讲说”或“讲谈”。从理论上讲,它肯定是具有着更加广泛而普遍的适用范围。——正因为这样,当我把以赛亚·伯林的思想过程,描述为下面这种开拓与延展时,我事实上也同样是在指,他是沿着从“照着讲”到“接着讲”再到“对着讲”的言说过程,而循序渐进地发展到了后来的立场: 跟那些把自由主义说成“规则之母”的意见相反,我个人反而倾向于认为,伯林思想进路的主要里程碑,反倒应当沿着这样的理路:跨文化→人类学→不可通约的多样性→选择的优先性→自由主义的宽容原则。说得更明确些,我个人反而倾向于认为,如果就其潜在的心理关联而言,所谓自由主义或政治自由主义——即使是部分的或不系统的自由主义——其实并不是伯林思想的起始之处,反而只是其意识的最终落脚之点。[x] 我当然知道,按照时下某种过于自信的观念,一旦说到了伯林的这个“最终落脚之点”,那么,正因为他曾经写过那本著名的《自由论》,也就差不多就等于是在走向“普世性”了。可我自己却不这么认为,因为在我看来,与其用哪个既成的现代政治哲学概念,无论它是否符合一时的潮流或时尚,来判定某种观念是否具有“普世性”,从而免不了要暗中裹挟了文化的偏见,还不如另创一套更加中性的术语,以此来涵盖交互文化的实际过程,以便更为客观地来审视各个文明的价值理念,是否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交流性言说,从而在一种水涨船高的铺垫中,逐渐走向真能被公共认同的“普适性”。 出于这种考虑,我要这里要再尝试提出的术语,就是一组可以称作“大空间”和“小空间”的概念。——而这也就意味着,在一方面,鉴于露丝·本尼迪克特和米利福德·格尔兹所提出的文化相对性,我们至少应当在进行文化对比时,慎用类似“普世性”这样的概念,可在另一方面,这种“退一步”而言的文化相对性,又不应当把我们拖入难以自拔的相对主义,因为我们总还可以在相对而言的意义上,借助于像“大空间”和“小空间”这样的概念,来历史性地描述不同的文化因其内在的特性,而在传播方面所展示出的优势或劣势,乃至在传播范围上所实际达到的广远或偏狭、普遍或逼仄。 早在二十年前,我就曾在退而认同“文化相对主义”的同时,又同时在上述的意义上,进而指出了这种立场的巨大缺陷,——而从现在的角度来回顾,我当时又要转而予以捍卫的,也正是同样属于自己的文化“大空间”: 扪心自省:尽管百余年来的中国现代史中的确充满了冲突与对抗——甚至可以说恰恰是由于有了这些冲突与对抗——我们中间究竟又有哪一位的人格不是被杂揉难分的多元文化因素滋养起来的?正因为这样,如果有人想要剥夺我们阅读康德、莎士比亚、威尔第和米开朗基罗的权利,那已经会跟想要抢走我们的苏东坡、王阳明、王羲之和吴道子一样令人痛惜;而再进一步说,如果有谁想要把我们对外来文化的醉心贬斥为“文化侵略”下的“亡国奴”心态,正好象有人曾经疑心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和格里格全都是莫扎特和贝多芬手下的“第五纵队”一样(我确曾读到过这种可笑的论调),那我们真可以把他看作是不折不扣的“迫害狂”患者了![xi] 那么,既然从这些人笔下流出的音乐已经传遍了全球,而且已经被形容为最“没有国界”的,为什么还不能把广受钟爱的莫扎特和贝多芬,索性就称为具有“普世性”的作曲家呢?——事实上,正是在这类以往特别容易滑过的地方,才显出了我这种“大空间”和“小空间”的理论,具有它特别谨慎和弹性的优点,因为惟其如此,我们才不致在所谓“普世”-“殊别”的简单二分法下,要么就把某种文化因子率然判定为彻底“普世性”的,要么就把某种文化因子粗暴判定为单纯“地方性”的。 比如,有了由此所带来的一分谨慎和弹性,即使对这两位如今已经广被接受的西方音乐家,也不必过于急躁地将他们全然归入“普世性”的范畴,而可以再对他们作品的内容进行小心的细分,看看其中究竟哪些有资格进入公共的“大空间”,而哪些则只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小空间”。——这样一来,就算我们内心中再喜欢莫扎特,或者再钟爱贝多芬,也仍然足以清醒而警觉地意识到,这种对于音乐的爱好实则是先行经过了自家诠释的,并且只有这样才能在内容的“过滤”之后,而被顺利地接纳到公共性的“大空间”中。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至少也就不必在跟从着他们的音乐,并且沿着其歌词的内容去无穷下探,一直下探到他们各自的“小空间”去。 比如,就以本人生平最爱的贝多芬为例,我们一方面当然应当意识到,即使以往只被抽象理解的《第九交响乐》,仍有暗中的文化之根和宗教之根,而不能对它用人声所推向的乐曲高潮,只认定是利用了某种“高级的乐器”。但我们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到,尽管这两者几乎就是前后脚完成的,而且《贝九》还肯定是挪用了《庄严弥撒》中的人声要素,但由于其宗教意味的浓淡不同,毕竟只有前者才是属于“大空间”的,而后者则只能是属于“小空间”的。——换句话说,在非西方的或非基督教的世界中,人们也许可以接受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却未必就可以领教他的《庄严弥撒》,因为至少在前者那里,特定宗教的意涵并不是以一种劝世口吻而道出的,而是以一种稀释的和人间的形式而表现的;甚至,人们即使在接受《贝九》的时候,也未必就是全盘接受了它的“文化之根”,而只是接受了它能跟自己的文化意识相互重叠的那个部分。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最近才在一篇讨论西学的文章中指出:“在交互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中,必须要分清哪些东西属于‘文化之根’,和哪些东西属于‘文化之果’,从而知道哪些东西只能属于‘小空间’,而哪些东西则可以属于‘大空间’。也就是说,由于任何特定的具体文明,都在它的特定起源之处,有其独特而隐秘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根源,所以,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真正能够提供给跨文化交流的,便只是从那些根底处长出来的、作为‘文化之果’的东西。反之,对于那些隐秘而独特的‘文化之根’,凡是居于特定文明之外的人们,充其量也只能去同情地了解,力争能够既‘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而绝不能亦步亦趋地再去学习。”[xii] 应当说明,这种方法并不是在针对哪种特定文化的,而毋宁说,它的原则乃是“四海皆准”的或“普世性”的。正如我在前述那篇文章中所指出的,有了“大空间”对于“小空间”内容的“过滤”,即使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在印度佛教哲理的背后,也还有作为隐秘身体态度的瑜伽修行,或者在希腊悲剧文化的背后,也还有作为民间孑遗形式的献祭节礼,正如在中国岐黄医道的背后,也还有作为身体想象的吐纳导引之术,我们在当下这种全球化的“大空间”中,也只能理性地收纳佛教哲理、悲剧文化,和岐黄医道,让它们到未来的世界性文化中,去构成具有普适意义的文化因子。——而如果缺乏这种方法上的这种谨慎,一旦认识到了曾经发生在某个特定“小空间”中的、曾经展现于某个特定历史阶段中的因果关系,就急于要沿着这种关系溯源回去,甚至恨不得让自己从文化上“脱胎换骨”,那么,这样一种过了时的、不无可笑之处的“返祖”心理,就仅仅意味着在步步地误入歧途了。 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基于“大空间”和“小空间”的区分,再进一步去厘清什么只是“文化之根”,和什么才是“文化之果”。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居于某个独特“小空间”之外的人们来说,那些具体的“文化之根”当然也是重要的,正如中国本土的“国学”对于我们自己一样;然而,它们这种独特的重要性,却毋宁表现在各自的“小空间”中,而不在这个同属于全人类的“大空间”中。——正是这一个个既不可置换、又不可替代的“小空间”,在一个方面,需要在自身共同体的“必要的张力”中,维持住自己固有的生活世界,和看护好既有文明的路径依赖;而在另一个方面,也要为彼此共享的、多元一体的“大空间”,提供出源源不断的、借以持续对话的精神动力;更不用说,在它们之间所发生的摩擦、冲撞和协商,还要为世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出作为互动与互渗之结果的未来方向。 然则,沿着这样的逻辑又不难想到,真正需要我们去完成的文化使命,就显然不是钻进别人的“小空间”去,而是要守护住自己的“小空间”,和照看好自己的“文化之根”,再把它由此生长出的“文化之果”,顺利地带到全球化时代的“大空间”去,使之构成世界性文化的普适因子之一。换句话说,我们当然不是不需要去同情地了解,居于世界其他“小空间”的人们,究竟是沿着什么线索思考到了这里,但我们却决不可以泥于还原主义的死板逻辑,并且沿着历史决定论的不可靠线索,打算回到别人未曾祛除巫魅的那个“原教旨”去;否则,一旦把倒车开到了别人的“小空间”里,那也就等于是掉进了思想的陷阱里,——那里对我们乃是深不见底和漆黑一团的,是属于神秘主义和特殊主义的,是对于各大文明都无法通分的。 回顾起来,这实则也正是为什么,我在那篇论述伯林的文章中,一方面要力主“文化之根”对他本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要劝止他的读者们,只去满足于他在思想上提供的“文化之果”——“既然这只‘跨文化的狐狸’想要平衡地立足于各种观念的叠合之处,那么,他自然就要提防任何‘不厌其深’的追问,因为任何这类刨根究底的、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追问,都自然要乞助于某种罗尔斯意义上的‘完备性学说’,从而触及隐藏其后的这个或那个文明的幽深之根。正因为这样,渴望生活在各个文明的哪怕是空泛公分母之上的伯林,也就宁肯漂浮在一个虽表浅却平静的外层上,也不愿陷入那个充满岩浆的黑暗地心了。”[xiii] (四) 有意思的是,借助于“照着讲”、“接着讲”和“对着讲”,“大空间”和“小空间”,“文化之根”和“文化之果”这一系列彼此关联、渐次生发出来的概念,以及由它们所共同构成的、既开放和进取又谨慎而弹性的理论立场,我们在文明进程中对于学术话语的“讲说”,已经表现为不仅是启发性的、而且是协商性的,不仅是批判性的、而且是自反性的。 这中间的“启发性”意味着,一方面,当我们把对于学术话语的持续言说,通过“对着讲”而拓展到国际的“大空间”之后,它当然会大大开拓我们的心胸与视野,从而以一种崭新的阐释语境与角度,激发出解说经典文本的新型灵感。于是,也正是在诸如此类的“对着讲”中,传统的中国文化虽未曾失去固有的风神,但它却会在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下,被不断地进行发掘、评估和重组。——也正因为这样,某些以往被压抑或忽视的潜在线索,如今就有可能在“对着讲”的语境下,被重新赋予了思想的力量和生机,从而,某些曾经被判为先哲“短板”的外缘观念,如今也有可能在“对着讲”的激发下,而以“正中下怀”或“早该如此”的惊喜口气,被从自身的精神历程中接引出来。 为什么偏偏是坚守儒生气节的陈寅恪,反会奋笔写下堪称“清华校魂”的名言:“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又为什么偏偏是被称为“一代儒宗”的马一浮,反而会在反驳章学诚的考据时,沿着儒家的思路发挥出这样的思想:“今人言思想自由,犹为合理。秦法‘以古非今者族’,乃是极端遏制自由思想,极为无道,亦是至愚。经济可以统制,思想云何由汝统制?曾谓三王之治世而有统制思想之事邪?惟《庄子,天下篇》则云:‘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某某)[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乃是思想自由自然之果”?[xiv] 其实,也正是沿着这样的思想逻辑,人们当年才可能又从梁启超的笔下,读到类似下面这样的激辩文字:“夫天地大矣,学界广矣,谁亦能限公等之所至,而公等果行为者?无他,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其有稍在此范围外者,非惟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此二千年来保教党所成就之结果也。曾是孔子而乃如是乎?孔子作《春秋》,进退三代,是正百王,乃至非常异义可怪之论,阐溢于编中。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而自命为孔子徒者,乃反其精神而用之,此岂孔子之罪也?呜呼,居今日诸学日新、思潮横溢之时代,而犹以保教为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xv] 但另一方面,这种文化言说“协商性”又意味着,即使已经坚定地步入了国际的语境,我们的学术言说也仍能保持它的谨慎,并且就在持续“对着讲”的研讨氛围中,即使对于已然涌入了“大空间”的文化观念,也仍能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思考,乃至保持着要求重申和剔除的权力。无论如何,既然迄今为止的全球化进程,仍在很大程度表现为“西方化”的进程,那么,对于这种“单极化”的不无偏颇的全球化,我们就有权利去进行反思、改造和重塑。——事实上,也是惟其如此,这种在“大空间”中对于叠合意识的寻求,才能够具有足够的弹性和活力,才容纳下所有人类部落的持续对话,也才能向今后的历史保持敞开。 摆在我们面前的“全球化”,毋宁是一种相反相成的运动。——在无可回避的外来文化冲击下,我们只能是虽然并非全然被动地,却又是心怀警觉地,既是要去加入、又是要去抵抗,既在从本土中抽离、又在朝向它再嵌入,既是在领受其裨益、又是在疏离其损害,既接受了它的标准化、又启动了传统的再发明,既去拥抱着普世化、又去向往着在地化,既在进行着向心运动、又在发展着离心趋势,既去享受均质化的好处、又去欣赏个性化的特色,既看到了历史的断裂、又努力要让文明延续,既在跨越有限的国界、又要回归文化的本根……宽广而全面地看,正是这种带有杂音的双向发展,才较为理想和包容地,构成了所谓“全球化”的全部特征。[xvi] 回顾起来,也正是因为这样,至少在我本人的解释中,以赛亚·伯林才既不是专主“自由”观念,也不是专主“多元”观念,而毋宁是把自己的立足重心,安顿在“自由与多元”之间的张力上。而且进一步说,在渊博而灵动的思想家伯林那里,作为一只“跨文化的狐狸”,他是既在向“多元”去寻求“自由”的文化支撑,也转而在以“自由”去划定“多元”的底线。——这样一来,居于思想两极之间的弹性张力,便使得彼此都能给对方带来自身规定性,也使得彼此都要接受对方的规定性,从而才能在不断的消长、辩难和协商中,逐渐地走向一种保持紧张度的融合。 看来,我们国学的前途也正是如此,而且,我们也没有理由不让它如此。我从来都不像我老师那样,哪怕是用半开玩笑的口气,去自叹一句“百无一用是书生”。相反在我看来,正是在我们这一代学者身上,担负着如何“讲说”国学的重大使命。严重的双重危机表现在,我们当然也有可能,只还打算去“照着讲”和“接着讲”,从而也就继续把它局限在这个“小空间”中,从而使它自然而然地萎缩下去,越来越失去它在“轴心时代”的巨大权重;但另一方面,究竟怎样在“对着讲”的持续进程中,既把它顺利地接引到国际的“大空间”中,又能同时发挥出它的“批判性”和“自反性”,从而既不让它显得消极、又不让它显得固陋,既不让它格格不入,又不让它化为乌有,那同样不是轻而易举之事。 与此相应的是,在自己那篇反思“通识”概念的文章中,我曾对未来“大空间”中的应有通识,给出过基于这种“对着讲”的规定性:“长远来看,作为全球共同努力的目标,则需要在持续的文明对话中,经由艰苦而平等的商量与研讨,共同制订出多元一体的、全球化时代的人类通识,那通识必须建立在各民族的国学(包括西学)之上,而保证它们既相互重叠、又各有侧重,——而且,那相互重叠的核心部分,必须具有足够的确定性,以确保人类的和平共处;那各有侧重的部分,又必须具有足够的浓度,以确保每一种宝贵文化的原生态与生命力。”[xvii] 正是在这种具有“自反性”的“对着讲”中,我们在把自己的国学带入那个“大空间”的同时,也应当头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后的传统无论多么厚重和伟大,都绝不是什么僵硬的、刀枪不入的死物;恰恰相反,它会在我们同世界进行持续对话的同时,不断借助于这种对话的“反作用力”,而同整个国际文化展开良性的互动,从而不断地谋求自身的递进,也日益地走向开放与自由。如果宏观地展望,实际上全世界各个民族的“国学”,都在百川归海地加入这场“重铸金身”的运动,而我们的传统当然也不能自外于它。——从深层的学理而言,也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这次从民间自然兴起的、正待被充满热情与远见地因势利导的“国学热”,才不致沦为一次毫无前途的、简单孤陋的当代复古,或者对于被毁传统的一种单纯情绪性的追悔懊恼;恰恰相反,正如一棵枯木逢春的大树一样,当我们的文明之树把根须扎向身下土地时,它反而是为了让居于最顶端的树梢,更加挺拔地指向和冲向蔚蓝的天空。 注释: [i] 刘东:《意识重叠处,即是智慧生长处》,《思想的浮冰》,第62-6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ii] 刘东:《从接着讲到对着讲》,《道术与天下》,第23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iii]韩愈:《原道》。 [iv] 韩愈:《原道》。 [v] 刘东:《从接着讲到对着讲》,《道术与天下》,第23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vi] 刘东:《从接着讲到对着讲》,《道术与天下》,第23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vii]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7-38页。 [viii]刘东:《个人认同与人格境界》,《道术与天下》,第18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ix] 刘东:《从接着讲到对着讲》,《道术与天下》,第238-23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x] 刘东:《伯林:跨文化的狐狸》,载刘东、徐向东主编:《伯林与当代中国:自由与多元之间》,第150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 [xi]刘东:《文化观的钟摆》,《近思与远虑》,第20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 [xii]刘东:《总体攻读与对话意识》。 [xiii] 刘东:《伯林:跨文化的狐狸》,载刘东、徐向东主编:《伯林与当代中国:自由与多元之间》,第157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 [xiv]刘东:《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第209-21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xv]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xvi] 刘东:《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第20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xvii] 刘东:《诸神与通识》,《道术与天下》,第50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责任编辑:admin) |
